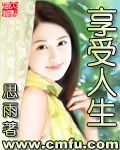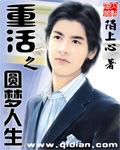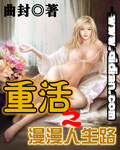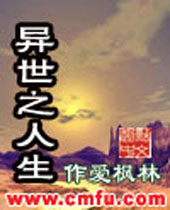才情人生-乔冠华-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泽东不亲不疏,在南北两乔中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南乔留姓北乔留名,真是极妙的 办法!乔冠华与胡乔木双双接受了毛泽东的“调解”。
不过,乔冠华后来曾对胡风夫人梅志开玩笔说:“胡乔木把我早就起用的‘乔木’这个名字 抢去了,真叫人气愤。”看来他还是有想法的。
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乔冠华与龚澎不止一次地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龚澎,同乔冠华是首度相见,但读过他的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 乔冠华的不羁的文才、洒脱的风度,尤为赏识。他曾戏对乔冠华、龚澎夫妇说:
“你们二人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时在中共代表团传为美谈。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1)
国共双方的《双十会谈纪要》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 陪同,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谈判。乔冠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留在重庆 。
尽管国共双方还在谈判,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在遭到解放区 军民的顽强抵抗后,被迫同中国共产党就军事冲突等问题举行会谈。
12月27日,周恩来把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书面建议提交国民党代表,请其转交 蒋介石。31日,国民党代表书面答复中共代表团,同意就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等问题进 行谈判,并提出由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会谈停战办法。
经过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7日,根据 协议,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 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其任务是协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和有关受降事宜 及整编军队等问题。
“三人小组”的协议,交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它的任务是执行停战协定和“三人小组”的协议。“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 国 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军调部”于1946年1月14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共产党委员叶剑 英,参谋长罗瑞卿;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美方委员饶伯森,参谋长赫斯克。
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叶剑英组建了军调部中共机构,有 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计划执行、新闻发闻、行政、交通等科组。乔冠华、龚澎 这时也被调去军调部,龚澎担任中共方面的新闻组长,在董华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委员叶 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
在此期间,乔冠华因公去了一趟延安。
杨家岭。枣园。延河。宝塔山。清凉山。桥儿沟。蜂寓般密密麻麻的窑洞。茂密的丛林…… 乔冠华是第一次到延安,延安的一切都给他新鲜可爱的感觉。最让他难忘,他受到了毛泽东 主席的接见。
那天,乔冠华接到通知,他穿戴整齐,渡过清浅的延河,约莫走过十来分钟,在山谷中露出 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央办公厅和大礼堂。再走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直 至山脚,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的住宅,门口站在英姿焕发的卫兵。
毛泽东的窑洞在山脚下,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内显得 亮堂。家具陈设简单,有的甚至用油漆漆过。毛泽东一生嗜书,书房里各种书籍不少,办公 桌上还摊着大摞书报、文件,以及正在起草的文稿。乔冠华被引进了毛泽东的房间,毛泽 东与他亲切地握手,使乔冠华心里暖融融。
乔冠华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工作近况和写作的甘辛,毛泽东提到了他所写的那篇《方生未死 之间》。
鼓励他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笑谈之中,毛泽东朗声大笑时的豪迈而天真的神态,给 乔冠华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逗留期间,胡乔木几乎每天都约乔冠华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作长时间的散步。在他 的 住处和延河之间,有一片相当开阔的绿色田野。每当工作完毕或吃过晚饭,他们两人相约穿 越田间的小径到延河边去,在延河边的岩石上闲坐谈天,或者是沿着河畔来往反复地漫步。 在他们四面,往往会有许多充满活力的男男女女像他们一样,把这里看作是可以使自己获得 休息和愉快的所在。
其时,沿着浅绿色的蜿蜒东流的延河向西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遥相峙立的清凉山和宝塔 山;往东看去,则是一片伸向远方的在陕北地区难得一见的平川……这片天地真是具有 无限的魅力。乔冠华和胡乔木在这里互相交换对重庆分别后时局变化的看法,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的憧憬……
别人,延安!
别了,革命圣地!
乔冠华与战友们依依惜别,又重返充满荆辣的国民党统治区。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2)
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中共代表团团 长周恩来率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齐燕铭、章汉夫、钱瑛、王炳南、 童陆生、宋平、章文晋等分两批飞抵南京。乔冠华则从延安来到南京。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位工作人员。对外的名称叫中共代表团南 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南京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
武汉 、湖南、广东、广西、闽粤边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南京局下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 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任副书记,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 络处处长)和龚澎是外委会的四员大将。
不久,中共代表团为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委托已从北平回到上海的龚澎,在上海找 一处适中的房子,作办事处用。
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有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名叫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这里是上海 旧 法租界的住宅区。旧法租界的路名,大多是以法国人的名字命名。例如霞飞路(现在的淮海 路),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军统帅命名的;贝当路(现在的衡山路),也是以一位老将 军命名的。马斯南也是一位法国名人。
马斯南路,当时在上海人心目中,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与其他马路相比,总是显得静 谧、清凉,不论是潇潇的风雨,不论是炎炎的烈日,马斯南路两旁高大的杼相树,总是深情 地伸展双臂,枝叶繁茂,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
龚澎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与一位可靠的朋友徐畹球女士一起寻寻觅觅,最终找到马期南路10 7号一处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为思南路73号,下面为叙述方便,均称思南路)。当时原住户 黄天霞已去南京,房子是空着的,于是便用6根金条租了下来,1946年5月16日办好了手 续。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中共代表团在沪设办事处。所以在它的门口挂了两块铜牌:一块是 用英文写的叫“周恩来将军寓所”,一块是用中文写的叫“周公馆”。这样,周恩来和代表 团其他同志来上海开展工作,就住在这里。
周公馆成了众人关注的中心,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处理党内外工作,同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商 谈,也会见上海各界的代表人物。一时间,这条旧法租界的僻静马路,为社会所瞩目,来往 行人,竟比过去增加许多。自然,其中还有不少化装成小贩、修鞋匠和三轮车夫 的国民党便衣特务。
乔冠华与龚澎夫妇常驻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因国民党不准在上海出版《新华日 报》,中共代表团将《群众》杂志从重庆移到上海于6月3日出版,李维汉主编,并出版英文 版《新华周刊》,由乔冠华、龚澎负责。这16开本的宣传刊物,是一家“夫妻老婆店” ,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统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 传刊物刚刚出版到第3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乔冠华夫妇在上海时工作勤勉,尽心尽力。这给曾在周公馆当过交通联络员的王思敏, 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周公馆生活散记》中回忆:
在这个公馆里没有主妇式的当家人的,每天的伙食即由我和杨胖子全权安 排,反正不超过也不低于两菜一汤就是了。
开饭了。别看这幢在外观上颇为气派的花园洋房,号称公馆,可连吃饭的桌椅板凳也是少得 可怜的。因此每当开饭时先来者总是捷足先坐,后来者只得伫立而餐,这个规矩对谁也一视 同仁,毫不例外。
乔木(乔冠华)和龚澎两口子是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他俩的外文造诣颇深 ,工作也比其他人似乎要忙一些,打字机的嘀嗒声不时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每次开饭,往 往要“三顾茅庐”,他们才姗姗下楼(当然是站着吃),为此,陈姐在背后曾嘟噜过:“平常 到蛮好格,就是吃饭架子大来兮。”
纵观这个公馆的种种生活方式和诸类人物,与一般真正的公馆对比,是非常特异的。为了工 作需要,这里男的也西装革履,女的衣着华丽,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王 思敏:《周公馆生活散记》,载《上海滩》1989年第6期。
乔冠华在周公馆工作时,与各界人士保持接触,他经常接待文化人。如胡风就曾多次来周公 馆,与他和陈家康、徐冰会面。乔冠华与胡风还讨论过文艺问题,围绕创作方法、创作技巧 发表各自的看法。
乔冠华还在新闻界组织了时事座谈会,每一两周一次,聚餐并漫谈时事问题,参加的人都自 付聚餐费。经常到会的除乔冠华本人外,还有陈家康、姚臻(当时是苏联在上海办的《时代 日报》“军事述评”
的专栏作者,笔名“秦上校”,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金仲华(《联合晚报》记者)、姜椿芳(时代社和《时代日报》总编辑)、冯宾符(《联合晚报 》编委)、宦乡(《文汇报》副主笔)等十余人,会上主要是分析时局变化,国民党军队如何 迅速崩溃,人民解放军如何向前挺进,以认清形势,澄清模糊认识。乔冠华每会必到,都要 发表宏论高见,侃侃而谈,往往语惊四座。
这样的聚会,胡风后来也参加了,他觉得收获匪浅,据他回忆:“大概有一次在我隔壁的冯 宾符家聚会时约我参加了,以后就每次都参加。他们漫谈国内国际时事和军事形势,我开口 不得,旁听而已。
但对我有很大好好处,能够把报上看到的情况理解得有条理些,更明确地 看清国民党的崩溃趋势和解放军的前进势头和方向,以及整个斗争局面。还有,乔冠华和陈 家康都是善于谈笑的,聚会时空气很愉快。不记得乔冠华有过摆领导人面孔的情况。……梅 志记得我也做过一次东,是在家里请他们。”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 稿》,第77~78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前面我们曾经写到的乔冠华夫妇在重庆结识的好友,李颢医生这时也在上海。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李颢意外地接到即将回上海接收卫生局的俞松筠同学的邀请 ,要他到上海某医院任职。回上海工作对李颢的吸引力太大了,因为上海是他生长和求学的 故乡。但是考虑去上海是国民党在卫生行政界的小头目俞松筠所邀请的,事关重大,必须去 找最信赖的好友乔冠华商量。
于是,李颢身揣俞松筠的邀请信,路上特地买了一大包磁器口特产盐水花生,当经过作家徐 迟的住处时,他忽然想到要给好友留下一点可口的花生,再去找乔冠华。
天下就是有那么凑巧的事,李颢这一拐还真拐对了乔冠华正在徐迟家里。听李颢这一讲 ,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商量着是否去上海之事。最后商定接受俞松筠的邀请。
不久,乔冠华、龚澎也随中共表代团来到上海,住在周公馆。而李颢就住在相距不远的贝勒 路,他们经常相聚。
1946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天气特别闷热。李颢正在吃晚饭,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 还来不及寒喧,就听到对方的声音:
“你在家等我,我有急事找你。”
原来是乔冠华打来打来的电话。
李颢凭着多年的经验,预料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而且此事肯定非同一般。因为往常乔冠 华打电话时,总免不了捎带说几句俏皮话,逗逗乐,而今天则完全不同,风趣幽默不见了。 出了什么事呢?李颢的心悬在半空中,始终放心不下,他放下电话就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着乔冠华的来到。
此时,天越来越灰暗,突然一阵旋风,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瓢泼大雨。只见雨幕中急驶 过来一辆小轿车,嗄地一声停在李颢前门,他赶紧迎上前去。
“什么事?快说!”李颢连忙问道。
“上车再说。”乔冠华说得很干脆。
李颢钻进车内坐下,就听到一声既熟悉又亲切的呼唤:“李医生,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