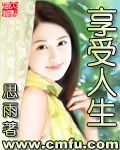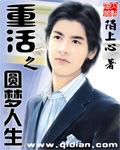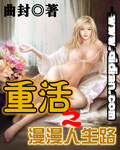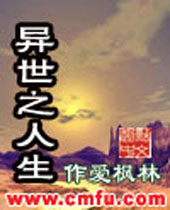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部分第3节 水木清华(2)
清华大学收费不高,比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少得多,只比北京大学略微多一点,在校学生 住宿、伙食条件不错,乔冠华每月只需花三元钱(三块大洋),就吃得很好,早餐有豆浆、油 条,有时还有个荷包蛋,稀饭则不限量。
当时考清华大学,不分专业,只分文、理两科,乔冠华报考的是文科。进了清华以后,马上 就面临选哪一个系的问题。第一年,乔冠华选择了中文系,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出于如
下的考虑:第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一向十分爱好;第二,中文系设置的必修课相对较少, 他可以有空余时间多看点各方面的书。
这时,清华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名教授有陈寅恪、刘文典、杨振声、朱自清、杨树 达、黄节等,系主任先是五四时期写过白话小说《渔家》、《玉君》的作家杨振声,后是朱 自清。听了他们的课,乔冠华觉得眼界大开。中文系一年级比较重视对学生进行文化修养, 特别是写作训练,所以乔冠华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更进一步提高,文章写得精炼深邃 ,富含哲理。
在中文系,乔冠华与国文教师朱自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彼此很谈得来。他既佩服朱自清深 厚的学养,又深膺他的人格魅力。朱自清,1898年生,散文家、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早 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创作了《毁灭》等多部新诗。1925年来清华任教后,专攻散文 ,成为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表现了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和正义感,意境清新幽 雅,语言简朴亲切。早在念中学的时候,乔冠华就读过不少朱自清的作品,其中像《背影》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名篇,乔冠华甚至能够背诵。朱自清散文朴实 近人 、委婉细致的风格,深深地感染着乔冠华。到了清华,他更愿意听朱自清的课,有时还就文 学写作、时政大事展开讨论,互为引援。
清华大学对教授们很优待,它靠着庚子退款的余额,在校园南园建造了教授住宅,薪金也很 优厚。工作到了一定时期,就由学校出钱让教授到国外去参观访问。这年,朱自清获得了公 费出国游历的机会,他利用11个月漫游了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 六国,考察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他在饱览异国风情的同时,也在同时思索人类 的文化发展。
朱自清从西欧考察归来,乔冠华与几位同学相约去看望恩师,并了解国外情况,因为外国毕 竟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特别像意大利这样的文明古国,在乔冠华心目中地位很高。他问朱 自清:
“威尼斯究竟是什么样子?”
“威尼斯嘛,当然很有名啊,不过你去了呢,你就会感觉到,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城市,有 一点像我们的苏州吧,不是威尼斯美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威尼斯有它的好处,我看苏州也有 苏州的好处。”朱自清语调舒缓地说道。
“听说西欧国家生活很富,”乔冠华又向朱自清打听,“那末,它们是否也有乞丐?”
“当然,外国也有乞丐。”朱自清侃侃而谈,他说:
“我到的这些国外,乞丐也分各色人等,有画丐、乐丐、话丐等等。警察禁止空手空口的乞 丐, 乞丐便都得变做艺人。若是无艺可卖,手里也得拿点东西,如火柴、皮鞋带之类。路角落里 常有男人或女人拿着这些东西默默站着,脸上大都是黯淡的。其实卖艺、卖物,大半也是幌 子;不过到底教人知道自尊些,不许不做事白讨钱。”这时,他停了一下,呷了口茶又道:
“只有瞎子,可以白讨钱。他们站着或坐着;胸前有时挂一面纸牌子,写着‘盲人’。又有 一种人,在乞丐非乞丐之间。有一回找不着一家杂耍场,请教路角上一个老者。他殷勤领着 走,一面说刚失业,没钱花,要我帮个忙儿。给了五个便士(约合中国三毛钱),算是酬劳, 他还争呢。其实只有二三百步路罢了。跟着走,诉苦,白讨钱的,只遇见一次;那里街灯很 暗,没有警察,路上人也少,我又是个外国人,他所以厚了脸皮,放了胆他自然不是瞎 子。照区区的见解,外国也不是什么天堂啊!”
这番对话,乔冠华始终记在心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东西都化为过眼烟云,不过乔冠 华对此却记忆犹新,他说:“他(指朱自清)这番话当时对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那时我们对 欧洲著名的建筑、著名的城市,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看出,朱先生 确实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他不像有些人到了国外什么地方,就把那地方说得天花乱坠。这 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 第133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朱自清表现的“非似媚 眼仰视外国,非以奴颜卑视自己”的态度,对乔冠华后来投身外交事业,不无裨益。
朱自清:《欧游杂记》,第180页,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5月第1版。
乔冠华的国文虽好,但是他的兴趣并不仅在文学。在清华的第一年中,他就了解文科各系的 情况,如果说中文系的必修课少,那末,清华的哲学系的必修课比中文系更少。所以为了能 够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1930年,乔冠华提出转系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这样,乔冠华在清华的第二学年就从中文系转到了哲学系。清华的哲学系也是文科的一个强 系,云集着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与中文系及历史系合聘)、邓以誓、沈有鼎、张荫麟、 贺麟等知名教授,他们都教过乔冠华的课。其时哲学系系主任是冯友兰,他是一位享誉中外 的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等煌煌巨著,他一生以光大中国哲学传统为己任,他在“起 而行道”失败之后,再一次沉寂下来 “坐而论道”,在他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以自己的生命 去点燃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希望之光。清华哲学系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教学目的,但在冯友兰 先 生主持系政期间,曾在当时校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0年3月31日,第57期)撰文强调 :学哲学可以养成清楚的思想;学哲学可以养成怀疑的精神;学哲学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 学哲学可以养成广大的眼界。……
参见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 文化》,第3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冯友兰等教授每天都为学生们上课,授课的时间不长,差不多平均每天一个小时左右。所 以,留下的时间可以由乔冠华自由阅读,由此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说穿了,乔冠华对学哲 学有一定的兴趣,但也不是他最想学的东西。不过无论如何用乔冠华自己的话说:“我在学 哲学,在念那样一些古典哲学、西洋哲学的书籍以后,尤其是后来我感到是受益不少的。”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32页,学林出版社1997 年12月第1版。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位教授,他就是金岳霖先生。乔冠华曾多次向他请教治学方向,探讨 如何做学问。金先生对他再三强调要有探索精神,要多动脑筋,弄清问题的是与非。
金岳霖先生终身未娶,潜心研究逻辑论和知识论以及西方古典哲学,他讲课时与同学们一起 研读英文原著,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多提问题,以养成质疑和思考的习惯。金先生还善于运 用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乔冠华晚年在口述自 传时,以较长篇幅,无限感激地回忆起金岳霖先生对自己莫大的帮助,他说: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金岳霖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教会了我对任 何事物要好好地想 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这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讲是件 大事。我记得,有一次金先生讲课,是关于伦理的知识,书的名字,我记不大清楚,金先生 教课是这样一个方法,他是一章一章地念,上课以后就问大家都有没有(英文本),请打开第 一章第一页,叫大家看,然后他在上面就问,你们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当 时课堂上五十几个人,课堂上没有几个能回答,鸦雀无声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金先生说, 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讲的话都是对的呢?大家也不讲话。
金先生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怎么不讲话?金先生又说,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人类的知识是不是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感性来吗?他没有往下讲,他说:“我希望 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
金先生这些话,对于我是很大的震动,所以在以后的年代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3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 第1版。
一个教授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金岳霖先生的巨大的精神魅力。有人称“碰见 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殷海光语,见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 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诚哉信言。乔冠华一开始不 习惯金先生这样上课,回来后经过思索,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就是让学生不要轻信书本知识 ,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判定是否真有真理,这种读书方法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部分第3节 水木清华(3)
一个人的信仰,是基于他的思想观念之上的,而正确的思想以及世界观的形成,必然需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西方哲人说过:“思想就是力量,一切力量都来自完成职责。”(雨果)
“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点;并且他的全部义务就是 要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帕斯卡尔)思想,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痛苦的,有
时 不够成熟,但思想对人来说,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可以这样理解,乔冠华上清华求学,就 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探索革命真理。
据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回忆,乔冠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常常念及清华园里的苦读马列经历。他 说在他到清华上学之前,在家乡,由于北伐战争、大革命的影响,他有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 想,因为在乡里、学校里闹点风潮,但是却并不懂任何革命道理。进大学,学哲学就是为了 追求信念,追求革命真理。
他说,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不少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 的同志当时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不过他的道路略有不同。他决心献身无产阶级革命,更多 地是从读通马克思的著作,弄通马列主义真理开始的。他说,那时在清华,他是个很用功的 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清华图书馆有一些马克思的著作。这些苦读使他坚定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章含之:《冠华心目中的清华园》,见《风雨情》,第264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在清华,最吸引乔冠华的只能是图书馆。乔冠华是清华图书馆的常客,一到课余时间 ,他就到图书馆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清华图书馆,是乔冠华心目中的“精神圣殿”。图书馆 装饰典雅,多种典籍、图书、报刊品种繁多,排列整齐,取阅方便。特别是收藏了不少马克 思的原著以及中西方哲学名著,这使乔冠华爱不释手,潜心钻研。只见他有时左右巡索,有 时埋头伏案,有时目不旁瞬,有时奋笔疾书。在这里,使他真正浸润于知识的海洋里,有一 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在清华的四年,乔冠华就是这样一头扎在书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阅读,书海无边苦作舟,他 如海绵吸水逐本逐本地阅读英文、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著作,几乎马克思的所有经典著作,他 都读过,甚至有的读了还不止一遍。此外,他还阅读大量西方古典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有 一 段时间,他就把很大的精力花在与马克思主义有很深关系的黑格尔的学识上。他读了图书馆 里收藏的黑格尔的绝大部分著作,有的是德文原著,有的则是英文译本。经过刻苦钻研,乔 冠华曾于1933年上半年在哲学系系会上,做过“黑格尔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报告。
这时,清华来了一个美国来的教师,他叫黑格,是黑格尔专家。乔冠华在看黑格尔著作的时 候,遇到难题就去请教他,他很热情,认真辅导,对乔冠华教益颇大。
乔冠华在清华的最后一两年,受马克思启发,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因为马克思在著作中, 有很大一部分篇幅谈到中国问题。他涉猎的范围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中国的 对外贸易、工商手工业、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变化的关系等等。他边读书、边摘记,他按问题 性质摘录好多本读书笔记。
当他翻阅腐朽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原文 ,读到帝国主义信口雌黄的叙述说,不禁拍案而起,大声怒斥:“岂有此理!”弄得图书馆 其他正在看书的同学转过脸来朝他笑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清华的不少校友都说乔冠华 这个人敢言敢怒,从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
后来,乔冠华每天在图书馆里抄录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海关的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