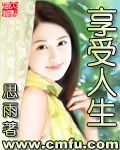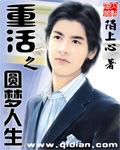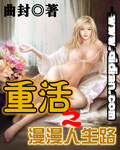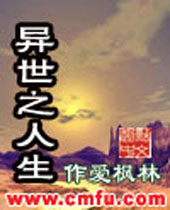才情人生-乔冠华-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挥洒自 如的文笔开始撰写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
当然,乔冠华积习不改,他还是利用空余时间读书。他从欧洲带回了不少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其中包括四大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集。在此期间,他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地看完了。 看完了书之后,他更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敬佩。
这时,原来一起留学日本的钟敬文教授以及年轻的记者、漫画作者郁凤(郁达夫的侄女),也 都投笔从戎,在余汉谋部任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乔冠华与他们有过不少接触。
1938年5月,乔冠华碰到了灾难性的日寇大轰炸。由于市政府防空组织的懈怠,根本无法有 效地组织群众及时疏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广州的居民伤亡特别惨重。
轰炸过后,乔冠华走上街头,眼前的惨状不忍目睹!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几乎被炸成瓦砾场 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夷为一片平地,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 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体。路上到处散落着人的碎肉,毛茸茸的 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人们发着呛天骇地的 哭声,在尸丛中寻觅他们的亲人。乔冠华的眼睛湿润了。
他诅咒这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也痛恨当局贪生怕死,毫无抵抗的意志与决心。当时 广州社会上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气氛,一般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 时候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情此景,真令人叹惋。
广州是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的,距日本从台湾发兵于10月12日开始进攻广州还不到十天。
乔冠华是在广州沦陷前夕,跟随军部撤离至韶关的。韶关本来是广东的一座中等城市,在19 38年10月以后变成了广东的中心。然而,设备、房屋不敷使用,一切都不能够适应这突如其 来的形势,就只好把机关分散在多个村庄里。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要走半个小时,办事 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情报、材料中断,乔冠华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而心情变得 极为郁闷。赵玉军曾派他去东江考察,实际上是让他游览风光,散散心。回来以后,乔冠华 心情并未改观。
第二部分第5节 成名香港(2)
这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 。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 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 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
集军事 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
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其他诸如印刷、校对、资料、发行等事务都由原参谋处的 工作人员来做,乔冠华是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 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 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 在进行。 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 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 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国军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 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 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的梁路晨同志觉得 我写的评论,登一下就完了,太可惜,就建议我办一个通讯社,把写的文章,用笔名的办法 发往世界各地,扩大我们的影响。我说可以呀!没有坏处嘛!但我们是余汉谋属下的报纸,不 能用原名发稿,必须用笔名发稿。那么就用乔木吧,他信口提出来,我随便就答应了。这样 ,在我写社论不久,我的社论差不多每出一篇,就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华侨报纸发 稿。当时的华侨报纸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用乔木的笔名就是这样开 始的。后来等到解放以后,我到这些国家访问,特别是去印尼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不少青年 ,他们告诉我,在抗战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48~149页。
如上所述,乔冠华所写的社论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此后每篇一如既往,这些国际述论能 做到文笔优美、论点新鲜、感情真挚。对这些精彩绝伦、警辟独特、动人心弦的文章,人们 从它的一贯风格,判断出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为社论一般是不署名的)。开始不知道作者 是谁,不过后来谜底还是得到揭晓。乔冠华的终身好友徐迟,在乔冠华去世一周年之际,饱 含深情地叙述他当时的感受:
报纸(案:指《时事晚报》)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 ,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 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们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 不舍了。
这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艰苦卓绝;随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铁骑过处,山河变 色;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莫斯科城下、涅瓦河畔和逐屋争夺的斯大林格勒废墟中 。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迅即沦陷。这一下,他的火焰般的热情社论,只好收笔打 烊,暂先停歇了。
徐迟:《祭于潮》,见《网思想的小鱼》,第1~2页,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乔冠华在《时事晚报》上的所写的社论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评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 的;尽管千头万绪,而乔冠华却慧眼独具,能够从纷杂的现象中理出明 晰的头绪,所以这些社论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在这基础上,回过头来,评说亚洲问题和中 日战争的关键内容。
与乔冠华同龄的冯亦代,当时也在香港,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每天在港岛《星报》担当翻 译英文电讯的工作,他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正是乔冠华以他成熟而犀利 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的他,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回忆说,每天读着《 时事晚报》的社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 他认为,自己对乔冠华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冯亦代:《 绿的痴迷》,第14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其实,其他年龄段的读 者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二部分第5节 成名香港(3)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 字:“粤华公司”。店里经营各式中国名菜,货色齐全,价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顾 。
这期间,乔冠华常来该店二楼“谈生意”,他清楚:这个“粤华公司”就是八路军、新四军 驻香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地。廖承志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也在其中,他是位中共老党
员,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华侨中有许多朋友。在广州时,乔冠华就结识了他们 。 一方面,乔冠华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告诉乔冠华一些关于时局的看法。乔 冠华认为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
对党的情况工作立下卓著功勋的潘汉年,经常出没香港。乔冠华与潘汉年、廖承志、连 贯等一起研究工作,有时甚至开开玩笑,不失风趣。
起绰号,这似乎是廖承志一生的极大嗜好。他起的绰号往往是内涵风趣,恰到好处。一天, 大家见面,颇为高兴,廖承志眼珠子一转,就笑称他的办事处是:“五子登科”。
潘汉年笑着询问:“何以出此高论?”
廖承志笑眯眯地拍拍自己的“颇有风度”的肚子,摇头晃脑地说:“本人乳名肥仔,故而, ‘胖子’的美称,非我莫属。潘兄,您脸孔不是一马平川,有些小小的盆地,称广林兄, 俗语‘麻子’;连贯老弟,身材矮小墩实,平生恐怕最大的愿望是长成高个子,故而该叫: ‘长子’;至于高挑瘦长个的乔冠华乔老爷,则就反其道而行之,称‘矮子’最合身份…… ”
连贯虽然是第一次与廖承志共事,却十分欣赏廖承志这种幽默风趣的性格,此刻忍住笑反问 道:
“胖子,你恐怕是数学不好吧,数来数去,只有四子嘛,何谓五子登科呢?!”
“这第五子嘛”,廖承志顽皮地眨巴着眼睛,嘴上拖腔拉调,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
恰在此时,只有15岁的小店员陈新推门而入,进来送开水,坐在一旁的乔冠华大手一拍,及 时“救驾”:
“你瞧,陈新是个孩子,岂不是五子登科齐也!”真是一语中的。
“好!不愧是《时事晚报》的大主笔!”看得出廖承志对这个有革命热情,且才华横溢,反应 灵敏的留德博士欣赏有加。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廖承志批准他成立中国新闻社,由国民党余汉谋部资 助,由乔冠华担任社长。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快批复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 在香港成立,成员还有胡绳夫妇、胡一声、郑展等人。他们的文稿,传遍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乃至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上空也不时有“乔木”的名字。
在《时事晚报》工作期间,乔冠华就住在报馆里,这是地处闹市中的一间狭隘的楼房。屋子 有点西晒,白日黑昼,闷热如蒸笼,而香港的暴热又是十分厉害,他常常挥汗如雨,伏案写 作。十分狭隘的居室又临街面,市声透入楼里,使他睡不好觉,他一般只在白天睡几小时觉 ,下午会友、访书、寻资料,晚上写社论,交发稿。
为了工作能集中思想,乔冠华在写文章的时候一手写字,一手端杯酒喝。他的酒量是很大的 ,一口气喝半瓶自兰地。为此,他得了“酒仙”的雅号。事情是这样的:
在冯亦代眼里,乔冠华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人,废寝忘食,吃的很菲薄,而且往往因 写文章,饱一顿有之,饿一顿亦有之。冯亦代与他熟悉以后,实在不忍心看他过着失饥伤饱 ,彻夜无眠的生活,因此几次向他提出在他每天的社论发稿后,即到冯家去吃饭休息。好不 容易,乔冠华才同意。可是不久冯家的保姆便来告状了。她称乔冠华为“酒仙”,说“酒仙 ”除 了喝酒看外国新闻报纸之外,就不好好吃饭睡觉。她说,我把他的书报拿开,不要一会儿又 在他手头了;给他装了饭,他又想心事,把饭菜冷了。好不容易看他睡下,可是我厨下没 有收拾完,他又在看书了。他难道真的成了神仙?因为这位保姆记不住乔冠华的姓,便以酒 仙称之,以后这外号便在朋友中流传开了。
冯亦代悉知很着急,他与乔冠华推心置腹地谈了话。乔冠华叹了口气说:
“国内国外的形势这么紧张,我要写文章就得收集材料,可是时间不多,我想如果当初定
48小时为一日有多好!”
冯亦代“警告”他:“可现在只有24小时一天,你必须服从这个规定。”
他苦笑数声作答。以后呢,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旧习!
为了收集多种资料,乔冠华几乎跑遍了香港书报摊。有一家名叫“利全记”的书报社,他去 得最多。
他在书店里存放了一些款子,随时到那里去,看到有自己喜欢的书刊报纸就拿走, 不用付现款,在账上扣除就是了。在老板的印象中,乔冠华是买书刊报纸最多的一位,几乎 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报纸,诸如《泰唔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 导 报》、《华尔街金融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幸福杂志》、《话时代》、《 亚细亚杂志》、《新群众》等等。
香港有许多旧书铺,逛旧书铺,淘旧书的习惯,是乔冠华在结识季羡林时染上的。在港时, 积习难改,只要有空,他就直奔旧书铺,他一见层层叠起的书籍,就仿佛是老相识了。有时 在那些书架的角落里,偶然拨开厚积的灰尘一看,正是一本心爱的书,说它是“踏破铁鞋无 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不够,而更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萍水相逢,直如梦遇,哪能轻易放过呢!每当黄昏时候,书店都快打烊了,他才挟着 书踱了出来。
当时,香港汇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重庆,有的来自武汉 ,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 在 主编《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