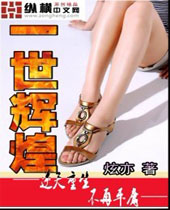宁玛的红辉-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标本用。在五十年代后期,二头牦牛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作父亲的心动了,但不敢作主,给在重庆的母亲拍了电报。母亲接到电报就赶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再穷,也不可把亲生骨肉卖掉,既然医院治不好,那就不治了,要死也死在家里。于是把他从医院里抱了回来。
这时,街上来了个疯疯颠颠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像个叫化子,当地人都叫他“哈子”,意为举止行为不正常的人。“哈子”来到他家门口,不走了,对他家里说,他是来找他的徒弟的。他父母问老头,这儿哪有他的徒弟?老头说那个快病死的小孩就是他的徒弟,还说小孩身上有三块胎记,在什么部位,是怎么怎么个形状。他母亲很惊异,那老头说得一点不错,除了他这当母亲的,孩子身上有什么胎记,连孩子他爸也说不清楚呢。父母没什么犹豫就同意了。反正儿子已没救了,不如就让老头抱去试试看吧。
他六七岁那年,老头把他送回了家。那时他的病已痊愈,从外表看,除了平时不肯多说话,说起话来稍稍有点口吃,一切已跟常人无异。但实际上他跟常人已不一样,常常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譬如,旁人看那座山上,光秃秃的,连一棵树也没有——树在前些年“大跃进”的滚滚洪流中被砍倒了“大炼钢铁”去了,可他就能看出,那山上有座寺庙,当然,那只是一座曾经有过的建筑物,用现代的语言来称呼,或是一种“残留信息”吧?
他回家后,若说跟常人还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小小年纪的他,对佛菩萨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和崇敬。那时,“文革”的浪潮已经兴起,当地许多寺庙已被造反派、红卫兵砸得粉碎。他常常晚上一个人跑十几里路去当地一所寺庙的旧址拜菩萨。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一到晚上就常有很多善男信女悄悄地来这座被毁的寺庙前顶礼膜拜,到了子时(半夜十一时至一时),从一块山崖上,可清晰地看到一个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的像,持续一二个小时,然后化为一片光明溶如更高的虚空夜色。据说,当地公安局长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后来他身着便装趁着夜色来这儿看个究竟,结果他也亲眼看到了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直至升空的像!打这以后,当地的公安人员、治安人员对前来进香拜佛的百姓不象过去那般气势汹汹了,也不再动不动就收缴信众的香烛供品了。
他上小学时,功课很好,在班级里不是当学习小组长就是当中队长。小学毕业读中学,读书成绩依然很好,老师仍叫他当班干部。初中毕业后考取县城高中,很多人都对他刮目相看,须知当地初中生能考上高中的至多十分之一呀。恢复高考后再考取大学,在当地就像从前乡里出了个秀才、举人似的引起哄动了。而他不仅考上了大学,还前后一共拿到三个大专文凭:除了他正式就读的全国某公安学院毕业文凭外,还有某大学中文系和某中外文化学院的函授毕业证书。
他从小立下志向,最想当的是警察、记者、医生这三种职业,而当他长大以后,这三种职业他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干过了,而且干得都很出色。拿看病来说,有些很重的病人,如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妇女、脚被车子碾伤几十年的老农等等,他念上几遍观音心咒,请诸佛菩萨一加持,疑难杂症马上就好了
他干得时间最长的,或者说,他的本职工作,是公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某市公安部门工作,至今已十多年了,前些年还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并且是单位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他的师傅是全国公安战线的劳动模范,其貌不扬而武艺高强,跟着他师傅追缉坏人,往往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可惜师傅的为人过于正直,这年头正直的人吃不开,所以一直没给提上去。
他一开始想当警察,是要作一个国家真理的捍卫者,作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这不能不说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等他真的干上了,干长了,理想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他就越干越不想干了。他觉得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恶的,犯罪,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很大,要减少犯罪,归根到底要靠改造社会。他认为佛法是改造社会最有效的手段。最好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对学生讲点佛法,提倡放生、发慈悲心。如果人人都能从小就遵守三皈、五戒、十善,那么这个国度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礼义之邦,社会秩序就必然会比现在好得多。
他曾三次离开单位想出家,每次都被找了回去。这一次,他来五明佛学院正式出了家,总算遂了自己的心愿。目前单位还没找到他。不过,即使找到他,也为时晚矣,他已正式剃度,不至于把他从出家人的行列里揪出去吧?
从年龙回到佛学院后,我去善宝师屋里坐坐,又跟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他的屋子建在学院东南面的半山坡上,面积不大,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他这人给人的印象一样:清清爽爽,明明朗朗。
他跟我谈起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庭。他的父亲,兄弟姐妹共有十六人,有的在国民党中统、军统中担任要职,有的参加共产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父亲曾是蒋介石侍卫团的成员,镇反时被打成“特务”,吃了很多苦头。后逃到马尔康,隐名埋姓,混口饭吃。在马尔康他父亲娶了他的母亲——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女,两人相依为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在马尔康生过四个孩子,前三个都饿死了。活下来的一个,前些年当兵去了。五十年代后期,他家回到汉地谋饭吃。母亲进了重庆的一家纺织厂当纺纱工,一个月才四块钱工资,她在厂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掉两块,还有两块拿回去养家糊口。
她母亲生他之前,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鱼塘,鱼塘很小,可是鱼塘里的一条鱼很大,在小小的鱼塘里呆不住,拼命要从鱼塘的浅水里跳出来
当我在善宝师干净简洁的小木屋里,听他敞开心扉,谈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经历时,就象是在听一个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故事,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虽然已经出了家,可在他的胸膛里,依然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火热的心
末了,善宝师说,一定要多放生,这是第一结累功德的。你看这儿的牛羊,你若对它们念经,它们的眼光会变得特别亲切。有一次,他跟别人说起,佛学院里的那只黑山羊,以前是个修行的老比丘,结果那只山羊马上拱到他怀里来,十分亲热
一位一起去年龙的女居士,见我跟善宝谈了好长时间,问我:他跟你说了吗?他小时候曾经全身变得透明?
我说我已听他说了。
“你知道吗?”女居士说,“这是硫璃身呀!是千载难得的菩萨身啊!”
十九、“武则天”转世
十九、“武则天”转世
直到我跟善宝师等人去年龙前,我同宝玲居士没打过交道。
不过,尽管没跟她有过任何交往,在佛学院那么多的觉母、尼姑中,她却给我留下过一点特殊的印象。那是有一次经过大经堂时,看到有一群觉母簇拥在一起谈论着什么,蓦地,觉母中有个身穿艳丽藏服的中年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单单是她那身蓝底色大花纹的衣服特别醒目,而是她脸上的一股贵族气息,使我觉得这女子有点与众不同。她的肤色也比较白嫩,看上去不像是个藏人。
后来偶尔听别人说起,才知这女子果然不是藏人,好象是从山西来的,有点神通,有人还称她是“空行母”呢。后来还听人说,她是达赖喇嘛的干女儿。她是否有神通,我没见过,反正到这儿来的人中,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谁多多少少有点神通并不令人奇怪。我觉得奇怪的是,达赖喇嘛早就跑到国外去了,这女子咋能认达赖为干爹呢?
这次去年龙,我才知道,原先我听错了,不是说她是“达赖喇嘛”的干女儿,而是说她认的干妈叫“达热拉母”——也就是久美彭措高僧的空行母,我把“达热拉母”错听成“达赖喇嘛”了。
在色达县城寻找去年龙的车子时,宝玲居士将她带在包里的两只百果月饼拿出来,切成扇形小块,分给大家吃。我接过她给我的一小块饼时,说了声谢谢。
“不用谢,”她说,“这是中秋月饼,请大家尝尝味道。”
今年的中秋已过去十天了,但在这连最普通的饼干、糖果都要靠内地运来的青藏高原上,月饼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大伙确实连月饼的味道都没闻到过呢。此时,还真用得着电视台播出频率最高的那句广告词:“味道好极了!”
由年龙返回色达的路上,因为车上风大,颠簸又厉害,大家很少说话。我跟宝玲居士坐得比较近,都坐在车厢中部,也没说话。高原天气说变就变。车子开出不久,天上突然下起冰雹来,打得卡车挡板叮当作响,落在车厢里的一粒粒小冰雹,弹性极好,蹦起来足有一尺多高。我打开随身携带的雨伞,为自己、也为坐我近旁的宝玲居士等人遮挡一下冰雹的袭击。冰雹不久就停了。我收了伞。当我跟宝玲居士的目光相遇时,她朝我微微一笑说,你的前世多少多少世,是什么什么你今世可以怎么怎么
听她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女子有点不简单。她说我前世如何如何,跟昨天善宝师对我所说,居然别无二致呢。
我问她,能看看我这几年的情况吗?
可以。她点点头,要我把一只手掌伸开,让她看看。她不像有的人看手相那样,又是生命线呀,又是事业线呀,要横看竖看看上好长一会儿时间,她只是稍许看了看,就把眼光移开了,无目的地望着空中,似乎要从空中找出答案来。慢慢地,她的脸上显出一点惊谔之色。
“嗯,这两年你怎么有一场十分奇特的经历?”她好象对她看出的这一结果也有点奇怪,随即作了一点说明。
她虽只是寥寥数语,却是不折不扣的一语中的。这位“空行母”的神通,果然名不虚传,令人佩服。从概率上说,你说一个人身体曾有点不舒服啊,事业上曾有点不顺利啊,多多少少,总能挂上点钩;可你若说谁有某种倒霉事,那恐怕是百里未必有一啊!而且,这种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话,若无相当把握,谁都不会随便说说的呀。
卡车依然颠簸在由年龙返回色达的简易公路上。公路两旁的草原渐渐变得开阔起来,有几群牦牛在吃草,离色达已不远了。我朝戒善师稍稍坐近一点,低声对他说:“宝玲居士果然不简单呢。”
“就是么,”善宝也低声对我说:“你没听说麽,她是武则天转世呀!她又是一个现世空行母,达热拉母很喜欢她,认她为干女儿,她身上那套漂亮的藏族服装就是她干妈送的。不过,她的命很苦,才四十来岁,丈夫就死了,留下了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最近也生病去世了……”
我忽然想起不久前圣普师对我说起过的武则天由婆罗门女转世的故事,当时还闪过一念,圣普师怎会一下子跟我谈起武则天的转世?现在看来,她倒不是无的放矢呢。
二十、山外人看山里人
二十、山外人看山里人
色达,这座高原小县城,它最高的民用建筑是去年建成的县邮电局,楼高三层,底层对外营业,二三层为办公室和电话总机房、电报房。在此之前,除了三十年前造的二层楼的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以及前两年临街新造的一幢二层楼房,县里再没有一座二层以上的房子了。
以一匹向上腾飞的骏马雕塑为中心,两条铺了没几年的水泥路成十字交叉,分布在水泥路两侧的总共几十家百货商店、食品商店、民族用品商店、杂货店、饮食店、新华书店、电影院、邮电局、集贸市场、长途汽车站等等,以及同十字路口保持或近或远距离的政府机构和稀稀疏疏散见于各处的民宅,便构成了这座高原小县城的主旋律。
全县人口不过三万几千,住在县城里的,大概不会超过二三千吧。
从早到晚,喏大的百货商店里冷冷清清,没几个顾客来买东西,而这儿的东西大部分比内地贵得多。
白天来往的卡车倒还有一些。色达出产木材,虽说老祖宗留下的原始森林已砍伐得所剩无多了,但总还能用砍下的大树换回一点当地所缺乏的日用品。
总有几条身强力壮的狗在街上溜达,它们的身材都比“托巴”高大得多,站起来恐怕比人还高,但在人前都很温和,不用害怕会不会趁你不注意时窜上来咬你一口。
色达电影院每晚放一场电影。我曾在这儿看过一部片子,那晚放的是《大汉恩仇》,票价二元,比规定时间拖了二十分钟开场,全部观众仅八个人,只怕连付电费的钱都没收回。
法王在洛若山里办起五明佛学院后,一开始尚不为外界所知,就连四川人也很少有谁知道。近几年,五明佛学院的名气一点点大起来,知道有色达这个地方的人也渐渐多起来。这为长期来相当落后闭塞的色达带来了一定的活力。县邮电局近几年收转的信件、汇款,几十倍几百倍地增加,于是才新盖了全县最高的邮电大楼。
近年法王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大法会,届时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的信众多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听说在色达也举行过大法会,那才是当地最盛大的节日呢,法会开始前和法会间隙都有涛涛人流涌进这座小县城,平日空空荡荡的街上人潮澎湃,商店里所有食品一售而空……我很想知道,住在色达县上的人们,尤其是县里的头儿脑儿们,是如何看待法王在洛若山中创办的这座为色达带来一定声誉的佛学院的。
我跟香根活佛说了,我想采访县里的几个头面人物,不知他能否陪我一起去?香根活佛曾当过多年县佛教协会主任,跟方方面面都很熟悉。在一个全民信佛的社会里,他这个“头衔”在民众中享有的声望,是汉地的任何“主任”、“主席”、“书记”之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活佛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