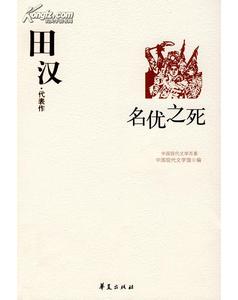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咳,可怜的作家呀!他只不过屈从于文学形式的规律罢了。谁能够把一阕黄钟宫声调的词曲,填成幽细缠绵的作品?谁能够使一首五言绝句,具有《楚辞·天问》般的磅礴与翻腾?谁能用散文追蹑整齐华美的姿采,一如骈文那样?谁敢突发奇想,用元曲写出《商颂》、《大诰》的风格?所以,形式不是工具,就文学作品来说,它是一切。文学,除了形式,还是形式。——最多,为了分析说明的方便,你可以划分成结构形式和意义形式。
由此,我们才可以知道,宣称打破形式的文学运动者,如果他的意思是要废弃球场,独自裸奔于旷野,那么,结果显然十分荒谬。因为文学脱离了形式就是死亡,一如围棋若无棋枰便不存在。形式,乃是文学美的根本要素。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人即曾企图以空间和数学来界定艺术,说音乐是一种有规律的音响,塑像的美是一种有规律的比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美,更是对称、比例,以及在统一的整体中各部分有组织的秩序。换句话说,美是什么?就是结构与形式。
这个“形式”,当然指的是客观审美对象的组织形式。但是,为什么对称、比例和统一,会使心灵感到愉快呢?难道不是因为它吻合了我们内在的理念吗?所以,叔本华就认为美的欣赏与艺术的天才,即是智力从欲念中得到解放,并且了解那些永恒的形式(即柏拉图所说的理型)。黑格尔也认为美就是变化的统一,是物质被形式所征服。至于克罗齐,更是极力宣称:形式就是心灵的活动和表现,而直觉的表现就是艺术。这么一来,形式又存在于内在审美主体中了。
这种形式既存在于审美客体又存在于审美主体的讨论,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昏眩。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形式既可以是结构的,也可以是内容的,一如我们在上文所说,便不会有疑惑了。
关键词
有意义的形式
英国著名美学家贝尔(Clive Bell,1881—1966)说:“美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他扬弃写实性绘画,崇尚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审美情感。他认为“美是线条与色彩的组合,此种组合需引起审美上的感受”,主张审美欣赏时亦不应受到创作者背景、信念、时代、社会等脉络的知识影响,而应就纯粹形式的趣味来玩味。此种极端形式主义,在20世纪初,将抽象绘画的地位大为提升,使绘画上的形式与内容分离成为两类不同的审美感受。
语言形式的符号作用
第九章 文学的形式与意义
文学作品的内容,即蕴藏在它的形式之中,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事了。但是,我们不禁又要接着追问:文学作品这种形式物,究竟传达或显示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以人来说,人的精神意态、思想内涵,皆存在于人的躯体言行之间;而我们勉强分析,却可以把有关意义生活的“情意我”、“德性我”,统称为这个人的内容内涵或存在的意义,把躯体言行的“形躯我”,称为人存在的形式。这也是一般的区分。可是,一旦我们开始追问“意义”时,我们的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我们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这其实也就是在问:人这种东西,究竟可以或应该具显、完成什么样的意义?确定了这个意义以后,个人存在的意义追求才有目标,才有依归。否则,空洞地谈某个人的内容或思想,均是无意义的。
这样解释,不知道读者是否会愈听愈糊涂,但是在一篇文学作品中,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明晰的。我们必须先确定文学作品所显示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才能观察某一篇文学作品跟这种意义相符的程度如何,是不是脱离了这一意义而岔入歧途。通过这种观察,我们也才有资格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和价值。
历来,不论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中,都存在着不少迷惘。依我们看,一切迷惘与错谬皆来自意义不明或失落,犹如不能确定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必将引发行为与价值取向上诸多狂悖和迷乱一样。因此,我们愿意在此谈谈。虽然我也跟每个传教士相同,不能确知所言是否即是真理,但说说总也无妨。
030。语言形式的符号作用
文学,无论如何,必须是语言、文字的构成。而语言、文字基本上是一套符号,是人这种符号的动物最擅长使用、也最重要的符号。
所谓“符号”,是一种东西,经过人类赋予意义的过程,用来代表另一件事物。所以,十字架、国旗、奖章、手势、硬币等,都可以是符号,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社会所界定的意义。语言、文字也是如此。
符号与它所指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天生而然,而是依照使用符号那个社群中人共同的规定。正因为它们之间不是实质的关联,是约定俗成,所以,人能利用符号去观察、去讨论世界上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至少在经验上不存在),例如鬼神、地狱、美丽等等,也会受符号的限制,观察不到实际上明显存在的事物。例如一群小学生去郊游,回来以后规定每人写一篇游记,结果,往往是每个人所能回忆的都只是老师平日在课堂上所讲的关于风景符号所指的东西,其他的则都过滤地排斥掉或根本不能“看到”。扩大来说,每个民族或社会的语言,也都因此而有它的局限,看不到自己符号系统以外的世界。
换言之,符号所构成的认识世界,很可能甚且必然不同于真实的世界。它的真实世界,就在符号系统所构筑的水晶宫里。它当然会跟客观真实世界有关联,但不必,也不可能企求它们相等。文学作品所建构的宇宙同样不存在于客观经验世界,而存在于符号所铺陈的场域,与经验世界并无必然的关系。所谓“本书人物,全属虚构,若有巧合,务祈原谅”,“虚构”二字,便是指它是从符号世界中长成筋骨,而非由现实社会获得血肉。
就此一特征而言,文学作品与符号逻辑所敷陈的演绎系统甚为类似。但,文学作品毕竟与一组瑰丽严密的形式逻辑不太一样。因为,文学作品又在其符号本质上加上了许多人为的形式特征,诸如格律、押韵、音质、文法、譬喻,以及其他一切微妙的形式,使它从形式上看就能辨别出是超离出寻常生活轨道之外,不属于经验事实的描述,而应听之以想象。
其原理,盖如李察兹所云:“韵律正是利用其人为面貌来产生至高的‘框架’效果,把诗的经验孤立于日常生活偶然与无关的事物之外。”它赋予艺术品一种特异的人为性质,使之有别于一切自然景象及事物,确保一篇艺术成品的“艺术性真实”,勿使之沦落分解到“事实之真”的层面去。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谨记:事实的真假,一如真人实事改编的小说,除了添加我们一些谈笑的趣味外,对小说的艺术价值、意义内容毫无增损。一篇有作者刻骨椎心、呕肺沥肝经历的诗歌,也很可能毫无文学价值,比不上某位作家书斋里的虚构。只有蠢到无以复加的人,才会相信世界上真的曾经有过一位林黛玉,而且,真的就住在大观园里。也只有患了某种狂热症的疯汉,才会醉心于高呼“社会写实是真正的文学”。
其实,文学作品的真只存在于文字形式中。所谓“至情至性”,只能由文字中见到,与作者无甚关系。因此,我们若被一首诗所感动,便会终身记得这首诗的文字,除非写文章时需要,我们往往不大会去查考作者是谁。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意味着文学所成就的,只是一种形式的知识呢?
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我只能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勉强写下:一般说来,形式的知识自以科学为典型。普通人谈到科学,便以为它是归纳实证的功夫,实则并不如此。科学中,形式科学纯粹处理符号架构,与实际世界无所对应,它只是一套依据一致的标准严格演绎的符号系统。至于事实科学方面,表面上似乎必须与客观事实对应,然而,事实上绝无任何科学系统能直接对应于现实。它们大多是人类在观察自然之后,选取几个据点作为前提,然后根据演绎技巧所导出的一些系统罢了。这些系统虽若吻合现实客观世界的相貌,却不完全恒等,所以,本质上它仍是形式的知识。
这种科学知识与艺术最大的分野,在于艺术考虑“人”的问题,科学则不。所谓人,至少是创作者自己。每件艺术成品,都多少带有些创作者本人的印记。许多人去仿造张大千、达·芬奇、溥心畲、石涛的画,许多人去假冒李白的诗,却不会有谁梦想伪造一项新发现,说是爱因斯坦的发明。仅此一端,便足以证明:艺术无不涉及人的存在。
这种涉及人的存在的知识,乃是比科学更为根本的。何以见得呢?科学家定要不服气了。
形式的来源与终极(1)
031。形式的来源与终极
其实也不必冒火。科学是一种形式推演的知识,但请问:形式的来源何在?其终极又何在?这两个问题,皆非科学所能回答的,非诉诸一非形式物不可。这非形式物,我们即称之为“存在”。
面对存在,有些人懔于存在的不易表达,不得不舍弃存在这一观念,存而不论,而只专心于纯形式的表达。有些人则借形式来逼近存在。前者当然可以完成一项科学知识。后者以形式作为存在表达的工具,却会有一些无法豁免的问题,因为,形式毕竟是无法表达存在的。
既是这样,我们就有几点可谈了:
(1)文学与艺术的表达,基本上都采取借形式来逼近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如前所述,实不足以表达存在的整体真实。故而,文学家,只要他具有深刻的存在感知与形式觉察,大多会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必须仰赖、借助、驱遣文字,以构筑文学的宇宙;另一方面,他又对语言文字不能信任,并感到有通过语言文字无法窥知存在的怅惘。
这即是“言不尽意”或“意不可言传”的困境。陈简斋《春日》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2)正因为有此困局,逼使文学家采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方法。这种形式表达异于科学的形式表达处,在于它是以遮诠、迂曲、歧义、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一般说来,凡注重形式方法表达的知识,都与矛盾的辩证密不可分;但这种异乎科学形式知识的表达,在处理矛盾问题时,不是以一种寓言或象征的方式,便是以形而上的统合或超越,不像逻辑那样,从事于形式的分析关系的无限展开。故其表达存在仍是一种言而不尽,且又不尽言以表物的象征表现。借着这样的方式,它消解了逻辑概念语言的执著和限定,表现了整体存有的无限性。
以诗为例。我们通常都说诗的创作形式有赋、比、兴三种,其中除了赋是直陈其事,比较接近逻辑与概念语言之外,比与兴都借迂曲的譬况或象征超越了指涉物,跨入另一个层面去了。尤其是兴,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超越了语言的局限与鸿沟,伸展到形式知识所无法触及的领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奇妙处。古来讲哲学的人,讲到最后,即不得不出之以诗的语言,原因也正在此。试看禅宗的公案机锋、偈颂,道家的老子庄子,乃至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等,不是充满文学意味,根本就是最精彩的文学。理由无他,正在于文学的表达方式较能趋近生命存在的真实啊!
(3)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文学或艺术的意义,即在于它能展现人生整体存在的关切。它不是纯粹的形式知识,所以,它也不必符合形式知识的要求与功能。形式知识的庄严,在乎形式概念间的严格关系限定。文学艺术则是对生命严格。其严格,表现在自我存在的价值或抉择的限定上。这就是文学意义的所在。
一切文学创作及活动,当看它能否符合这个意义。能,就有价值;不能,便是缺陷。所以,站在这个标杆下,我们也不妨执此以为权衡,估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
由于文学作品是这么努力地想彰显人存在的价值,所以它才能突破形式的平面世界,不断提升、抉择或信持其存在价值,建构一个立体的世界。它使人生有所企慕、有所仰望;通过文学,可以构成生命的自我追求与上扬。文学若有功能,功能殆即在此。通过美学的想象,人自然会有趋向真正终极理想的力量,超越现实,观看自我,并冲破人与人之间形躯时空等形式的限制,在人的存在处取得感通。
形式的来源与终极(2)
(4)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或艺术,本质上都是超越现实的。它绝不是单纯的时代反映品,更不能视为社会运动的工具。
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许多疑惑,甚至会招来严苛的攻讦。然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真是那么牢不可破?每一个头脑还长在脖子上的人,都有责任重新思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人类大部分的争论和坚持,都来自语词含义的紊乱。所谓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亦然。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人的生命及更大的普遍生命”吗?是指“人生”吗?是指政治状况吗?……历史上,像法国美学家居友(Guyau)所主张的社会学的美学,其所谓社会就是指群体的生命。托尔斯泰所强调的现实社会文学,用意也只是指人类的活动,诸如社会的傲慢、肉欲、生之倦怠,等等。至于王安石所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则显然是就政治这一方面立说。历史上由于名词含义不同而引起的文学论争已经太多了。我们讨论这一问题,自然首先应对它稍予界定,才不会引起混淆。
我们所谓的社会,含义等于现实人所生活的时空场域和事件。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超乎现实的,可能第一个就会激起“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信徒的反感。但是,一般泛泛使用这句名言时,说话者未必清楚什么叫做“反映”。
反映,必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