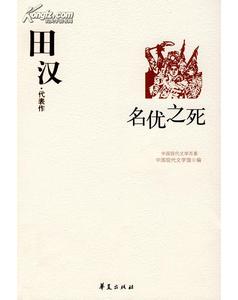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缩短,咫尺之隔亦可以邈如山河,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因此,时空,是小说美学的基本架构。脱离了时空,一切都甭谈了。
(1)小说里的时间
在小说里的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三种:一是表面时间(physical time),指小说本身的时间变化,例如现在、过去、未来的穿插,现实与幻境的交叉呈现,倒叙,等等。二是心理时间(psychological time),指读者在观赏小说时所感受到的主观及情感的时间,像小说中悬疑的安排、韵律与节奏的设计,都会影响到读者心理时间的构成。三是戏剧时间(dramatic time),指小说中故事情节整个前前后后所发生的时间及其篇幅,有些小说描述“一天”的事迹,有些写“廿年”,其戏剧时间便不相同。同时,早期小说与戏剧关系甚为密切,而戏剧的演出必受时间的限制,说唱小说亦然。这种戏剧时间,自然也会影响到小说时间上的设计。
以上这三种时间,例如《西游补》,全书的戏剧时间很短,篇幅也不长,只是叙述孙悟空在借得芭蕉扇,扇灭火焰山之火以后,一次化缘途中的一场春梦罢了。一梦乍入,忽然而寤,其表面时间,则运用现实与幻境交错、融入的方法来展现。而读者因这种迷离恍惚,陷在悟空无法冲出鲭(情)鱼障的危机里,乃感到心理时间特长。这就是一篇时间安排得非常妥善的小说。反观金庸则不然,像他的《神雕侠侣》,往往因为在心理时间和戏剧时间方面配合不佳而失败。例如,杨过在古墓中遭李莫愁师徒追杀,千钧一发,系生死于俄顷,而作者写来,竟不能有逼人窒息的紧张感。同时,小说叙述小龙女危急时,杨过牢牢抱住李莫愁后腰以防她杀害小龙女,而李莫愁一生未亲近过男人,陡然间被抱住,“但觉一股男子热气从背脊传到心里,荡心动魄,不由得全身酸软,满脸通红,心神俱醉,快美难言,竟然不想挣扎”(第六回)。须知李莫愁初遇杨过时,“十多年前是个美貌温柔的好女子”,则此时年已在三四十之间,会被一位十五六岁少年抱住而心生绮念,已是匪夷所思。即使姑且承认有此可能,则杨过能让一位三十多岁老女人感到有“男人”气息,应该看起来不再像个小孩子了。却又不然,十三回写杨过力斗金轮法王及其门徒,一直都以“孩子”称呼杨过,甚至说他是“顽童”、顽皮的“小畜生”。但此顽童比在古墓抱住李莫愁时可又大了许多。这分明是作者在小说时间构成上的疏漏,无法取信于读者。而更严重的,则是小说人物没有成长。
康洛甫(Manuel Komroff)的《长篇小说作法研究》中曾提到:小说亦如人生,无法逃离时间之流,小说中每一个人,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就都长大了一天。他称这种时间为“小说钟”,每个人物在说话时,时钟都在滴答着。——可惜这一点常被小说家们忘记,就像我们除非特别去留意,否则总是听不到时钟的滴答声一样。
(2)独特的小说钟
话虽如此,每个小说家对时间的理解与处理并不相同,他们安装在小说里的钟形形色色,各异其趣。例如西方小说所注重的“情节”,就是根据直线式的时间观念,构成事件的因果关系(causality)。因此,小说中情节的悬疑和进度,即来自对时间推移的悬宕,而形成美感。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小说面面观》说得好:“美感是小说家无心以求却必须臻及的东西,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始,但不能以缺少‘美’终。不美的小说就是失败的小说。关于美……我们得先将它视为情节的一部分。”(第五章)
反之,中国传统的小说,在与西方小说对照之下,显得几乎没有情节可言,或者只是一种“拼凑的、缀段性的情节”(heterogeneous and episodic quality of plot)。它的结构方式不是有机的、统一的,经常有偶然的状况发生,也常有“此处暂且按下不表”、“话分两头”及章回缀段的情形。这些情形,一向都被解释为宋元说书惯例所留下来的遗迹。但事实上,我国所有叙事文类,如史、传、传奇、白话短篇小说,都和长篇一样,有这样的“缀段性”。因此,这应该与作家所习惯的观物方式有关,而非仅属说话人的遗习。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曾经提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轮即列于五方之旁罗盘。”(《藏智于物》)这充分显示了重视时空综合呈现、强调时空相互依存的特色,至于四季轮转、五方分列,更是把局限性的时空伸展成无限的广大相关性时空了。希腊欧氏几何,是局限于有限时空的世界观;文艺复兴以后,坐标几何出现,欧洲才从“封闭世界进入无限宇宙”。但牛顿的物理学,依然是时空明确独立的并举,整个是机械式的,到了爱因斯坦,才注重时空的连续与交错。换言之,因果律为传统西方思想的特质之一,它视每一事物都是包含在一个以因果为环的机械锁链中,而只有在这种观念底下,紧密而集中的情节结构才有可能成立。因为在这既是直线式而基本上又是时间性的结构中,人物或事件被选为叙事中的“原动力”(prime mover),或活动而含有顺序性的要素。相反地,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由于注重时空综合呈现,强调时空相互依存及交错流转的关系,因果关系中的时间秩序便被空间化了,成为广大、交织、网状的关系,展现出并列的具体“偶发事件”(incidents)的有机形式。故在小说里,小说家很少选择一个人物或事件来统合整部作品。它们经常是东拉西扯,让这一个或那一个人物、这一桩那一桩偶发事件浮现在叙事的主要脉络上。小说人物的出场、相遇、退场、再出场几乎都是随意的,仿佛全为机遇和巧合所支配,但一切偶然,却一定符合“时命”——这个“时”,就是中国小说中惯见的小说钟。看不懂这个钟,便解不开中国小说的奥秘,更无从体会其美感了。
时间与空间(2)
(3)小说的空间
小说并无如现实人生般实际的空间,一切空间及空间感,都是由文字在纸面上构成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的空间可以随意变换,不像现实的空间那样固定不可移。这是小说胜于实际人生的地方。
可是相反地,由于叙述观点的运用,小说中事实上只表现出一种空间及空间关系。与现实世界里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不同的空间不同,这又是小说不如现实人生的地方。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方便,便于小说情节的构成及叙事的集中。
这种空间,也不同于戏剧。小说与戏剧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看戏时,观众好像是站在窗子外面往里头看,只能看到舞台上限定空间内演员们的戏剧动作。小说就不然了,由于小说的叙事观点自由,空间的伸缩性非常大,而且可以制造出景深,提供给读者想象性空间的幅度,一般说来要较戏剧为大。
这是小说空间的基本性质。然而,什么是小说的空间呢?在纸面上如何构筑空间,并带给读者空间感?
首先我们应了解:空间感(space)不是地方感(place),也不是“背景”。仅仅有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地点、历史背景,不能构成小说的空间。空间感是深入到小说本质的东西,小说中一切情节与人物,都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才具有了生命。例如《战争与和平》中,一切人物与事件得以发生的辽阔的俄国领土,事实上是包含了桥梁、冰封的河川、森林、道路、花园及田野,等等,而整个浮现在小说里,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特殊的气氛,而小说里的人物与事件就活在这个氛围里。其他,像《红楼梦》的大观园、《水浒传》的梁山泊及北宋末年的社会、《三国演义》的分崩离析大时代,等等,人物都是从这个空间里“生长”出来的。我们不能想象脱离了这个空间,其人物与事件还能发生。这才是成功的空间。
地方感则不然。作者借其旁白来“描写”一个地方,说明该事件发生在某地,但这个地方的地方色彩、语言、风俗习惯,虽然经过作者极力刻画,却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一种“先验的形式”的感觉。譬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写大漠、写江南、写京城,虽然用了很多的笔墨去渲染,涂饰该地域的特殊风物及景观,但基本上它并不能让读者感觉到这儿是塞北绝漠,那儿是江南烟景,其人物亦不一定要与那个空间紧紧抱在一块儿,所以它就丧失了空间感。
背景感,则是交代时代的地理背景,但小说本身的人物都可以自行活动,跟背后的布景并无太大关系。如《神雕侠侣》之类,时空场景不过是个幌子,与小说的关系不大,充其量也只是舞台上的布景,使小说看起来不全然是“虚构”而已,使读者产生一些“拟真”的幻觉效果而已。
由此看来,空间虽然是小说先验的形式,是小说的美学基础,可是却不是容易达到的。以金庸《天龙八部》来说,它的时间是北宋,空间则南起大理,北达辽金,西有西夏,南有姑苏燕子坞(燕),中间是大宋。这是一个大时代、大空间,仿佛《三国演义》的格局。书中分成三条主线来发展(段誉、萧峰、虚竹),亦如三国之分为魏、蜀、吴。但整部小说写下来,却只是段誉儿女情长、萧峰英雄气短,其空间功能完全不显。这充分证明了小说空间处理之难。小说不能具体地去描写空间,因为,一旦我们把空间当做具体的事物去描摹、刻画,空间就不是空间了。康德说过:“空间只是一切外感官之现象的形式,是感性的主观条件。只有在感性这种主观条件之下,外部直观对我们才是可能的。”它是先验的、直观的,它规定了对象的关系,不能以经验现象去规范它。有些小说——例如古龙——凛于空间的难于表达,遂干脆抽离了时空,意在投机取巧。殊不知这么一来,小说便整个垮了,情节不合理,人物不合理,事件也不合理。
这并不是说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时代背景,因为那是背景的问题,而不是空间的问题。小说可以与任何历史时间无关,不必有现实时间与之呼应,但其空间感自然存在,没有这个空间,小说就不能架构起来。
(4)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
不过,由于空间不能从外部现象的关系里根据经验获得,刚好也显示了经验理解的现象,其本身是在空间中所无法察知的。譬如一枝玫瑰,其本身就是“物自身”,而“在空间中直观到的全都不是物自身”。同理,“如果时间是附属于事物自身的规定或秩序,那么它就不能先于对象,作为对象的条件,从而借助于综合命题先验地被认识和直观了”。
这就变成了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永不接头的局面了。小说家即使描述了他的感觉与经验,但在他自己的现实时空里,既不可能察见物自身,小说的时空关系,又与现实时空不同,则小说中出现的玫瑰,离物自身当然就更遥远了。这种距离,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小说与“真实”的距离。
而小说要怎样才能逼近真实呢?首先它必须将小说里的时间空间瓦解掉,然后再经由这种时空的瓦解,暗示或象征现实时空也是虚幻的,借此“遮诠”地显露人生的真实,指出在有限时空之外,还有无限时空的存在。
例如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邯郸记》及《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其主旨本来就在揭示小说中时空场景里所发生的种种事相都是虚幻的,甚至其时空也是诡谲不真实的。黄粱梦醒,而老人之炊黄粱犹未熟也。经由这种揭明,读者顿然惊寤:原来一切悲欢离合或生老病卒,都是“以上皆非”的。这不是人生若梦,而根本就是人生即梦。
换言之,小说中存在着二重时空关系:一是黄粱梦中的虚幻时空,一是邯郸旅舍里令人悟真的时空。
藉着这两层时空的对照,让人领悟到有限时空的虚妄性,而即在邯郸旅舍那种现实人生的时空里,知道了无限时空的奥妙与人生的真实。小说中,梦与神话的展现,作用经常是如此,它犹如绘画中的虚、空白,可以使人由有限起悟,接触到无限的时空。我们应该要了解,中国画的空白,不是“留白”而已,不是画上山水实景而留下一角空白,让人若有若无地去品味,而是——根本是在空白处,偶尔只画一山一水。空白本为无限,在无限之中,唯画一山一水,以使人由有限通往无限。不画满,才能保有这种无限空间的性格,故书法、篆刻中皆有“计白以当黑”的说法,因为它真正要处理的不是线条及图像,而是空间。
这个无限时空,才是使有限时空可能的基础,也是人生真正的趋向所在。小说至此,已非纯属艺术,而逼近“道”的领域,能使读者由此悟道。中国文学中此类倾向特别明显,可能也是由于哲学上对此特别重视的缘故。
结构与图式
3。结构与图式
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美学基础,是结构与图式(pattern)。
小说的图式,既表现在依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故事上,也表现在有关人物因果关系的情节上,而形成小说的美感。在小说里,情节诉诸我们的智慧,因为它是小说的逻辑面;图式则诉诸我们的美感,构成叙事脉动的线条,起伏有致。
这种图式,跟作者所要创造的气氛应该适当地配合,使小说中散乱的人物与事件,可以以一条他们自己血肉编织而成的线串联起来。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里,这位小说家及评论者说道:
图式是小说的美学面。虽然小说中任何东西(人物、语言、景物)都能有助于美感的呈现,但美感的主要滋养物还是情节,情节可以自生美感……此处所谓的图式面与情节紧密相结,它生自情节——美感有时就是一篇小说的形式、一本书的整体观、一种连贯统一性。
事实上,图式并不仅仅产生于情节,它是小说整个叙事架构所形成的一种图式。福斯特为我们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