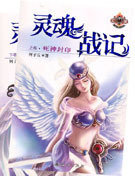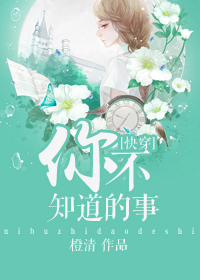灵魂的事-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当然不是说,我就相信人不如猪好,进而去发“当人不如当猪”的牢骚。我只是说,人之复杂的欲念,乃由上帝之复杂的嗜好所牢动,绝非人的自以为足够复杂的智力可以全知,别以为有什么伟大的公式、主义或旗手,可以令其交出全部秘密。老子——我以为那是他在表扬人的时候——说:知不知为上。浪漫些想:若在天国的动物园,有一栏叫作人的生物展出,诸神会否送给他们一个俗称呢?如果送,料必就是这“知不知”,相仿于麋鹿的俗称是“四不像”。
但是,听“知不知”们讨论起随便什么问题(比如文学)来,你又会觉得,单此一个“知不知”远不够概括这一物种的特点,完全有必要在(王朔先生已经留意到的)写有“动物凶猛”的地方,换上尼采先生的发现:权力意志。确实,其凶猛盖由于此。因为,你慢慢听吧,那里面常常只有一句话:(文学,或者随便什么)当如此,不当如彼,如此者当助其昌隆,如彼者则莫如早早厄其于摇篮。当然,人有这样自由地思想与表达的权利,但幸好止于权利,倘变成权力呢?尤其要是在灿烂的旗帜上飘舞呢?
这样的时候,我就更加地相信了: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以及这样一种警醒多么有益于心情的健康。
文思之不同,恰如命运之大异,怎么能把它们捆到一条路上去呢?你比上帝高明吗?潇洒一生的人看不懂坎坷一世的心,屡屡遭殃的命进入不了好运频逢者的联翩妙想,人之间有着无形的永固的墙。人们都是在一条条无形且永固的巷子里走,大多时候,其情其思隔墙隔巷老死难相往来。世界真大,墙与巷多到不可计数。世界其实小,谁若能摸住三五面墙走进三五条巷也就不坏。这世界真是很糟糕吗?但上帝造它时,看这是好的,才这样成了。上帝却让通天塔不成,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寓言:人的思路一旦统一,人就要变成魔鬼手中的小机器了。这大约,不,这肯定是上帝与魔鬼的一次赌博:上帝说他创造的是一场无穷无尽、美不胜收的舞蹈;魔鬼说不,你等着看我怎么把他们变成一群呆头呆脑、丑不堪言的小玩偶吧。
7
有两件似乎很大的事,我百思而终未得到哪怕稍稍可以满意的回答。
其一:人应该更崇尚理性呢,还是更尊重激情?(最勇敢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呵,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最好是鱼与熊掌兼得——但这不是回答。理性之为理性,就因为它要限制激情,继而得寸进尺还会损害激情、磨灭激情。激情之为激情,就因为它要冲破理性,随之贪得无厌还要轻蔑理性甚至失去理性。(山楂树下统共这么两位可爱的青年,你到底要哪一个?)但是你抛弃哪一个似乎都不可能,首先(姑娘呵)你忧郁地想念(他)它们,这就是激情;其次,你犹豫不决地选择,这就是理性。是呀,没有激情,人原地不动地成了泥胎,连理性也无从发展;丧失理性,人满山遍野地跑成兽类,连激情的美妙也不能发现、不能享受。这便如何是好?我想:姑娘她这么苦着,真是理性的罪行,否则她闭上眼睛去山楂树下摸一个回来,岂不省事?我又想:姑娘她这么苦着,实乃激情的作恶,否则她颈上套一串珠子远远地躲开山楂树,不就了结?或者我还想:这完全是那两个青年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坚具理性慨然告退,而另一个饱富激情冲过来把姑娘抱回家去!——但这无论是对姑娘,对两个青年,还是对我自己,都像似什么也没回答。
其二:人应该保留欲望呢,还是应该灭断欲望?不要欲望,亿万泥胎实际就已经掉进魔鬼的陷井。甚至比这还要糟。鸟不叫云不飞,风不动心不摇,恶行灭尽善念不生,没有欲望则万物难存,甚至宇宙也不再膨胀,那是什么?有一种说法:那是一种凡夫俗子无从想见的美妙世界。——但是,这已经动了欲望,不过更为奢侈些罢了。看来还是得大大方方地保留欲望。可是,欲望不见得是一种甘于保留的东西,欲望之为欲望,注定它要无止境地扩展。但是,看看河流已经让它弄成了什么吧,看看草原、森林、海洋、土地和空气……都让它作践成了什么,地球千疮百孔空乏暗淡已经快被榨干了!那么,保留欲望同时限制欲望,如何?呵,这是不是又回到“其一”的逻辑里去了?限制的边界划到哪儿,划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就是说欲望,应该到什么地方停下,什么时候截止呢?止以后呢,咱们干嘛?咱们可不是一群傻瓜,能把一件玩具来回来去玩上一辈子。咱们总是要看看边界(不管什么边界)之外的奇妙。看看就够了?不行,还要拿来。拿来就够了?不行,我们总是看见边界就总是想越过边界。有人说:远游或探险,与窃盼外遇同出一源。又有俗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真是真是,谁会爱一个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欲的呆子呢?呆子不坏但不可爱,聪明的家伙可爱但可能坏,女人们的这份难处很像上帝的难处:把地球给泥胎去作花园呢,还是请欲望横生的人们去把它变成垃圾站?
8
我以为我终于听懂了人性恶。
说“人之初性本善”,恶行都是后天土壤的教唆,这很像是说种瓜得豆,种豆得海洛因。人性恶,当然也并非是说人这种坏东西只配铲除,而是说人性中原就埋着险恶。
还说“权力意志”吧。陈鼓应先生宁可把它译为“冲创意志”,认为尼采的本意是指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世俗的权力,并引了尼采的原话,证明他是蔑视权势的。而章国锋先生相信还是“权力意志”译得正确,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法遏止的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欲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说“事实上,尼采所说的权力不仅指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权力,即在精神上压倒、征服别人,从而取得控制,支配,统治别人的权力。”尼采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当是专家的讨论,我没有资格作判断。但我注意到了章国锋先生的这一句话:“维持生存、追求发展和渴求控制异体是权力意志的两种本质。”我倾向这句话。于是想到:我们赞美梦想,崇尚创造,同时提防欲望,但梦想、创造和欲望实为一母同胞。我虽然相信尼采的原意是要鼓动人的创造与超越,但“冲创”的本性中肯定携带了“权势”的基因。
记得诗人西川有一首诗,写笼中之豹的美丽生动,我已记不住原句,但我记住了那很像是人性的注脚与警示:绚耀的皮毛,浪动的脚步,警敏的眸光贮满勃勃生气,但是别忘了铁栏——千万别忽略它。唉,我们如何走去那美丽与生动呢?要么把它关进笼中,要么把自己关进笼中,走近它,中间隔着铁栏,去看它,赞美它和倾向它。否则,我们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好去作杀手。
战争的概念,绝不限于刀枪与火药、导弹与核武器——比这悠久并长命的战争是精神的歧视、心灵的戗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个“我”,即这类战争的受害者与继承人。本世纪末,有“话语霸权”的消息传来,有新一轮的反抗热情兴起,但慢慢听去,都还是来自“控制异体”的古老恨怨。
爱情问题(6)
9
于是我又碰见一件想不大懂的大事——“价值相对主义”。
是呀,如果价值真理是绝对的、独尊的,它一向都应该由谁来审查和发布呢?霸主的宝座虚位以待,众人有幸可以撞上一位贤哲,倘事不凑巧,岂不又在魔鬼掌中?何况——“价值相对主义”说——真理压根儿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或时过境迁,或入乡随俗,绝难以一盖全。譬如:西方有西方的价值理想,东方有东方的传统信念,凭什么要由你或者他说了算?可是我却总也想不明白:西方是谁?东方又是谁呢?西方有很多国度有若干亿人,东方也有很多民族有若干亿人,一国又有若干省,一省又有若干市、县……如此仔细地“相对”下去,只好是每人一面旗,各行其是去吧。
我有时觉得应该赞成这样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本来就是别人管不了的事。每个人有每个人惬意的活法,本来就不该遭受谁的干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虽可能有失恋的苦果,但绝不容忍谁来包办一份“甜食”。但我又想,这肯定行不得长久。孤独的旗上早晚还要飘起沟通的渴望,便是玄奥的禅语,不也还是希望俗众悟出其公案的含意?各行其是的人们呢,终于还会像最初那样谋求协作,但协作必要有规则,而规则的建立能不赖于价值的共识?
人呀,这可是在上帝的园中跳那永恒的舞蹈呢?还是中了魔鬼的符咒,在宇宙中这块弹丸之地疯牛一样地走圈儿?
10
大事很多,愚钝如我者,没弄懂的、弄不懂的、以及没弄懂而自以为弄懂了的大事就更多。但按“排行榜”的惯例,以十为限。那就把最后的机会用以说明:在各种大事上,我是乐得让别人开导一番乃至教训一顿的。当然这不意味着盲从,在没听懂别人的意思之前,我还得保留自己的糊涂,总也听不懂呢,就只好愚顽不化——这像是没有第二种逻辑可供替换的事。跟好多人一样,我是想说话的,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也想听别人的话,甚至想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我很可能既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又是一个“非价值相对主义者”。比如:爱情,这件事我固执己见,不听外人劝告,我相信劝告者并没有弄懂我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他就不会劝告。再比如:还是爱情,这件事你又不能一意孤行,必得听懂对方的意思,倘对方说“请你走开”,而你偏闭目自语“这不是我的习惯”,岂不是要把一番好意弄成了性骚扰?是呀,爱情,真是妙,这是你个人的不容干涉的梦想,但其中又必要有一个他者,他者的必要恰说明对话的必要,否则爱情倒又是为哪般?看过许纪霖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但记得其中有“独白,还是对话”之句。于是想:在爱情中正如在人世间,便是独白,也仍是对话的结果与继续。
所以我知道,沟通是我至死的欲望,虽然它总在梦想之域跋涉。所以,我又知道:永存梦想的人间,比全是现实的世界,更能让我坦然对死——这就像你在告别故乡的时候,是仍然怀念她,还是已经不想再来。
1996年9月7日
灵魂的重量(1)
一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该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若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此既不是,什么才是?这什么,便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
二 存在,并不单指有形之物,无形的思绪也是,甚至更是。有形之物尚可因其未被发现而沉寂千古,无形的思绪——比如对意义的描画——却一向喧嚣、确凿,与你同在。当然,生命中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思绪和喧嚣,永远都没有,比如狗。狗也可能有吗?那就比如昆虫。昆虫也未必没有吗?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三 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一,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二,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死亡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四 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建立意义,或对意义的怀疑,乃一事之两面,但不管哪面,都是人所独具。动物或昆虫是不屑这类问题的,凡无此问题的种类方可放心大胆地宣布生命的无意义。不过它们一旦这样宣布,事情就又有些麻烦,它们很可能就此成精成怪,也要陷入意义的纠缠了。你看传说中的精怪,哪一位不是学着人的模样在为生命寻找意义?比如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比如猪八戒的梦断高老庄。
五 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六 不过,精神和灵魂就肯定是一码事吗?那你听听这句话:“我看我这个人也并不怎么样。”——这话什么意思?谁看谁不怎么样?还是精神的我看肉身的我吗?那就不对了,“不怎么样”绝不是指身体不好,而“我这个人”则明显是就精神而言,简单说就是:我对我的精神不满意。那么,又是哪一个我不满意这个精神的我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我,不仅高于(大于)肉身的我并且也高于(大于)精神的我,从而可以对我施以全面的督察呢?是灵魂。
七 但什么是灵魂呢?精神不同于肉身,这话就算你说对了,但灵魂不同于精神,你倒是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不是胡说?
因为,还有一句话也值得琢磨:“我要使我的灵魂更加清洁。”这话说得通吧?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