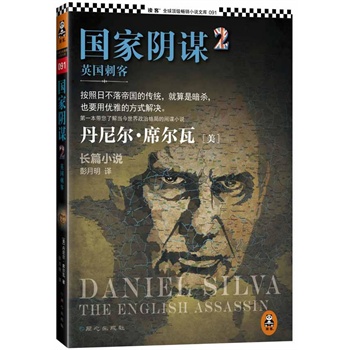袋鼠 [英国]劳伦斯-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个傻子。”理查德·洛瓦特说,他最经常的发现就是这个。每有一次发现,他都会感到更大的惊诧与懊丧。他每爬上一座新的山头俯瞰山下,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界,还看到一个充满期盼的傻子,那就是他自己.
而小说被认为仅仅是情感冒险的记录,在感情中挣扎的记录。我们坚持说,一部小说亦是或亦应该是思想的冒险,如果它要成为什么完整之物。
“我真傻,”理查德自忖,“居然幻想着能在一个毫无同情心的世界里挣扎,岂不等于说苍蝇能在药膏中生存一样?”我们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药膏,但没想到苍蝇。它掉进药膏里了,叫着:“哈,这里有一种纯粹的香脂,里面全是好东西。这里有一种玫瑰油,里面一根刺都没有。”这就是药膏中的苍蝇,被香脂浸着。我们感到恶心。
“我是个傻子,”理查德自语道,“竟然在这个处处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的友好世界里东游西晃着。我感到像药膏中的一只苍蝇。看在老天的分上,让我摆脱吧,我快窒息了。”
可去哪儿呢?如果你要摆脱出去,你必须出去后有所依附才行。
窒息在无害的人类那油腻腻的同情之中。
“啊,”窒息中的理查德叫道,“我磐石般的主心骨呢?”
他很清楚它一直的所在,就在他的心中。
“让我回到我的自我吧,”他喘息道,“回到那个坚硬的中心。
我要淹死在这种无害物的混合里了,淹死在富有同情心的人类之中了。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让我爬出这种同情的污泥,把自己洗刷干净吧。”
回到他自己的中心,回去,回归。这种蜷缩是不可避免的。
“一切,”理查德自言自语道,这种无尽的自我对话是他最主要的乐趣所在,“一切都是相对的。”
说着他跳进松油罐中。
“并不尽然,”他爬出来时喘息道,“把我孤独绝对的个性自我拽出这乱麻团吧。”
这就是相对论的历史。当我们跳进药膏或糖浆或火焰中时,一切都是相对的。可一旦我们爬出来了,或带着焦糊味跳出来了,“绝对”就从此攫住了我们。哦,孤独,绝对吧,那样可以喘得过气来。
这样看来,即使是相对论也是相对的,与绝对形成相对。
我在药膏罐子边沿上站着用嘴巴梳理我的翅膀,这副样子挺悲惨的,理查德自忖。不过,趁着站在这个高度的时候,让我给自己布道吧。他布道了,布道的记录就成了小说。
木,自我是绝对的。它或许是宇宙中其他一切的相对物。但对它自己来说,它是一个绝对物。
回归中心的自我,回归那孤独绝对的自我吧。
“现在,”理查德满足地挥手自喃,“我必须招呼所有的人回归他们中心的孤独自我。”于是,他挺直身体,越过药膏罐子的边沿,再次进入人类的香脂中。
“哦,主啊,我几乎又干了一回。”他心中作呕地爬出来时这样想道,“我还会经常这样做。人类的大多数都还没有什么中心的自我,什么都没有。他们都是些碎片。”
只有他心中的恐怖能让他袒露这种心声。于是他安静地趴着,像一只爬得精疲力竭的苍蝇,趴在药膏外思索着。
“人类的大多数都还没有什么中心的自我,他们都是些碎片。”
他知道这是实情,而且他对人类福音这香甜的香脂味道腻透了,他几乎沉溺其中。
“多少层微小的眼面才能构成一只苍蝇或一个蜘蛛的眼睛?”他自问,其实他在科学上糊涂得很,“哦,这些人只是小眼面儿,只是碎片,只配给整体凑数儿。你尽可以一次次将它们拼凑起来,可就是无法赋予这臭虫以生命。”
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碎片,即使孤立其中某块碎片,它还仍然只是碎片而已。孤立的普通人,他不过是一个最基本的碎片而已。假设你的小脚趾头不幸被砍掉了,它不会立即立起来声明说:“我是一个有着不朽灵魂的孤独个人。”它不会这样的。但普通人则会这样。他是个骗子。他只是一块碎片,只分享一丁点集体的灵魂。自己的魂呢,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仅仅是集体灵魂的一丁点,再没有别的。从来不是他自己。
去他的吧,普通人,索默斯这样对自己说。去他的集体灵魂,不过是洞中的死老鼠罢了。让人类抓挠自身的虱子吧!
现在,我又要呼唤自己祈祷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阿拉,真主啊!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各自有其灵魂。人人忠于自己。人人回归自我!独自,独自,独自守着自己的灵魂。上帝是上帝,人是人,普通人则是虱子。”
无论你与什么相对,这既是你的起点,亦是你的终点:一个人守着自己的灵魂,黑暗之神在远处与你相伴。
独善其身的人。
开始吧。
让那些普通人──荷,可怕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地球表面上爬行,如同虱子、蚂蚁,或其他下贱的东西。
独善其身。
那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们的名字之一。
独善其身。
那是开始,亦是结束,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是绝对:独善其身,独守自己的灵魂,独自凝眸于黑暗,那是生命的黑暗之神。孤独如同阿波罗的女预言家站在她的青铜三角祭坛上,如同站在通往未知世界的罅隙上的预言家。预言家,通往未知世界的罅隙,从黑暗中发出的奇特蒸腾,预言家必须发出奇特词语。奇特残酷但意味深长的词语,是意识的新词句。
这是男人最为内在的象征:独处他自我的黑暗洞穴中,倾听命运无声的脚步悄然踏入。命运、末日,悄然流淌而入。那又怎么样?独善其身的男人,那才是绝对的,谛听吧,对他的命运或末日来说,独善其身才足以与之抗衡。
独善其身的男人是谛听者。
但大多数男人听不进去。罅隙正在合拢。没有无声的声音。他们聋哑兼具,是蚂蚁,匆忙的蚂蚁。
那就是他们的末日,是一种新的绝对,就像渣滓从活生生的相对中坠落到纷乱的尘堆上或蚁冢上一样。有时这尘堆愈变愈大,几乎覆盖整个世界。随之它演变成火山,一切从此重来。
“这与我毫无关系,”理查德对自己说,“让他们为所欲为去吧。既然我是个心地善良的可爱之人,我会爬上寺庙的塔尖去当自己的呼唤者。”
那就领略一下这可怜又可爱的人站在塔尖上高举双手的风来吧。
“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每个人都独善其身,每个人都独自与自己的灵魂相守,独自,似乎自己已经死了一样。权当自己已死,孤独地死去了。他死了,了然一身。他的魂是孤独的,只与上帝在一起,与黑暗的神同在。上帝就是上帝。”
不过,如果他喜欢召唤而不是叫卖炸鱼、报纸或彩票,随他去。
可怜的人,这简直是个莫名其妙的召唤:“听我的,独善其身。”但他感到是在应召而发出召唤。
于然一身,独善其身,独自依仗不可知的上帝。
上帝定是不可知的。一旦你定义了他并描述他,他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只要你谛听牧师布道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而一旦你与上帝成了好友,你就再也不会孤独了,可怜的你。因为那就是你的结束。你和你的上帝携手穿越时间和永恒。
可怜的理查德发现自己的处境可笑。
“我亲爱的女人,我恳求你,孤独吧,自顾孤独下去。”
“哦,索默斯先生,我原意,只要你握住我的手。”
“有一处漩涡,”语气严厉起来,“包围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漩涡包围着你,也包围着我。”
“我掉下去了!”她惊叫着,展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或许是袋鼠的也未可知。
“我为什么对袋鼠如此有成见?”理查德自忖,“因为我卑鄙。
我对他们就像一个可恶的小魔鬼。”
他感到自己是个可恶的小魔鬼。
可是袋鼠意欲成为另一个蜂群的蜂后,蜂群如云依附着他,看似一棵硕大的桑树。恶心!他为什么不能独山至少一次世行,彻底超脱一次。
蜂后嗡嗡传达着福音、福音,还是福音。无论是蜂的姿态还是别的什么姿态,都令理查德厌倦。越来越多的慈善,只能令人越来越厌恶。“慈善之苦难深长。”
可是,一个人不能在彻底的孤独中生存,像猴子搂着一根根子爬上爬下度日那样。必须有会晤,甚至像圣餐那样的交流。“此乃汝之肉体,吾取之、食之”,牧师,还有上帝,在血祭仪典上都这样说。
这仪典表达的是至高无上的责任和奉献,祭品献给黑暗的神,献给那些体现黑暗的神之意志的人们。祭品献给强人而不是弱者;是怀着敬畏之心,而不是少许爱心。体现力量的圣餐,向天国之荣耀的升腾。
赞美。
第十五章 杰克反击
一章接一章,可什么也没发生。不过,男人可是思想的冒险家。
他落入药膏的漩涡,他在亘古礁石上触礁,他越过渊薮接吻,他的剪影晖映在伊斯兰寺院的尖塔上。这一切都撼人心健。
简言之,这里有个哈丽叶、一个袋鼠、杰克、杰兹、维基,还有几个纯粹的澳大利亚人。不过你像我一样知道,哈丽叶此时正兴高采烈地涂上洗发剂,双手挽着头发。阳光下,她把头发拢到额头前,观看一道道金丝、铜丝,啊,还有几条银丝和锡丝呢,看得她好生欣喜。此时,袋鼠刚刚接手一个十分棘手的辩护状子,成败事关上千镑得失。当然,他正竭尽全力,直到一部分钱流入自己的腰包。而杰克和维基去维基父亲家过周末了。他出去垂钓,已经钓上了一条鲤鱼、一条鳍刺豚、一大条笛鲷、一条鹦嘴鱼、七条黑鱼和一条墨鱼。那他有什么错?她骑着小马去看望一个旧情人,那人实在太年轻,让她无法忘怀。而此时杰兹则同一个男人争论货运费呢。散落各处的澳洲人都在为这事那事打着赌。那他理查德趁机攀登一两座精神的寺院塔尖又有什么错?当然并无机可乘。可你知道的,哈丽叶正在阳光下梳理她的头发,袋鼠正为一大笔钱煞费苦心钻研辩护状,杰克正垂钓,维基正在调情,杰兹在与人讨价还价,你还想知道点什么?我们不能总像提琴上的E弦那样绷得紧紧的。如果你不喜欢小说,你尽可不读。如果布了吊不起你的胃口,别吃,弃之一旁。我并不在意你的莽撞无礼,我太明白,你能强使驴子喝水,如此而已。
至于神嘛,理查德想,有些神是爱报复的。“我,你们的主,你们的神,是个爱嫉妒的神。”事实如此。一个嫉妒之神、复仇之神。
“父辈造下罪孽,他们的后代要受惩罚,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因为他们都恨我。”当然。父辈逃脱了,可第二代和第三代逃不掉,父债要由他们来还。我们该把这东西放进烟斗里品上几口了。因为我们正是这第二代,而正是我们的父辈骄奢淫逸,经冬我们新生地球上的珍馐。他们暴殓天物,给我们只剩下残羹。
“我,你们的主,你们的神,是个嫉妒之神。”
他确是嫉妒之神。上帝是夜半时分敲门的隐身陌生人。他是神秘的生命启示,敲门要求进屋。奇妙的维多利亚时代竟能够把门关得死死的,并用电灯将院子照得雪亮,排除一切外界,一切均关在门里。
那不可知物变成了一个笑料,现在依然是笑料。
可是,外界开始变得愤怒。“看看呀,我在门外敲门呢。”
“那就敲下去吧!”自鸣得意、心地善良的人类说。人类刚刚发现其祖先是猴子,由此明白了自己何以会耍猴子的把戏。“敲下去吧,没人阻止你敲门。”
赫尔曼·亨特绘了一张画,画上的红胡子男人打着一盏星条灯笼在敲门。无论那敲门人是谁,他已经敲了三代了,对此已经腻了,怕是马上要开始踹那门了。
“这是因为,我,你们的主子你们的神,是个嫉妒之神。”
倒不是说他嫉妒雷神、宙斯、巴克斯或维纳斯。门外的伟大黑暗之神是所有这些神之集大成者。有时你打开门,雷神会冲进来,一锤子击在你头上;或许神秘地进来的是巴克斯神,他使你的头脑变得混沌一片,可膝盖和大腿却开始闪烁;或许进来的是维纳斯,你闭上眼睛,开歙鼻孔,像一头牛那样喷香水的芬芳。所有这些神,当他们通过这扇门时,他们就变成了人。在门外,他们分别是黑暗的这神那神,是不可知物。这不可知物是个嫉妒心极强的神,而且善于报复。一个可怕的复仇之神,即摩洛神,阿斯塔蒂神,阿什塔罗斯神和巴尔神。正因此我们现在不敢开门,否则进来的将是一个地狱之神,这一点我们太明白了。我们是第二代人。我们的孩子是第三代。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则是第四代。嗯!嗯!是谁在敲门?
星期天下午,杰克来看妻子家人时,匆匆来“咕咕宅”串门了。
他知道,当世上的男人们偕妻子刻意打扮一番拥上街头时,理查德和哈丽叶十有八九会在家──他们星期天不爱出门去凑这热闹。
没错儿,他们都在家,坐在廊檐下听雨看海呢。灰蒙蒙的天上落着小雨儿,透过雨丝看大海,似乎那海显得苍白而窄小。杰克突然出现,拐过墙角向草坪走来。见此情景,索默斯吃了一惊,似乎是有敌人扑向他一样。杰克身穿灰色旧装,看上去瘦高健壮。走过来之前他略为迟疑一下,似乎在打量雨廊上的这一对毫无戒备的斑鸠,随之脸上露出微笑来。他收住脚步时,那双黑色的眼睛亦透着笑意。索默斯一眼就看到了他,哈丽叶扭过头来看他。
“哦,是考尔克特先生啊,怎么,您好吗?”说着她惊起,穿过雨廊边走边伸出手来要与他相握。这样杰克就得过来。沉静的理查德也同他握了手,随后,趁着杰克跟哈丽叶友好寒暄的空儿,进屋去搬椅子,端出杯盘来。
“好久没见面儿了。”她说,“太太为什么没来,我很想见见她呢。”
“您瞧,我是骑着小马来的,可天不作美啊。”说着他忸脸朝海面上看去。
“是啊,寒风袭人!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