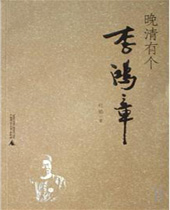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粘龆鳌⑷杖攵ⅲ旄呋实墼叮嗥哪茏缘闷洹钙蜇っ裰鳌梗╞eggar 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着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 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义日加上个斯大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共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
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 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着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