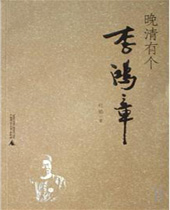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7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未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谓「势力范围」也);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这个名词对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盲、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椿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还好,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 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五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 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 Mall Gardner 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加以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间」(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作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椿更可笑的偷窃小事而闹入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其它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 ,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而发现赃物却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儍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不付钱只好开门传教。
他二人吵不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是还要噜噜嗉嗉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德军肆虐,传教士收保护费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十月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