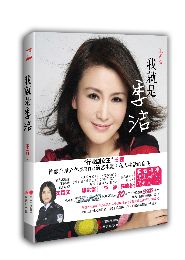无字 张洁-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又说: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一九五七年马上遭到不可抗拒的申斥——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会议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
而且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还没等到一部哪怕不太完备的法律,一个哪怕不太健全的法制,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置于死地。置一个国家主席于死地的法律,根据何在?
比起“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刘少奇所倡导的法律、法制什么的,是不是很天真烂漫?
更不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一九六O年开始,又命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没有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从而也就没有了各司法机构间的相互制衡。
幸好男婚女嫁方面,还有个托派分子王明起草的《婚姻法》可以借鉴。不过,谁又能指望一个托派分子,对《婚姻法》有什么科学性的贡献?
面临不论什么理由导致的家庭破裂而又无计可施的女人,至少还有《铡美案》这一出成为依据,成为对付不管什么理由婚变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
当故事叙述到这里的时候,“陈世美”已经在一个角落里,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还没有出生的胡秉宸。即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统天下,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可是那时候的人很呆、很死性,不懂得使用“外调”这种既可翻天又可覆地,一瞬间上天、一瞬间人地的手段。
石灰窑子离叶家不过二十多里地,居然就没派人到那里外调一下:能不能把姑娘许配给叶家?
秀春的外祖父在应允这桩婚事前,不是没有犹豫过。
他不那么看重聘礼,这和财大气粗无关,只因他是个有气振的东北汉子,对鸡毛蒜皮、装腔作势极为不屑。因此他反感叶家的聘礼过于玄虚——哪怕一块土坷垃,也用红纸煞有介事、一包包地包着,一盒子一盒子地抬着,一抬好几架。但他对此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背着手摇头又晃脑,想着怎么推诿,才能让那来说媒的,拐了八道弯的亲戚下得台面。他这样背着手踱来踱去、摇头晃脑、思前想后的时候,不像——个地主兼猎人.倒像一个豪放派的、正在吟诗作赋的文人。更不像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戏剧、小说、电影里的地主那样,獐头鼠目,心黑手辣、广收暴敛,除了租子六亲不认。
想来想去,还是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他这样思维、办理事情的人,如何维持、治理、发展那样一个地主之家?实在逆反地宅之常。
这时有人来招呼他,大门拍得山响,嗓门也很敞亮,和坐落在林海雪原里的石灰窑子很是相称:“人已经联络好了,明天一早上山打狍子。”一听打猎,秀春的外祖父就开始心猿意马。他最爱打狍子,家里净吃狍子肉。到了冬天,一家子人吃火锅用的抱子肉、野鸡肉、野兔子肉,全是他猎来的。
转脸看到聘礼上的那笔字,他停住脚步,寻思起来,立刻想到家学渊源:
这个穷人窝在本世纪初石灰窑子里的业余猎人兼地主,很奇怪地迷恋上知识,这种迷恋居然使他把两个儿子送到省城,上了洋学堂。他的正屋里甚至还有一张大书案,书案上摆着文房四宝,虽然称不得上品,价格却也不菲,因为难得使用,更像一道点缀。就像后世人们有了点钱,又不懂得何为绘画艺术,就花钱雇个三等画匠,给自己画张两米高的肖像,挂在客厅或是回旋楼梯侧面的墙上,以示风雅,兼及资产的说明。否则也也不会给女儿起了那样一个文气的名字——墨荷,与文房四宝连带的“墨盒”,不无谐音之趣,既有荷,就有莲,叶莲子的名字,可能便是由此而来。
他的文明程度还表现在各辈夫妻有各辈夫妻的单独房间,而不是按照当地习俗,一大家子人按辈分顺序排列,成双捉对地睡在一张大炕上。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房产钱财,当地就是有房产钱财的人家,也不一定像他这样做。
他又扭头看了看来说媒的——那个绕了八道弯的亲戚,便骼膊一甩,同意了这门亲事。
从思量着如何推诿,到一甩胳膊同意,前后不过二十来分钟,可见他是如何地胸无定见,尽管还费了一番思量。其实他的推诿根据不大,同意的根据也不大。
吴为考虑问题那种舍本求末的方式,不会说“不”的毛病,一旦面对需要当机立断的大事就临阵脱逃的懦弱,可能有根有源。叶志清能写一点,会算一点,这大概和他父亲不但是村里惟一的私塾先生,还是个秀才有关,因此叶家又算得是村里的书香门第。
说到这个乡下的私塾先生,难免不想到孔乙己。
虽然舞台不在酒店,而在他梳小辫的当儿。他的小辫不是每天梳,隔几天才让秀春的奶奶给他梳一次,更谈不到洗。每逢奶奶给他梳小辫的时候,总是一边梳,一边狠狠揪他的头发,嘴里还念念有词,历数他的无能、知识的狗屁以及由此殃及全家的穷困……与孔乙已在咸亨酒店的遭际,同屑斯文扫地,且更加直露。
这个脑袋后头扎着根小辫,一身短打,连孔乙己也不如的乡下私塾先生,每天不过就是教学生们念念《上孟子》《下孟子》,或是《论语》。不论怎样,孔乙己还有一件破长衫,可以去吃茴香豆,时而还可以喝上一口绍兴花雕,闲情逸致地和人讨论“苘”字的几种写法。他呢?连讨沦“茴”字几种写法如此的精神享受也不可得。他身处的环境,与人杰地灵的绍兴如何相比?真是荒漠一片,就连懂得从何处下手奚落孔乙己的人也难以寻觅,可以想知他是何等的寂寞。全家人主要靠他的束惰勉强维持生活。所谓束惰,不过是一小袋高梁米或一小袋包米楂子,和弟子们送给孔子的一条条干肉,风马牛不相及。
。墨荷延续了娘家对知识的嗜好,在她没有去世之前,一直坚持让秀春跟着爷爷到私塾去唱《弟子规》《百家姓》《三字经》《论语》什么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等等,虽不明白意思,却是倒背如流。这个四五岁的孙女,算是这个私塾先生的得意门生,爷爷也很趋时,时而找些文白夹杂的新书来念,什么“天朗气清,恰日良辰,吾辈去旅行,柳暗花明,春满山城……”之类。
秀春还跟爷爷正经临过帖。这一手童子功,使她的字迹直到去世前,在手腕哆嗦、运笔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仍让吴为望尘莫及地风骨犹存。因此秀春的爷爷,对这个个能继承叶家烟火的女孩,倒是钟爱有加。
墨荷嫁到叶家以后,与昔日生活大变。叶家的屋子,下雨漏雨,刮风漏风,不下雨不刮风的时候,就从房梁上往下掉老鼠或是掉长虫。
她喂猪、喂鸡,做一大家子的饭、刷一大家子的碗,还得缝一大家子的衣服、袜子、鞋……却样样还不称大家的心。
她做得太多,就有太多的不是可以数落。她和家里的长工没了两样,分明也是了一个长工。
墨荷轻蔑地想,叶家的人实在比自己娘家还会摆谱,也不知道自己没嫁过来以前,叶家人是怎么活的!
女人对女人是苛刻而锐利的。墨荷对叶家的轻蔑有多少,婆婆和小姑姐就能体味多少,一分也疏漏不了。她们就更加变着法儿折磨这个新进门的,轻蔑她们的女人。
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好,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好,政客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好,个人之间的血债也好……总会有个尽头。杀了,剐了,抢到手了,胜利了……也就了结了。
女人之间呢?
自一八七九年的娜拉出走到现在,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斗争已经一白多年,可谓前仆后继。岂不知有朝一日,真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时候,她们才会发现,女人的天敌可能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己,且无了结的一天,直到永恒。
严格地说,叶家算不得虐待儿媳妇,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
小姑姐只管盘坐在炕上发号施令,闹得墨荷放下簸箕拿起筲,说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可能太夸张,说方便的时间都没有,倒还恰如其分。
一个穷家,居然也能想出那许多折腾人的事情来!那能想出这些活计的脑袋,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小姑姐果然聪明过人,倒也不仅仅表现在如何支使墨荷这一桩事情上。她是样样累,样样拔冲。就连她的头发是不是比他人黑,也是她的一桩心事。更不要说在墨荷没过门以前,她是村子里顶尖的美人……也就难怪她最后累得生痨病而死,至于秀春的奶奶,只不过添了晚上抽烟袋的习惯,喂了一天的猪,喂了一天的鸡,做了一天一大家子的饭,刷了一天一大家子的碗,缝补了一天一大家子的衣服、鞋、袜以后,墨荷别指望躺到炕上歇歇腿,去睡那世上再苦再穷的人也得睡的那一觉。她得服侍婆婆抽烟。
秀春的奶奶抽一袋,就让墨荷装一袋、点一袋,一直抽到三星上来。有时秀春的奶奶都睡了一觉,醒过来,接着抽。
一穷二白的叶家,自叶志清的媳妇娶进门后,即刻有了地主的修养和脾性。可见地主的修养和脾性以及对他人的欺压剥削,未必只和劳资关系、生产资料什么的有关。奶奶的一统天下,直到叔叔娶进媳妇,也就是秀春的婶子之后,才有了较为彻底的改观。
如果说到秀春的婶婶,就必得先交代秀春的叔叔是什么样的角色,方见得婶婶的不同凡响。就好比武林中人看那对手惯于使用的家伙,便大约可知对手的路数。秀春的叔叔在村里开小杂货铺,卖个油盐酱醋。从前倒也见过世面,在大铺子里当过伙计,只因手脚不老实,让东家炒了鱿鱼。
叶家的确乏善可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要说五世,叶家连一世之泽也谈不上。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秀才,怎么会养出不是手脚不老实,就是挪用公款、被人通缉的儿子?这里指的是,不久以后买卖学成的叶志清,刚被一家银行录用,就因逛窑子挪用公款,不得不逃之天天那一档子事。叔叔娶进的女人和他很匹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绝非信口胡言。
婶婶刚嫁过来的时候,秀春的奶奶也曾打算给她一个下马威,像制伏秀春的妈妈那样,一举制伏秀春的婶婶。
那天奶奶也没让秀春的婶婶干什么重活,不过是吩咐她去磨豆子。磨豆子的活计有什么累?哪家农村妇女没有磨过豆子?
可是她一上来就喝了卤水。想来早在娘家的时候,她就谋划好了。
也不是一上来就喝,而是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村前村后地先跑了几圈。她一面跑,一面尖厉地号啕着:“老天爷呀,我是不能活了,不能活啦!这老叶家就是不让媳妇活呀!——”好像叶家人就跟在后面追杀。
她跑了多少个圈,村里人就跟在她后面跑了多少个圈。乡下的日子太单调、太没有色彩、太寂寞了,尤其对于胸无大志,也就是说企图不大,却不排除心怀一点乱头的女人。除了鸡鸭猪狗,除了干活,除了一身破衫,还有什么?
特别是冬天,冰雪封了万物,天上地下一片死白,人人都躲在屋子里猫冬,只有屋顶上那点炊烟,才袅袅地生出一点活气。
春夏之季好一点?可那景物,一辈子地看下来,也腻烦了。山从没有崩一方,地从没有陷一块,永远地依旧。人不光靠景物来陶冶,还得靠事件来激活。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生动而又富有感召力的女人,谁能不跟着跑,谁能不跟着激动呢?
村前村后跑回来之后,就舀了一碗卤水,真舀还是假舀,聪明过人的小姑姐也忘了扒着她的碗查看查看。
婶婶也没有真喝,只不过把卤水碗“哐——”的一声砸在了门口,接着就是口吐白沫,眼睛翻白。一家人又是灌凉水,又是掐人中。
农村里很多女人都会这一手,不知墨荷是不会还是不屑。
想来是不屑,一个嗜好知识的人,常常不屑于去干于生计非常实惠的事,反倒会吃知识的很多亏。面对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他们最拿手的办法就是自闭,叫他们“窝囊废”也无不可。
因此,秀春的妈妈没有在这方面给她做下结实的铺垫,秀春一生凡事忍气吞声,墨荷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穷凶极恶、从来不信因果报应的叔叔,纵身一跃掠仕了婶婶的头发,稳、准,狠地像是套住一匹烈马,扬起拳头就要让她灿烂出一些颜色的时候,婶婶就像练过武功。回身就是一脚,直捣叔叔的鸡巴。叔叔立时脸色煞白,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两口子哪有不打架的?在农村,打架就是打架,是很务实,很具体的力的较量,不像城里人,把只务虚不务实的吵架也叫做打架。
此后他们又比试了几次。在村子里战无不胜的叔叔,从此不能再拔头筹,也从此开始了北的记录。
婶婶也没什么绝活,就是专踢叔叔的鸡巴。一个敢踢男人命根子的女人,是何等了得的女人!
男人又是如何爱惜自己的命根子!又如何为了他们的命根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以后叔叔见了婶婶,就像兔子见了鹰。
不谈满腹经纶,肚子里也算有些文章的爷爷,在这样的女人面前,除了仰面顿足说些“家门不幸,家门不幸——”的空话,还能指望这酸腐的穷秀才有什么作为?奶奶也再不敢招惹婶婶,不但不敢招惹她,反倒让她制伏了。
小姑姐也再不敢吩咐她什么,只要她皱着眉头,发出一声“啊?——”小姑姐马上就含糊其辞,不再重复她的指令。
可这并不等于奶奶就会对另一个媳妇手软。奶奶甚至用更加升级的办法折磨墨荷,以笼络、讨好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