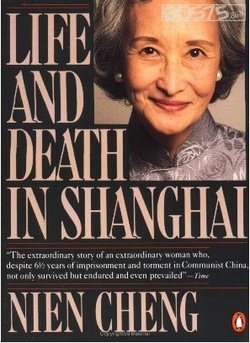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郭鹏听到“次泾阳”三个字,根根神经紧张了,吃惊的眼光木然地盯着韩工程师。他想:这下可糟了,秦妈妈虽然揭露了沪江纱厂和信孚记花行来往的秘密,但和他没啥关系。韩云程坦白“次泾阳”,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了解“次泾阳”的名称是郭鹏给取的,那他摆脱不了这关系。勇复基吓得低下了头,不敢呼吸,他后悔不应该去参加第一次总管理处倒霉的秘密会议,现在无论如何也跳不出这烂泥坑了。梅佐贤心里很坦然,他不动声色,坐在那里。他知道:天掉下来有徐总经理顶着。他端徐总经理的饭碗,当然服徐总经理管。资方代理人还有不为资本家服务的道理吗?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正要紧紧靠着徐总经理,“五反”过后,料想徐总经理不会亏待自己的。徐义德给秦妈妈进攻得浑身有气无力,已经招架不住,这时又亲自听了韩工程师这几句话,迎头又受到一闷棍,打得他非常沉重,痛上加痛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在广播里听到韩云程归队,还以为是大势所迫,不得不应付应付,现在听他那口气,完全不是应付,而是不折不扣归了队。那么,“次泾阳”以外的问题,当然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他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个缺口堵住。秦妈妈只是揭露问题的一个方面,韩云程却了解生产方面的全部情况,如果这个缺口突破,汹涌澎湃的大水通过这个缺口便会冲垮他的防堤,一泻千里,洪水泛滥,便不可收拾了。他向韩工程师笑了笑,用那鹰隼一般的目光注视着韩工程师:
“韩工程师是学科学的,态度严肃,办事认真,不随便讲话。你是我们厂里的技术专家,沪江靠了你,我们的事业不断扩大。我对你一向是很尊敬的。你每次讲话我都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你的记忆不好,没有把事体说清爽,使人容易误会。我们厂里过去用过‘次泾阳’,工务日记上写着的,报表上也填了的,因为花司配的花衣不够,我们不得不自己买点花衣贴补上,你说,是吧,韩工程师。”
徐义德最后两句话充满了热情和无限的希望。他热望韩工程师再回到他的身边,即使不肯马上回来,也不要使他太难堪了。他这一番话在韩工程师的心里确实起了作用,总经理就坐在自己的面前呀,多年的交情,哪能抹下这个面子呢?要是现在当面顶撞,以后要不要在一块儿共事呢?在徐义德面前,秦妈妈又把“次泾阳”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听到这里面的内幕,叫他吃惊,也使他懂得做了事是隐瞒不住的。他不能作证“次泾阳”的秘密。可是杨部长的眼光正对着他哩,他在杨部长面前能够不作证吗?他曾经向工会谈的那些事哪能好收回?说出去的话,谁也没有法子收回了。他一时解脱不开尴尬的处境,只好紧紧闭着嘴。杨健看韩工程师拉不下脸来说话,他亲自点破徐义德:
“花司给别的厂配的花衣够,同样数量的花衣,沪江就不够,你说,奇怪不奇怪?照你这么说,你贴补了很多‘次泾阳’,那么花司还欠你不少花衣了?”
“已经贴补进去,不必再算了。”
“那你不是吃亏了吗?”杨健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身上。
徐义德的脸唰的一下红了。杨健追问:
“你一共用多少‘次泾阳’换了好花衣?”
徐义德从杨部长口气里已经知道韩云程啥都坦白了,秦妈妈揭露的那些材料,物证人证俱在,再也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现在再坚决否认,那对自己不利。他毅然下了决心: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干,干脆坦白。他想用坦白把韩云程这个缺口堵住。他低着头,用悔恨自己的语调,沉痛地说:
“唉,这是我的过错。从一九五○年六月起,棉花联购处宣布联购,私营厂不能自行采办。花纱布公司配棉很好,纤维很长,我资产阶级本性未改,觉得有利可图,就在信孚记花行头了一些黄花衣搭配。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次泾阳’。我先后一共买了两千多担,大约用了一千八百担,现在还留下两百多担在仓库里没用。余静同志提出重点试纺以后,我就没敢再用了。以一百万元一担计算,一千八百担共取得非法利润十八亿。细账要请工务上算。这是我唯利是图。盗窃国家资财是违法的,请上级给我应得的处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徐义德说完了,连忙又补了一句:
“这些违法的事情是我个人做的,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希望上级给我处分好了。”
“这个我们了解,当然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不用你操心。
现在就是要你彻底交代。”杨健说。
“是的,我要彻底交代。”
钟珮文匆匆走到余静面前,附着她的耳朵,低低地告诉她夜校教员戚宝珍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会议,已经踉踉跄跄走进大门了,余静一听到这消息,马上皱起眉头:戚宝珍那个病哪能参加这样激烈的会议呢?她的身体支持不住的?余静要他赶快劝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进入会场,派人送她回去好好休息。他站在余静旁边,迟迟不去,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他这个夜校教员怎么能够阻止戚宝珍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说别人,就说他自己吧,听到这样重要的会议,不管身体哪能,一定也要来参加的。余静察觉他的顾虑,果断地说:“你告诉她,是我不让她参加的。她要是生气,过两天,我亲自到她家去解释。”
钟珮文立刻走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回到铜匠间,坐在汤阿英附近的木凳子上。
汤阿英听到徐义德坦白用了一千八百担的坏花衣,顿时想起从前那段生活难做的情景,心里汹涌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怒。她听了徐义德的坦白,霍的站了起来。
坐在她前面的人闪出一条路,她站在长方桌旁边,感到无数只眼睛都在对着她,耳朵里乱哄哄的,听不清楚是啥声音。她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右手抓住白台布,激动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点。这时,整个铜匠间很平静,她知道大家在等她发言。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慢慢地说:
“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她说到这里激动得再也讲不下去了。
余静在一旁鼓励她:“慢慢讲好了。”
“我要控诉徐义德的罪恶,”等了一会,汤阿英才接下去说,“你害得我们工人好苦呀!你用坏花衣偷换国家的好花衣,我们流血流汗,你吃的肥肥胖胖。我们累死了,你还不认账,说我们做生活不巴结,清洁卫生工作不好。我的孩子都早产了,这样做生活还不巴结吗?徐义德,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坏家伙,你有良心吗?……”汤阿英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句紧接着一句,声音也渐渐放高了。她每一句话像是一粒火种,散发在人们的心田上,立刻燃烧起熊熊的愤怒的火焰。
坐在韩云程紧隔壁的清花间老工人郑兴发心里特别激动。他在清花间做生活总是很巴结的,就是因为徐义德盗窃国家原棉,车间生活难做,工人同志们怪来怪去,最后怪到清花间。余静虽然在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是原棉问题,不怪清花间,可是没有水落石出,在人们心上总有个疙瘩。徐义德坦白交代才完全道出问题的真相,给汤阿英一提,他的心像是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激动。他站了起来,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要把徐义德的丑事揭出来。在纱厂里,清花间顶重要。清花间花卷做不好,那么,钢丝车棉网不灵,影响棉条,粗纱条擀不匀,细纱断头率就增多,前纺就影响到后纺。细纱间工人骂粗纱间工人,粗纱间工人骂钢丝车工人,钢丝车工人骂清花间工人,从后纺骂到前纺。这个车间和那个车间不团结,大家都怪清花间。我在清花间做了二三十年的生活,哪一天也没有磨洋工,生活做的不能再巴结了。本来一千斤一镶,不分层次;后来五百斤一镶,分八层,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做到家了,后纺的生活仍旧不好做。毛病出在啥地方?余静同志和秦妈妈把资本家偷盗原棉秘密揭出来,盗窃国家原棉,破坏我们工人团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徐义德。徐义德一共盗窃国家多少资财,要详详细细地算出来。”
“是呀,就是徐义德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陶阿毛大声叫了起来。
铜匠间各个角落同时发出相同的声音。可是谭招弟靠墙坐着,闷声不响。自从生活难做以后,她最初是怪细纱间,后来又肯定是清花间不好,余静在会上虽然说过,她听了心里总是不服,相信自己是对的。她老是说: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她认为总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这一天终于到了,但证明自己的意见不对。事实不可驳倒,心中也服了,她面子上还有点扭转不过来。
汤阿英等郑兴发讲完了,她举起右手高声叫道:
“我们要徐义德彻底交代五毒罪行,不胜利决不收兵!”
大家都跟她大声叫了起来。汤阿英叫过了口号,转过身子要退到后面去,余静要她坐在刚才发言的地方。她就坐下了。她现在感到非常舒畅。
徐义德见汤阿英慷慨激昂的发言,而且还叫了口号,确实叫他吃了一惊。他深深感到上海解放以后变化太大了,秦妈妈那样的老工人发言有步骤有层次,条理清楚,一步步向他紧逼,叫他不得不服帖;汤阿英这样女工也毫不在乎地指着他的鼻子叫口号,使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向是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今天才觉得这个日子过去了,要低下头来。他低声地说:
“我一定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把盗窃国家原棉的细账算出来,呈交杨部长……”
“其他方面呢?”杨健问他。
“还有哪个方面?”徐义德故做不知,惊诧地问。
“哪个方面?”杨健看他装出那股糊涂劲,想从他的口气里探风声,就反问道,“你自己的五毒行为还不清楚吗?”
“清楚,清楚。”徐义德不敢再装糊涂。
“那就交代吧。”
徐义德望着吊在铜匠间上空的一百支光的电灯在想,他感到今天这盏电灯特别亮,简直刺眼睛,叫人不敢正面望。可是杨健的眼光比这盏电灯还亮,照得他无处躲藏。他想了一阵,说:
“关于偷工减料方面,我想起了两件事:去年人家用包纱纸,我下条子叫不用。打大包可以多拿十个工缴,打包不够,没打,棉纱商标也减小……”
杨健止住了他往下说:
“这是小数目,你就重大的方面谈……”
“我想不出了。”徐义德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袖筒里去,不再讲了。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徐义德听杨部长一追问,不敢应承,却又不愿否认,很尴尬地站着。他把头歪过来,似乎在回忆。
“要不要别人帮你想一想?”
杨健笑着望望他。他不好答应,也不好拒绝,顿时想了个主意,说:
“启发启发我也好。”
韩工程师见他吞吞吐吐,就对他说:
“你每月在总管理处召开秘密会议的事忘了吗?”
“韩同志,事情太多……”
韩工程师听他叫同志,慌忙打断他的话,更正道:“啥人是你的同志?我已经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韩先生,事体多,一时想不大起来。”徐义德见静云程态度那么坚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刚才想把他拉回来显然是不可能了。他便狠狠给韩云程一棒子,想叫韩云程抬不起头。他说,“韩先生每次会议都参加的,许多事体也不是我徐义德一个人做的。韩先生是专家,是工务上的负责人,过去工务上有些事我不懂,还亏韩先生帮忙出力。今天也请韩先生坦白坦白,有啥错误,都算我的,我一定愿意多负责任。”
徐义德轻轻几句,把目标转到韩云程身上。韩云程心里想:徐义德你好厉害,把事体往别人身上推,想摆脱自己!他有点狼狈,急得说不出话来,头上渗透出汗珠子,结结巴巴地说:
“徐义德,你,你……”
工人们的眼光转到韩云程身上,在等待他发言。杨健的眼光却停留在徐义德胖胖的面孔上,说:
“韩工程师早向‘五反’工作队交代了。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是你主使的,别的人受你的骗,上你的当,他们参加了,受了你的钱,不要归还,也不要负责。今天是你坦白交代,怎么要韩工程师坦白?态度放老实点,不要拉扯到别人身上。”
余静从杨健几句简单有力的话里进一步看出徐义德的阴谋诡计。她钦佩杨健的智慧,及时识破了徐义德的阴谋。
杨健把韩云程从狼狈的境地里救了出来。韩云程紧张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盯了徐义德一眼,说:
“别耍花招了,你的五毒不法行为我都向杨部队检举了,你快坦白吧。”
“是,韩先生。”徐义德竭力抑制心中的愤怒,表面装得很平静。
“在座还有梅佐贤,郭鹏,勇复基……他们也都晓得,你再也隐瞒不过去了。”
从会议开始到现在,勇复基的眼光一直望着面前的白色台布,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噗咚噗咚地跳,希望会议早点散,可是今天的时间过去的特别缓慢,一秒钟比平时一点钟还要长。他在担心别联系到自己,韩工程师终于点了他的名。这不比在别的地方,这是在铜匠间呀。这里有徐义德,还有杨部长啊。正当勇复基左右为难的时刻,徐义德怕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他们动摇,赶紧接着说:
“我做的事,我一定负责;就是韩先生帮我做的事,我也负完全责任。”
郭彩娣指着徐义德说:
“你叫别人做的事,你当然要负责。不要兜圈子,快说!”
“我马上就说。偷税漏税部分我已经写在坦白书上了,早交给了‘五反’工作队。是不是可以还给我看看?这是我和总管理处同仁一道弄的,我没有亲手弄,记不清楚了。”
“刚才我说的话,以前写的谈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你忘记了吗?你自己做的坏事写的坦白书,不清楚吗?还要看啥?”杨健知道他又想把问题扯远,延迟时间,分散大家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