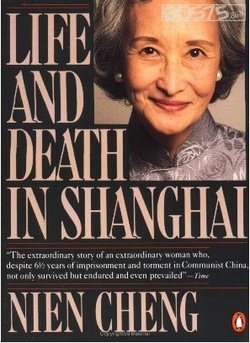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2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的黄金手表,戴在手上,显得富丽堂皇。”
他看了一下手上金晃晃的厄尔近,觉得她说的不错,又换了一块瑞士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问她:
“这一块呢?”
“十分名贵,非常实用,样式新颖,朴素大方,戴在手上并不显眼,却很实惠。”
他满意地点点头,顿时想起在五反运动的辰光,曾经戴过两天,准备万一到提篮桥坐班房,有这块日历表,好派用场。五反运动虽然斗争激烈,场面紧张,但是运动一过,沪江这些企业仍然是徐义德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传达学习和风细雨,既不激烈也不紧张,而是令人兴奋,想到祖国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前途,没有人不欢欣鼓舞的,可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一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紧跟上,北京带头全市公私合营,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只有一条出路:紧跟。全市私营工商业合营了,他的沪江那些企业也先后合营了,想起自己的企业,不禁黯然了。他木愣愣地望着劳莱克斯,像是瘫痪一般,一阵心酸,忍不住掉下几滴清泪。
林宛芝正想拿出一块瑞士欧米茄的手表逗他开心,见他默默地望着劳莱克斯,以为他喜爱这日历表,没料到会突然掉下眼泪,大吃一惊,问道:
“义德,有啥心事?”
徐义德没有吭声,她说:
“有啥心事,对我说,别闷在肚里,伤身体啊!”“我有啥心事!我啥心事也没有!完了,完了,全完了。”
“怎么完了?你收藏的手表不是都在这里吗?一块也没有少,怎么完了呢?”
“你,你不知道。”
“你讲出来,我就知道。”
“你不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不懂,你告诉我,我就懂了。”
“晚了,晚了,”他想起解放初期所设想的三道防线,自以为很聪明,现在看来,却有点愚蠢了。为什么不把机器和原物料都设法运到香港去呢?留在上海干什么?幸亏香港那点锭子没有运回来,要是“生儿子”开分厂,全丢到水里去了。如果当初千方百计设法把机器和原物料运走,也不会让人家吃光。他不胜惋惜地说,“太晚了。”
她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焦急地说:
“怎么晚了?你办事快的很,总是抢在别人的前面,谁也赶不上你。”
“你不知道,让有人办事比我快哩。”
“谁办事能比你快?我不相信。”她眼睛里露出惊异的光芒,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办事比徐义德快的,担心地说:“你说晚了,快想办法赶上去就是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你说出来,我们一道想想办法。”“没有办法了。”他说了一句,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幽幽地哭泣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她感到莫名其妙,自从认识徐义德以来,从没有听他说过这样丧气的话。她过去衷心钦佩徐义德一表人材,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倒他,什么麻烦的事体,他都有办法对付。这回遇到什么强人,叫他束手无策呢?她放下手里的表,摘下塞在腋下的苹果绿的细纱手绢,雪白细嫩的左手扶着他的肩胛,右手用手绢给他拭了拭眼泪,不解地问:
“有啥事体叫你生气吗?”
他摇摇头,鼻子一抽一抽地发出伤心的低微的音响。
“和啥人寻相骂了?”
他举起右手,轻轻摇了摇。她感到奇怪,究竟出了啥事体,这样伤心呢?
“别哭了,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我没办法,还可以托人。你在上海滩上熟人那么多,和工商界大亨都有往来,啥办法都可以想出来的。”
“工商界的大亨?唉,他们和我一样:没用。”
“为啥工商界大亨没用?你不是说全国工商界看上海,上海工商界看大亨,大亨们看史步云、潘信诚、宋其文和马慕韩他们吗?你找史步云、马慕韩他们想想办法不行吗?”她知道徐义德和史步云、马慕韩比较亲近,几乎无话不谈。
“什么工商界大亨,全完了!”
“工商界大亨全完了?”她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工商界大亨全完了?他越说,她越不明白。
“你忘记中苏友好大厦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吗?”徐义德一生中参加过许多大会,几乎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唯独全上海申请公私合营的大会却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没有多久的事体,哪能会忘记?”
“这个会一开,公私合营,我们工商界全完了。”“哦。”她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他刚才那一番话的意思。但她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不解地问道:
“那不是工商界自愿申请的吗?”
“你相信工商界真的自愿申请的吗?别人我不了解,我把心里话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对人家说,我就不自愿。”
“政府首长不是说,不自愿可以不申请公私合营吗?”
“工商界都自愿,我一个人不自愿,行吗?”
他听了她安慰的话,内心越发伤感,想起整个私营企业都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流入东海了,一去不复返了,幽幽的哭泣声越来越高。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传到卧房以外,震动了朱瑞芳。
朱瑞芳坐在她的卧房里红木太师椅上,面前的红木圆桌子上摆着一排一排的大大小小的黄金元宝,有二十两一个的小金元宝,有五十两一个的金元宝,也有十两一根的金条,按照大小不同的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顺着金元宝一个个望去,一边默默地数着,脸上闪着得意的微笑。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这不是不相信自己数数的能力,而是对金元宝的爱好,永远也看不够似的,贪婪地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她看到放在红木床上一大包物事,才不舍地把金元宝一一收进特制的小铁箱里。她吃力地捧起重甸甸的铁箱子,放在地毯上,掀起绣花的天蓝色的缎子被罩,把箱子放在床底下。她有点累了,额角上渗透出几滴晶莹的汗珠子,用手绢拭了拭,坐到红木扶手的丝绒沙发里,舒徐地喘了口气。
红木床上那一包物事又闪上她的眼帘。她坐在沙发上,望了半晌,马上站了起来,走过去,捧起那包物事,慢慢移到红木圆桌前面,解开藏青色府绸包袱皮,里面用紫色漆布又包了一层,打开漆布,里面是一堆大大小小的金戒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消息一传到上海,经过传达学习,了解生产资料要公私合营,唯有生活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她带头买生活资料,并且鼓励徐义德和家里人也分别去买。这正合徐义德的打算,大家分别出去选择抢购。朱瑞芳买了电冰箱一类的高档货,觉得家里早已有了冰箱,顶多再买两三个,花钱不多,而且显眼;她就转而买黄金,凡是金元宝,不论大小,凡是能够弄到手的,她都买来。金元宝和金锭不易买到,即使有,买多了,也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她就买金镯头,也不容易买,只是戒指比较多,买起来也不显眼,于是东奔西跑,到处搜购金戒指,原先还买一两一只的,后来八钱七钱的也要,再买下去,不论大小轻重,凡是金戒指,一律都买,她从静安寺一直到了南京路江西路,又从外滩顺着淮海路一直到了常熟路上,整天收买金戒指,集了一堆,用藏青府绸包袱包起,沉甸甸的,府绸吃不住,里面就加了一层漆布。现在她把金戒指都拿出来,放满圆桌子,还摆不下,远远望去,一片金光闪闪,照得她脸上红光焕发,满面笑容。她把戒指按着大小轻重的次序整理了一下,一排排摆起,用右手涂着红艳艳的食指,一个个数过去,殷红的嘴唇一动一动地念着数字。她看戒指互不相连,拿起来费事,眉头一皱,想了个主意,取出一条小手指粗细的丝织带子,把金戒指一个个穿起,约摸穿了有二尺多长,把带子上的金戒指在腰上围起,她那身堇色哔叽的衬绒旗袍好像拦腰镶了一道圆滚的金边,闪闪发着一片灿烂的金光。她想:必要的辰光,把这些金戒指让她的爱子徐守仁带上,拴在腰里,算作裤带,谁也看不见,谁也偷不走,够他用几年了。她解下身上的金戒指裤带,又取出一根同样的丝带,把戒指一个个穿上,穿到三尺长左右光景,忽然从门外传来嚎啕的哭声。她连忙放下手里的金戒指,蹑起脚尖,走到卧房门口,歪着头,耳朵冲着门缝,凝神对外边静听,听了一阵,她辨别出是从林宛芝卧房里传出来的。哭声好生熟悉,聚精会神仔细一听,是徐义德的。她大吃一惊,原来徐义德已经回家,为啥忽然哭泣,是不是发生不幸的事故?还是和林宛芝争吵?她神经紧张,捉摸不定出了啥事体,立刻回到红木小圆桌旁边,匆匆把桌子上的两串戒指收起,包好,放到红木衣橱的最低一层的装衣服的抽屉里。她站在深绿色的地毯上,向卧房四周扫了一眼,见没有收拾金元宝、金条和金戒指的痕迹,才扑扑堇色旗袍,擦了擦手,打开卧房门上的弹簧锁,轻轻走到林宛芝卧房的门口,生气地把门推开,板着面孔,望了林宛芝一眼,愤怒地问:
“为啥把他气哭了?”
“是他自己哭的,怎么说是我气的呢?”
“他在啥人房间里哭的?”
“在我的房间里。”
“这就对了。”
“在我的房间里,就是我气他的吗?”
“你房间里有第三个人没有?”朱瑞芳把林宛芝的卧房一扫,理直气壮地追问。
“没有第三个人,但他也不是三岁小孩,你问他好了。”
“这还用问?除了你气他,还有谁?”朱瑞芳看到桌子上摆着各色各样的手表,以为林宛芝想占有徐义德心爱的手表,可能引起争执,气得他哭了。她撇一撇嘴,说:
“我晓得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从来不哭的。我哥哥朱暮堂给镇压了,他没哭;我弟弟朱延年判了死刑,我和丽琳去收尸,回来给他说枪毙的惨状,他没掉一滴泪。这回要不是你气他,想夺他心爱的物事,伤了他的心,他会哭吗?”她说完了,眼光旋即转到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
林宛芝最初听不懂她的话,见她眼光落在手表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林宛芝辩白说:
“他搁在我房间里的心爱物事,我从来没有动过,更没想夺取它的意思。你不要信口开河,冤枉好人!”
“明摆着的事体,还想抵赖?真是又想吃羊肉,又怕挨一身臊。”
“他今天回来,想看看表,叫我拿出来,他一块块欣赏,我连一块也没问他要。不信,你可以问他!”
不等徐义德开口,朱瑞芳就把林宛芝顶了回去:
“你们两人穿一条裤子,啥事体都依你,你说没要,他还敢说你要吗?”
徐义德心里正烦,讨厌朱瑞芳突然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辟哩啪啦地给林宛芝吵了一顿,语言之间还夹着新愁旧怨,怪他对她的两个宝贝兄弟死亡没有痛哭流涕,真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朱暮堂和朱延年血债累累,作恶多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真是死有余辜,谁了解这两个犯人的罪恶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居然还想他伤心掉泪,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他气得脸色发青,微微低着头,没有理睬朱瑞芳。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心里稍为得到一点安慰,忍住哭声,拿起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接着又戴了欧米茄,西马,厄尔近……一连戴上六块手表,一块紧接一块,把左边小胳臂都戴满了,没有地方可戴了,他卷起府绸衬衫的袖子,想往大胳臂上戴,可是他的大胳臂又肥又粗,手表带子没有那么长,带不上。他于是戴右边小胳臂,也戴了六块各国名牌手表,样式不同,大小不一,不是黄金壳子,就是白金壳子,两只胳臂上的手表闪闪发光,互相辉映。他看了左胳臂的手表,又看了右胳臂手表,看了又看,认为这些手表才是永远属于他的,可是又担心有人拿走,舍不得从胳臂上摘下来。
林宛芝不解徐义德为什么现在对手表比过去任何时候喜爱,看到他那两只光芒四射的胳臂,差点要笑出声来,可是看到朱瑞芳一脸不高兴的望着她,她忍住了。
朱瑞芳怀疑徐义德给了林宛芝许多名贵的手表,从来没有给她一块,她又不知道徐义德究竟买了多少块名贵手表,她冒叫了一声:
“义德,你不是买了许多手表吗?怎么只剩下这么一点?”
林宛芝听她话里有话,连忙声明:
“他只买了这些,一块也不少。”
“我不信。我知道他的嗜好,不管哪个国家出了新牌子的好手表,他都要想方设法买来,国内买不到,就托人到香港,到外国去买。哪个国家新式名贵手表没有?为什么这儿没有最新式的名贵手表呢?”
朱瑞芳有根有据,言之确凿,林宛芝朝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一看:新牌子的名贵手表的确很少,难道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徐义德不再交给她保管,藏到江菊霞手里去了吗?
她不禁诧异地说:
“咦,真是的,怎么没有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呢?”
“不要撇清了,义德什么好东西不交给你保管?他把好手表送给你也呒啥关系,直说出来,我也不夺人所爱,何必在我面前撇清呢?”
“义德没有送过我新式名贵手表,你不信,可以当面问义德。”林宛芝不能再受冤枉,她酸溜溜地说,“他是不是把新式名贵手表送给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朱瑞芳以为指她,瞪了林宛芝一眼:
“我可没有福气收他新式名贵的手表。”
徐义德知道林宛芝怀疑他送给江菊霞。他心情不好,没有时间和她们谈这些问题。他后悔买的手表太少了,为什么各国出产的新牌子名贵手表只买一块呢?每种牌子买它十块一百块不是很好吗?有钱不花掉,都放在厂里,扩大再生产,生产扩大再扩大,现在可好,叫人家连锅端走了。他不耐烦地回了她们两人一句:
“我啥人也没送。”
“我不信!”
“我也不信!”林宛芝同意朱瑞芳的意见。
徐义德给她们两面夹攻,不说说清楚,是没有平安日子过的。他唉声叹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