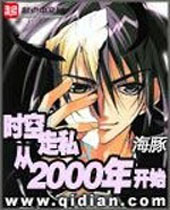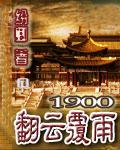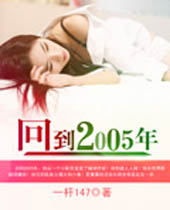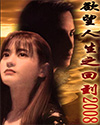芙蓉-2006年第5期-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了。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渐渐就像宰相了。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作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外族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又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弹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作主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明白国情的人都知道,官员批示往往比法律、文件之类更管用。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作数,竖着批示的不作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有的官员面对某些重大事件,他们心里清楚很可能给自己历史留下污点心的,居然用铅笔签字,随时可以擦掉。
素材与灵感
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读书仅为写作,真是惭愧。近日便读《清史稿》、《清史编年》之类,想从史书中寻得蛛丝马迹,看能否变出几个文学形象来。毕竟手头正做的活计同历史有关,我不想完全弄得空穴来风。不曾想,还真有些意思。
比方,有个叫佛伦的人,就让我很感兴趣。史载:“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山东巡抚佛伦疏言,该省累民之事,首在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役,富豪之家田连阡陌而不出差徭,以致全由百姓负担。请以后绅衿等与民人一样,按田亩赋役照例当差,不免役。有旨准其所请,并命其他各省督抚确议具奏。”
我想这位佛伦真是位替民做主的好官,不妨记下他的名字,看他还有其他善举与否。倘若更有作为,便可树为清官形象。
可是再看此人后面的疏报,我就皱眉头了。“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从山东巡抚佛伦疏奏,该省今年正赋豁免,秋成丰收,绅衿人民愿于每亩收获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备积贮,计全省可得二十五万余石。”
我想象不出佛伦是如何知道丰收了的老百姓愿意捐粮给官府的,而且老百姓意见很统一,每亩收获一石者都肯捐出三合。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官员下乡也没有汽车坐,怎么就把全省老百姓的爱国热忱摸得那么准确?我想,佛伦此举大为可疑。
再往下看,佛伦已擢升川陕总督。“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川陕总督佛伦疏报,陕西麦豆丰收,秋禾茂盛,流民回籍者已二十余万。”因为前面已对佛伦质疑了,此处又见他报喜,感觉总不是味道。再回头看看,原来康熙三十年陕西大旱,官府赈济不力,且隐情谎报,总督和巡抚都革了职。我没法查阅当年的气象资料,不知道康熙三十二年陕西是否就风调雨顺了。但是按照古今惯行的官场逻辑,既然前任没有把事情干好,上面重新任用能人,工作就应有新的起色才是。如此推断,佛伦走马上任,陕西即获丰收,应在情理之中。只是不知道陕西丰收了,老百姓是否愿意捐献余粮? “受灾自有朝廷关怀,丰收不忘朝廷困难”,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回佛伦的主意变了。“康熙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川陕总督佛伦疏请,动用正项钱银,贱价收买本年秋粮三十万石,以备西安旗标兵明岁一年军需。”贱价收购余粮,百姓是否自愿,我没能力考证,只好悬想而已。而从事收购勾当的人,大可从中渔利,似乎是肯定的。这并非我的官场成见作怪,《清史编年》中有类似案例记载。
又,“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川陕总督佛伦疏言,奉旨查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修建军事工程,投资自是不小,油水旺得很啊!好在康熙脑子还算清白,他对修长城并不热心。康熙说自秦始皇以来,长城历代整修不迭,却从未有御敌之功,贵在人民团结,众志成城。
阅读到这些材料,佛伦在我眼里就大打折扣了。我怕自己犯胡乱臆想的毛病,便去查看佛伦列传。一看,方知此人的确不是什么好鸟。有个叫郭琇的人曾经参劾佛伦为明珠朋党,佛伦因此获罪罢官。佛伦复出后,到了山东巡抚任上,便挟私报复,参劾郭琇做吴江县令时私吞公帑,而且说郭父乃明朝御史黄宗昌家奴。拿今天的话说,郭琇既是现行贪污犯,又是历史反革命了。多年之后,郭琇得到机会进觐康熙,替父亲伸冤。当面对质,佛伦不得不承认当年指控不实。康熙震怒,欲罢他的官,最终还是豁免他了。也许因为他毕竟是正黄旗官员吧。
皇帝其实都知道
康熙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曾对大学士们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说,治国宜宽,宽则得众。若吹毛求疵,天下岂有完人?康熙还举例说,赵申乔任湖南巡抚的时候,大小官员都被他参劾过,难道全省没有一个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张鹏翮居官很清廉,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曾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居官也清廉,但他刻了那么多书,而刻一部书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只是朕不追究而已。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追究!
读了康熙这番话,方知官员清廉与否,皇帝其实都是知道的。似乎康熙也并不在乎官员是否真的清廉,只要大方面说得过去就行了。康熙提到的几位官员,在历史上都有清名,而最清廉的是赵申乔。偏是这个赵申乔,康熙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有回,康熙又同大臣们说起赵申乔的清廉,这位英明天子并不以为然,说道,朕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但作为封疆大吏,要说他一清二白,朕未必相信!倒是对明知其多少有些贪行的张鹏翮、张伯行,康熙宽宏多了。就我所读到的清史资料,康熙对这两位“张清官”颇多赞赏。
康熙朝被史学界称誉较多,但并不妨碍它出产贪官。贪官并不一定都会倒霉的。索额图和明珠都贪,前者死于监牢,后者得享天年。徐乾学和高士奇也都贪,徐被皇上罢斥永不叙用,高告老还乡仍被召回。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因贪污被参劾,论罪处斩了。原来康熙说,赵申乔确实清廉,但他养的这个儿子太贪了,应按律处斩!不能臆断康熙杀赵凤诏的真实动机,但他并不喜欢赵申乔这个清官,应是事实。康熙曾责怪赵申乔教子不严,赵便上疏,称自己“不能教子,求赐罢斥!”康熙看了他的折子,龙颜大怒:“今阅赵申乔所奏,其词意愤激,殊非大臣之体。”这时的赵申乔是户部尚书,因失大臣之体,挨了处分,戴罪留用。
赵申乔是否真的清廉,不必再去辩护。况且清官多酷,也有不是之处。就说赵申乔,他在湖南巡抚任上,把所有官员都参了,实在有些过分。奇怪的是康熙对官员之好恶,同他们官品之优劣,并没有多大关系。说桩公案,便知康熙如何英明了。李光地和陈梦雷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当时李陈二人正在老家告假,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清廷,告知耿精忠造反详状。可李光地是个夺情卖友之人,上“蜡丸书”时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陈梦雷便成了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李光地却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非但不救陈梦雷,反而落井下石。陈梦雷很是愤恨,屡屡上告,终无结果。多年之后,闹得康熙都知道了,就在巡视关外时,召见了陈梦雷。康熙却并不想昭雪冤情,而是挑唆陈梦雷说出李光地的不忠之状。陈梦雷倒是个君子,任康熙如何暗示、胁迫,他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若是常人,即使不为陈梦雷的厚道而感动,也应为李光地的忠诚而欣慰。可康熙恰恰不是常人,他是皇帝,非常失望,而且气愤。他斥退陈梦雷,怒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原来,这时的康熙想整李光地了,只是治罪无凭。皇帝想治别人的罪,本可不用理由,但若能有些把柄,毕竟方便些。可见,皇帝用人整人,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也不关乎国法纲纪。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