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洗澡
周六下午,这位母亲开车去了购物中心的那家面包店。看完活页夹上贴着的蛋糕照片后,她订了巧克力的,是孩子最爱吃的。她挑选的蛋糕上面装饰着一艘宇宙飞船和发射架,在闪着光的白色星星下面。再用绿色的冰霜写上“斯科蒂”这个名字,就像它是宇宙飞船的名字一样。
当这位母亲对他说斯科蒂就要八岁了时,面包师若有所思地听着。他年纪很大了,这个面包师,他穿着一件古怪的围裙,很厚重,围裙的带子从他胳膊下面穿过去,再从后背绕到前面来,在那里打了个很大的结。他一边听她说话,一边不停地在围裙上擦手。在她研究样品和说话时,他潮湿的眼睛看着她的嘴唇。
他没有催促她。他一点都不着急。
这位母亲定了那个宇宙飞船蛋糕,她给了面包师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蛋糕会在星期一早晨做好,离下午的派对有足够的时间。面包师愿意说的就这么多。没有客套,只有简短的交谈,最基本的信息,一点不必要的东西都没有。
星期一早晨,这个男孩在另一个男孩的陪伴下走着去上学。两个男孩来回传着一袋炸薯片,生日男孩想套出另一个男孩给他的礼物是什么。
在十字路口,生日男孩没有看就走下了人行道,他立刻被一辆车撞倒了。他侧身摔倒在地上,头落在了排水沟里,腿却在路上动着,像是在爬一堵墙。
另一个男孩拿着炸薯片站在那里。他在想是否要把剩下的吃完,还是继续去上学。
生日男孩没有哭,但他什么也不想说。当另一个男孩问他被车撞到后有什么感觉时,他没有回答。生日男孩爬起来,转身往家走。另一个男孩和他挥手告别,向学校走去。
生日男孩告诉了他母亲发生的事情。他们坐在沙发上。她握着他的手,把它放在她的大腿上,就在这时,男孩抽出他的手,仰面躺了下来。
当然,生日派对没有举行。生日男孩住进了医院。母亲就坐在病床旁,她在等着男孩醒过来。男孩的父亲从办公室匆匆赶来。他坐在男孩母亲的旁边。所以现在他们俩都在等着男孩醒过来。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后来,男孩父亲回家去洗澡。
这个男人从医院开车回家。他开得比平时要快。到目前为止,生活算是一帆风顺。工作、做父亲、有了家。这个男人一直很幸福和幸运。但现在恐惧使他想洗个澡。
他拐上了自家的车道。他坐在车里,想让自己的腿恢复正常。孩子被车撞了,他住在医院里,但他会好的。他下了车,向前门走去。狗在叫。电话铃在响。在他开门和在墙上摸索灯开关时,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停。
他拿起话筒。他说,“我刚进门!”
“这儿有一个还没有取走的蛋糕。”
电话那端的声音就说了这么一句。
“你说什么?”男孩的父亲说。
“蛋糕,”声音说道。“十六块钱。”
这个丈夫把听筒贴近耳朵,想弄明白。“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少跟我来这一套。”声音说道。
这个丈夫挂断了电话。他走进厨房,倒了点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
孩子的情况没有变化。
在给浴缸放水时,男人往脸上抹上肥皂,刮了胡子。电话铃响起时,他正躺在浴缸里。他爬起来,快速穿过房间,嘴里说着,“真蠢,真蠢。”因为如果他在医院里呆着,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他拿起话筒,大喊一声“喂!”
那个声音说,“已经好了。”
午夜过后,孩子父亲回到了医院。他妻子正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她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又回过头来看着孩子。一个装置上吊着一个带管子的瓶子,管子的一头连着孩子。
“这是什么?”男孩父亲说。
“葡萄糖。”男孩母亲说。
丈夫把手放在女人的脑后。
“他会醒过来的。”男人说。
“我知道。”女人说。
过了一会,男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在这儿呆着。”
她摇摇头。“不。”她说。
“真的。”他说。“回家休息一下,不要太着急了。他只是在睡觉而已。”
一个护士推开门。她来到病床跟前,冲他们点了点头。她从被子下面拉出他的左臂,把手指搭在他手腕上。她把手臂放回到被窝里,在一个和床连着的夹板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样了?”母亲说。
“稳定。”护士说。接着她又说,“医生很快就会过来。”
“我在说她也许应该回家休息一下。”男人说。“等医生来过以后。”他说。
“她可以这么做。”护士说。
女人说“先看看大夫怎么说吧。”她把手放在眼睛那里,头微微向前倾着。
护士说,“那当然。”
父亲盯着儿子看着,小胸脯在被子下面一起一落。他越来越害怕了。他开始晃动自己的脑袋。他对自己说,这孩子没事,他没有睡在家里,而是睡在了这里。在哪儿睡不都是睡。
医生进来了。他和男人握了握手。女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安,”他边说边点头。医生说,“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怎样了。”他来到病床边上,摸着男孩的手腕。他翻开一只眼皮,然后另一只。他掀开被子,听了听心脏。他用手指在身体上到处压了压。他来到床脚处,研究起表格来。他记下时间,往表格里写了点什么,然后留心地看着男孩的母亲和父亲。
医生是一个英俊的男子。他的皮肤湿润,晒成了棕褐色。他穿着三件套西服,鲜艳的领带,衬衫的袖口带着链扣。
男孩母亲对她自己说。他刚从一个有观众的地方赶过来。他们给他发了个奖牌。
医生说。“没什么好说的,但也没什么好紧张的。他很快就会醒过来。”医生又看了一眼男孩。“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就会更清楚了。”
“哦,天啦。”安说。
医生说。“有时你能见到这样的情况。”
父亲说,“你不会称这个为昏迷吧?”
他等着,他看着医生。
“不会,我不想称这个为昏迷。”医生说。“他处在睡眠中。这是一种复元措施。身体在做它该做的事情。”
“是昏迷,”母亲说,“某种程度上的。”
医生说。“我不想这么称它。”他拿起女人的手,轻轻拍了拍。他和她丈夫握了握手。
女人把她的手指放在孩子的前额上,在那儿放了一会儿。“至少他不在发烧。”她说。她接着说,“我不知道。摸摸他的头。”
男人把他的手指放在孩子的前额上。男人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样的。”
女人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她回到椅子那里,坐了下来。
丈夫在她身旁的椅子坐下。他想说点什么,但他说不出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腿上。这让他觉得自己在说着什么。他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不说话。他时不时地捏一下她的手,直到她把手抽开。
“我一直在祷告。”她说。
“我也是,”男孩父亲说。“我也一直在祷告。”
一个护士回来检查了一下瓶子里液体的流动。
进来一位医生。说了他叫什么。这个医生穿着双路夫鞋①。
“我们要再带他下楼去拍几张片子,”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扫描。”
“扫描?”男孩母亲说。她站在病床和这个新来的医生之间。
“这没什么。”他说。
“我的天啦。”她说。
进来两个勤杂工,他们推着个像床一样的东西进来。他们拔掉男孩身上的管子,把他搬到那个带轮子的东西上。
他们把生日男孩送出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母亲和父亲跟着勤杂工进到电梯里,上楼送男孩回病房。家长们再次坐在了病床旁自己的位子上。
他们等了整整一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医生又来过,又对男孩作了检查,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后离开了。医生和护士走进走出。一个化验员进来抽血。
“我不明白这个。”母亲对那个化验员说。
“医生的指示。”化验员说。
母亲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开着灯的车子开进开出。她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沿上。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们遇到问题了,很严重的问题。
她害怕了。
她看见一辆车子停了下来,一个穿着长外套的女人上了车。她想让自己相信她就是那个女人,相信自己正开车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地方。
医生进来了。他看上去比过去更健康了。他径直走到床前检查男孩。“他的迹象很好。一切都没有问题。”
男孩母亲说,“但他一直在睡觉。”
“是的。”医生说。
她丈夫说,“她累了。她还饿着了。”
医生说,“她应该休息。她应该吃点东西。安。”
“谢谢你。”丈夫说。
他和医生握了握手。医生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离开了。
“我觉得我俩中的一个应该回家照料一下,”男人说。“狗要喂一下。”
“给邻居打个电话,”安说。“如果你请他们帮忙,有人会去喂他的。”
她在考虑找谁。她闭上眼睛,累得什么都不想去想。过了一会儿,她说,“也许我去吧。也许我不一直坐在这里看着他,他反而会醒过来,也许是我一直看着他,他才不醒过来。”
“可能是这样。”丈夫说。
“我回家洗个澡,再换身干净衣服。”女人说。
“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男人说。
她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皮包,他帮着她穿上了外套。她走到门口,转身回头看了看。她先看了看孩子,然后看着他父亲。丈夫点点头,微笑了一下。
她经过护士室,走到走廊的尽头,找着电梯。在走廊尽头,她转了个弯,看见一个不大的候诊室,里面有一家子黑人,都坐在藤椅上。一个男子穿着咔叽布的衬衫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大块头妇人穿着家常的衣服和拖鞋,一个姑娘穿着牛仔裤,头发梳成十来根卷曲的小辫子。桌子上面堆满了薄的包装纸、泡沫塑料杯子、搅咖啡的棍子和小包的盐和胡椒。
“尼尔森,”大块头妇人惊声说道。“是不是尼尔森?”
妇人睁大了眼睛。
“现在就告诉我,女士,”妇人说道。“是不是尼尔森?”
妇人试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但那个男子按住了她的胳膊。
“别急,别急,”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男孩母亲说。“我在找电梯。我儿子住在医院里,我找不到电梯。”
“电梯在那边。”那个男人说,用手指向右一指。
“我儿子被车撞了,”男孩母亲说。“但他会好的。他现在处于休克状态,但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昏迷。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昏迷。我要出去一下,也许去洗个澡。但我丈夫在陪着他。他在看着他。有可能我走后一切就会改变。我叫安?维斯。”
那个男人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子。他摇了摇头。
他说,“我们的尼尔森。”
她拐上车道。狗从房子的后面跑过来。他在草地上打着转。她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听着引擎发出的滴嗒声。
她下了车,来到前门。她打开灯,烧上沏茶用的水。她打开一听狗食喂狗。她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
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我!”她说。“喂!”她说。
“维斯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是我,”她说。“我是维斯太太,是和斯科蒂有关吗?”她说。
“斯科蒂,”这个声音说道。“是和斯科蒂有关。”这个声音说,“这个和斯科蒂有关,是的。”
① 路夫鞋(loafer),一种矮帮休闲皮鞋的商标。
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比尔·贾米森一直是杰瑞·罗伯茨最好的朋友。两人在南区一个靠近旧集市的地方长大,一起读完小学和初中,然后一起去上艾森豪威尔高中,他们在那儿尽可能选同一个老师的课,换穿对方的衬衫、运动衫和紧腿裤,约会和睡同一个姑娘——怎么方便怎么做。
夏天他们一起去做工——浇灌桃树、摘樱桃、穿晒啤酒花①,任何能赚点小钱、又没有老板在屁股后面盯着的事情。他俩还合买了一辆车。高中最后一年前的夏天,他们凑了钱,花三百二十五块买了一辆54年的红色普利茅斯。
他们伙着用那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杰瑞在第一学期结束前结了婚,退学在罗比超市找了份正式的工作。
至于比尔,他也约会过那个姑娘。她叫卡罗尔,和杰瑞过得很好,比尔一有时间就上他们那儿玩。有了结了婚的朋友,让他觉得自己变老了。他去他们那儿吃中饭或晚饭,大家在一起听埃尔维斯②,或者是比尔?海利③和他的彗星乐队。
有时候,卡罗尔和杰瑞当着比尔的面就亲热起来,因为公寓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客厅里那张平时收着、可以放下来的床,比尔不得不找个借口出去遛一圈,去迪松加油站买点可乐回来。有时卡罗尔和杰瑞会跑进卫生间里,比尔不得不去厨房,假装对碗柜和冰箱感兴趣,而且没有在听。
他去他们那儿没有那么频繁了。六月份他毕了业,在达瑞果德④的一个工厂找了份工作,加入了国民警备队。一年后,他有了自己的送奶路线,和琳达的关系也确定下来了。比尔和琳达会去杰瑞和卡罗尔那里,喝啤酒,听音乐。
卡罗尔和琳达相处得很好,当听到卡罗尔私底下说琳达是个“真实的人”时,比尔很开心。
杰瑞也喜欢琳达。“她很棒。”杰瑞说。
比尔和琳达结婚时,杰瑞是男傧相。婚宴当然设在唐纳利旅馆。杰瑞和比尔在一起胡闹。他们勾肩搭背,一杯接着一杯地干着鸡尾酒。这期间,比尔有一次无意看了一眼杰瑞,觉得他看上去很老,比二十二岁要老多了。但那时杰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已被提拔成罗比的助理经理,而且,卡罗尔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他们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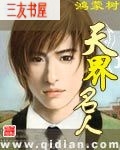
![[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