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一丁点好处。
①威纳奇,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
②切努克风是北美落基山脉东坡的一种干暖西南风。它导致气温快速上升,落雪迅速融化。
严肃的谈话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来自薇拉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劵。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来自女儿。一支圆珠笔来自儿子。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呆着的地方。他喜欢呆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一小块带着锯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①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领口的浴袍,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开吵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了。”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到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这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这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呆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②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档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①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 ②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
平静
我那时正在理发。我坐在理发椅上,有三个男人沿着墙根坐在我对面。①这等着理发的男人有两个我以前从没见过。但我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尽管我不能确切地想起在哪里见过他。理发师在我头上忙活时我一直在看着他。那人把一根牙签在嘴里弄来弄去。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有着短短的卷发。然后我想起那天看到他一身制服制帽的打扮,在一家银行的门厅里,小眼睛很警惕的模样。
另外两个,一个年龄相当地大,满头的灰卷发。他正在吸烟。第三个男人,猜想年龄不会很大,却几乎秃顶了,两边的头发垂挂在耳朵上面。他穿着伐木鞋,裤子沾着机油,油亮亮的。
理发师一只手放在我头顶,把我转过来细细端详。然后他对那个门卫说,“你打到鹿了吗,查尔斯?”
我喜欢这个理发师。我们不很熟悉,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当我进来理发,他就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常去钓鱼,所以我们会聊一聊钓鱼。我认为他以前没有打过猎。但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在这点上,他是一个好理发师。
“比尔,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事儿却又糟透了。”门卫说。他取出牙签将它放在烟灰缸里,摇摇头。“我既打到了又没有打到,所以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声音。对一个门卫来说,这种声音不适合。这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
另外两个男人抬起头。年长者正翻阅着一本杂志,吸着烟,另一个小伙子正拿着一张报纸。他们放下手中看的东西,转过头来听门卫讲。
“接着说,查尔斯,”理发师说,“让我们听听。”
理发师又把我的头转了一下,继续用剪子剪。
“我们上了魔岭。老爷子,我,还有小家伙。我们去打那些鹿。老爷子守在岭那边,我和儿子守在这边。孩子那天醉了一夜,看起来糟透了。他脸色发青,喝了一天水,把我和他的都喝了。那时已到了下午,
我们天刚亮就出来了。但我们还盼着,指望岭下的猎人能把一些鹿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听到谷底的枪声时,就坐在一根木头后边,观察着猎物。”
“那深谷下边有几处果园。”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有些坐立不安,把一条腿架着,将他的靴子晃了一会儿,又换另一条腿架上。“那些鹿总在那些果园附近走动。”
“说得没错,”门卫说。“它们在晚上遛进园子,这些杂种,它们吃那些没熟的小苹果。哦,对了,后来我们听到枪声,一只又大又老的公鹿从不到一百英尺远的矮树丛钻出来,我们就坐在那儿严阵以待。孩子和我同时看见了它。当然,他马上卧倒在地开始射击。这个木头疙瘩。那只老公鹿根本没事,结果我孩子根本没吓着它。但它已分辨不出枪声来自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向哪一边逃。然后,我打了一枪,但慌乱中,我只把它打晕了。”
“把它打晕了?”理发师说。
“你知道,把它打晕了。”门卫说。“一枪打在肚子上。就像是这一枪把它打晕了。于是它垂下脑袋开始这样颤抖,它全身都在颤抖。孩子还在射击。我,我感到我就像回到了朝鲜。于是我又开了一枪,但没有射中。随后那只老公鹿先生又挪回了灌木丛。但是,现在,上帝作证,它已经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孩子瞎打一气,把该死的子弹也打完了。但是我确实打中了。我把一颗子弹射进了它的肚子。我所说的把它打晕了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呢?”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把报纸卷起来,轻轻地敲着他的膝盖。“后来呢?你一定去追它了,它们每次都找一个难以发现的地方去死。”
“但你追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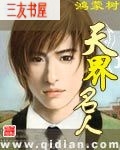
![[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