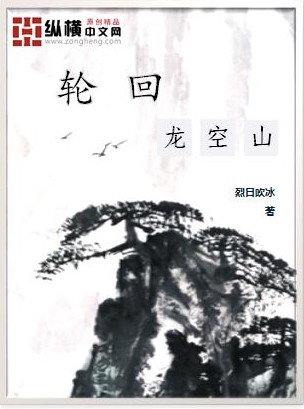空山疯语-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采,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1998年收到第一张圣诞卡之前
(此文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杂文报作品选》。)
“共和国”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现在各地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庆典活动,广电报刊也不断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我相信今年的国庆一定会办得庄严隆重,有声有色。可是近日来,我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词汇被频率越来越高地使用和传递着,那就是“共和国”三个字。什么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诞辰,共和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共和国的未来,共和国的花朵,献给共和国的礼物,捍卫共和国的尊严,共和国是我的母亲,共和国呀你听我说……这些“共和国”,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祖国”的代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代称是不合适,不妥当的。目前全社会的语言使用状况,极为混乱,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一个干涉一个。但是“共和国”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称号的严肃问题,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和一个文化工作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使我发生困惑的问题提出我的质疑。
首先,“共和国”不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简称为“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是君主国的对称,有时亦叫做“民主共和国”,指的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即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如今全世界以“共和国”为国名的国家共有120多个,占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如果号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儿女”,那么你是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儿女,还是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儿女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提议国名叫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在讨论中,多数人觉得有些拗口和啰嗦,后来就采用了张莫若的建议,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它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我爱共和国”,那并不意味着你爱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只说明你不爱君主专制,爱民主选举。
其次,有些国名中不含“共和国”字样的国家,其政体性质也是共和国。比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时,大量使用的就是“共和国”的概念。20年代130年代的学校教材,就叫做《共和国民教科书》。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法学意义在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政体上的共和国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笼统地歌颂“共和国”那将意味着歌颂封建王朝结束以来的所有岁月,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其中的“中华民国”还包括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中华民国等等。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1949年建立的国家,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俗称可以叫“新中国”,如果叫“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可以,但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头几年,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好像是从《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开始,“共和国”一词时髦起来。在写歌作诗等特殊语境中,偶尔这样一用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是许多主持人,还有领导干部,一口一个“共和国”,实在令人费解。用“共和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不妥,代替“中国”或“祖国”就更加不妥,因为“中国”和“祖国”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不爱封建时代的政体,但封建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仍然是热爱的。所以我希望举国上下慎用“共和国”一词。也许我说晚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惯性已经彻底强暴了“共和国”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我们这个人人怕提意见,大家都等着领导来解决一切的国度里,我也只好寄希望于哪位负责的“共和国领导”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组织专家研讨一下,不要再让那些追逐时髦语汇的人们顺口胡说下去了。特别是到了国庆大典上,千万不要喊什么“共和国万岁”,否则就太让人遗憾,太让人笑话了。
(此文发表于《中华儿女》号外。)
人文学者的道义
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19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度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将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的。
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20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20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党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党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变为党的同路人,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暖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进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份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