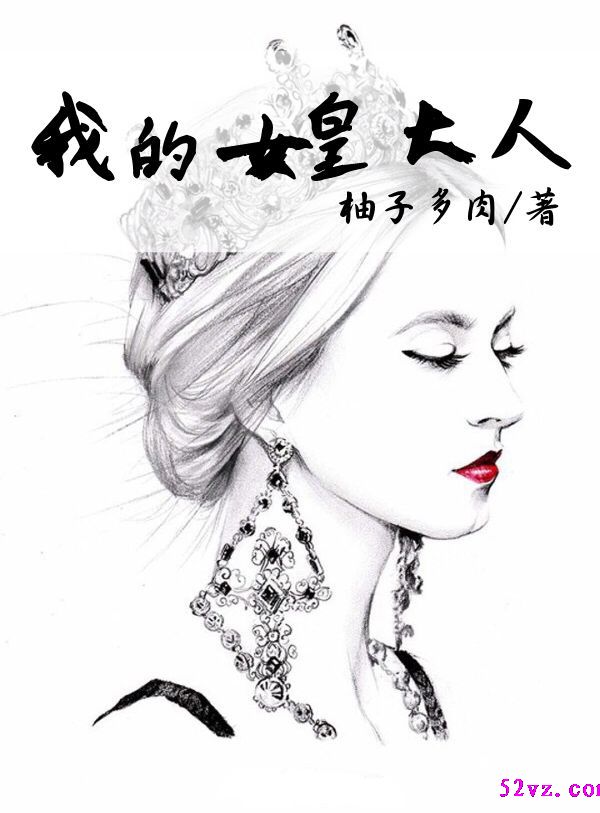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冶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性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红卫兵来了,为数甚众,嘭!嘭!嘭!响声惊醒了每一个人。〃开门!〃〃快点儿!快点儿!〃沉住气,越慌乱事情就变得越糟。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皮带解了下来,绳子和手铐也都备齐了。搜捕令?没必要,有人坦白交待了,法律不再保护我们。抽屉拉出来了,箱子打开了,东西倒了一地,他们逮捕了父亲,他们逮捕了我,把我们押上因车,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解放前国民党用来抓人的。〃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哭,坚强些!黑暗就快过去……〃
黑暗。我被黑暗完全笼罩住,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到血腥味儿。我的眼睛瞎了么?严刑拷打……实在是不堪忍受……我的血肉之躯……但是我必须坚持住,不能让同志们遭殃。
〃我得讲实话,不能无中生有!〃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决不出卖同志!
他们在父亲面前拷打我,他们拷打父亲……拷打我……父亲……我失去了知觉,两眼漆黑,从高山之巅跌下落入万丈深渊,像一片羽毛,飘忽而下。气流摆动。晕眩……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毛泽东……〃
噢,真倒霉!我刚要睡着,这首曲子就响了起来,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得很。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不让人有片刻喘息……。现在我真烦透了这首曲子,以前我对它曾那么钟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红卫兵,阶级敌人……大概没有一个反革命有我这么痛恨这首曲子。这不是音乐,这是对人的摧残,我卧室窗外的松树杆上给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曲子就从里面没遮拦地泄出来。它快把我弄疯了。这所学校还有没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受高音喇叭搅扰的?恐怕没有。
黎明时分,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这首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老师、学生、工人、家属,都不得不就此醒来。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东方一红,每个人都必须早起。
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一巳开始,没两小时别指望它停下来。乐曲过后紧接的是新闻联播,然后是本地新闻,各种声明、宣言、通令、最后通牒、节选的大字报等等,没完没了。
我的头用被子蒙住,藏在枕头下,还是不管事,声音硬是钻进耳朵里去。我的脑袋像是一个战场,顽固的声波和我的瞌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搅得我头疼欲裂,忿火中烧,神志濒于崩溃。
〃打倒某某某!
〃砸烂某某某狗头!〃
我恨不得砸烂这个喇叭!把它踩扁,踢出墙外。这下它就哑巴了,让它躺在阴沟里像个没人要的夜壶,让它烂掉……
〃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革命人民……提高警惕!〃
〃反对……破坏……阶级敌人……〃
如果他们逮住我砸这个喇叭,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现行反革命,当场抓获。他们会开我的公审大会,游街,判处死刑……那又如何?完事之后,砰地一声,一了百了。死人可就听不见音乐,我于是长眠不醒,多美妙!
这个学院的红卫兵司令,他居然也会自杀。这件事神神秘秘,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准是这病把他逼疯的,不然一个四岁的有为青年,率领着学院里上千名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怎么会从校园主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而下?在一个绚丽的早晨,在一大群目瞪口呆的观众面前,他扑向绊红的云际,以一个极漂亮的跳水动作落下,像是要夺取一枚奥林匹克金牌。他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坠落在20多米下的水泥道上,目睹的人都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手臂折断了,头骨摔破了,颈椎错位了,大量内出血,但他却没有马上断气。他大口喘气,大声呻吟,疼得全身是汗。人们将他送往医院,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死了。这两小时一定是他长眠之前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如果魔鬼能教我怎样使这个喇叭沉默,我情愿把灵魂出卖给它。使它接触不良?从里边切断它的金属线?拉掉它的磁铁?……怎么才能爬到树上去呢?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最好?午夜过后,星月无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你们干嘛不教我几个恶毒的诡计!
我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有许多荒诞不经。幸好我还残留了一点儿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两小时后,广播冲破了我瞌睡的防线,我起床了:头重脚轻,睡眼朦胧。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16 〃壮士一去不复还〃
失眠症缠了我一年半,到了1968年6月,我再也不愿受此煎熬。我对自己说,得想点什么办法改变一下现状。这点办法便是自愿报名到东北的一个农场去,那地方人称〃北大荒〃。
我用〃自愿〃这个词,是因为我这番下乡还不同于后几届的中学毕业生,在1968年那会儿我们仍有选择的余地:不愿远行的可以留在北京。当然,分配的工作不是什么叫得响的,也就是补补鞋子,修修自行车,扫扫街道,卖卖豆浆油饼之类,而且共事的多是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头儿老太太,典型的〃小市民〃。这些人鸡毛蒜皮的事可以从早聊到晚,茶杯里都能掀起风暴。我想到这样的前景就不寒而栗。原本以为考人了一零一中就可以永远告别这种生活,谁又料到5年后我仍旧摆脱不了它的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北大荒。
于是我选择了北大荒。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殊死的战斗……
死?我倒不怎么怕。与其一天天地熬这漫漫长夜,倒不如轰轰烈烈像个荚雄似地去赴死。最近我的身体每况念下,生病令我心烦,父母令我心烦,小炼和小跃更是令我心烦。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呆下去,呆着徒然浪费时间。是该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父亲。母亲。小炼、小跃从西郊过来,二姨从市里她自己家中过来,还有几个同学。吴当然没露面,我记不太清同学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