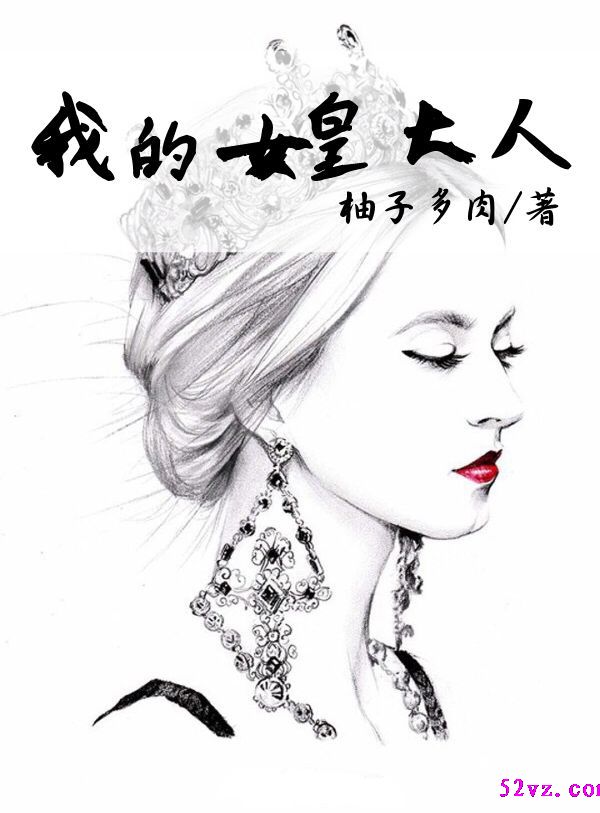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村民们说在1960年那会儿常看见陈晚上背了东西去赵家。到了陈要受处分了,赵马上将陈和养猪场的头儿对调一下职务。事儿就这么结了。
我耳闻目睹赵的这些行径,暗暗掂量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下现状。如果现在还是1966年,一切都好办得很,动员农民,揭发赵,定他个走资派,夺了他的权。可惜今时非同往日,我们不再是红卫兵,而是来这儿改造思想的知识青年,赵则代表了当地党组织。但他是这么个土皇帝!我们看着他滥用职权,欺压贫下中农,难道只能置若罔闻么?若要和他斗法,又能怎么斗呢?手中没有了尚方宝剑,我们还不是和村民们一样无权无势?思来想去,我们斗不过姓赵的,这种念头纯属心血来潮,打消它吧。
我主意已定,远离赵和村民的是非,但有了这个主意并不管用,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毛主席说得不错,〃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比喻说的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躲都躲不了。
10月底的一天,赵突然把我找去了。他找我有何责千?这有点不同寻常。我想不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还是小心为妙。
我到了他家,这次他颇有礼貌,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哈!他上次对北京知青也这般招呼,他便不会丢面子了。
〃你来这儿3个多月了,农场工作很辛苦,是吧?〃他发问。
〃嗯哪,不过现在慢慢习惯了,有点摸着门路了。〃
〃除了体力劳动,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你的思想呢?有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你对我说,我也许能帮你解决。明白么?〃
赵今儿是怎么啦?他像是变了个人。他究竟是什么意图?该不是意识到不应和知青过不去,想要挽回影响,巴?但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又没在那一伙找他汇报思想的人中。
〃我每天都读毛主席著作,它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要是将来我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来请您帮助的。〃
〃你对村里的领导没什么意见么?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在我面前应该实话实说。〃
〃我知道,我想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对领导提意见。〃
话说到这会儿,赵似乎没着儿了,他沉默了几分钟,突然发话:
〃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没意见,那你为什么说你在这儿是个劳工?〃
〃劳工?〃这话从何说起?我大吃一惊,〃我没说过这种话。〃当然没说过!我怎么会这么说?劳工指的是那些日本侵略期间被日本人抓来做苦工的中国老百姓。很多人死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
〃你保证你没说过这话?可是你写过这样的话!白纸黑字,还能抵赖?〃
他的小眼珠斜着看我,尖锐得跟钉子一样,似乎要在我的身体和灵魂钻出洞来。
〃我在哪儿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我的声音都发抖了。〃你最好自己想想。〃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有这种事。〃
〃就在你前几天填的表格里。你在你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劳工!〃
表格!该死!真有这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填的。想想这种表格没什么太重要,也忘了检查一遍。我好蠢!
〃我写的是农工,不是劳工,如果写错了,一定是笔误。请让我看一下儿我那张表好吗?〃
〃不行,表格已经送到场部去了。现在这份表格很可能在虎林县公安局手里。〃
我的心猛往下沉,知道自己闯祸了,这祸还闯得不轻。我一时语塞。
〃现在你仔细听着:你要好好深挖思想根源,问问自己是否对现实不满,是否对党把你送到农村来有怨言。〃
〃我是志愿来的!我热爱党和毛主席!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止不住浑身颤抖,房间的温度似乎突然降到了零下40度,从骨头里透着寒意。我使劲咬着嘴唇,不让牙齿咯咯作响。〃
〃革命干部家庭?哼!我告诉你吧,从现在起,北京来的青年,家庭成分得看三代。不单看你父母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还得看你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你祖父解放前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但是如果你祖父是贫农,到了你父亲成了地主,你的成分还是地主。〃
这又是当头一棒!我脚下的地似乎正在崩溃,突然我好想放声大哭。但我不能在赵的面前哭!我不能让他看出我心里害怕。完了就完了,我不必再给他提供弹药来朝我开枪。我默不作声。赵过了一会又说:
〃你回去想想问题的根源,随便说一句,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笔误!写一份自我检查,你应该清楚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谈话结束了,我走了出去。全身怪怪的:手脚冰凉,面颊发烧,失神的双眼呆呆直视前方,仿佛看到了万丈深渊,我正站在其边缘。
过去我耳闻目睹了很多人因口误或笔误而在眨眼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小唐是最近的例子。在他之前是张,一个1964年来凉水泉的北京知青。〃文革〃爆发后有一天,他在场部废弃的图书馆里拿了一本百科全书。在书里他看到国民党的党歌,便哼起来。有人叫他不要哼,他面子上一时下不来,便和别人争辩说国民党在孙中山建立初期是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首歌一度是革命歌曲。就因这几句话,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不许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工资降到了一个月18元。打那时起,他就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难道我也要步他后尘么?果真如此,我这辈子便算交待了。更糟的是,我还会累及家人,父母定会受牵连,小炼和小跃的前途也被我毁了。二姨呢?我会伤透她心的。我们全都完了,赵就是要看我们的好戏,这条毒蛇!
〃杀鸡给猴看〃,老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他能把我打成反革命,其他北京知青都会被震慑,被打断脊梁,从此俯首帖耳,没人再敢挑战他的权威地位。这一群傲气十足的前红卫兵,曾领受毛主席的御旨走遍全国,到处掀起红色风暴。我们对他和他的小独立王国该是多大的威胁。即便没人提到他的级别,仅是我们的存在也足以使他晚上睡不着觉……
门岁的年纪,我对政治还不是一无所知,我想自己是被选来做靶子了。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同伴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能意识到我刚才想的这些,我还有希望,否则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边盘算边回到宿舍。一进门我就趴在床上嚎啕大哭。我的舍友都紧张起来,她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于是和盘托出。她们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马上就有一群北京知青聚集在我们房里商量,这些人是我们的智囊团,大家得出结论赵在故意挑衅,此举并非针对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北京知青。如果我们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我算走运,知青伙伴也都有些政治头脑。
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听到赵想查三代来改我们的家庭出身,都觉得气愤不堪。高于子女中不少祖父一辈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的心病。
〃按赵的说法,毛主席的孩子也是富农啦!如果周总理有孩子,那他们不都是资本家?这有多么荒谬!赵的这个发明简直反动透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北京的知青同伴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他们向村里所有领导讨个说法。(当时村里还有一位队长,八九位副队长。)他们要求领导对我的错误性质作明确表态,并澄清我们的家庭出身。如果村里的领导不及时作出回应,我们就把问题捅到场部去。
几天后,赵软了下来。接下去的会议上,他表示我的错误属于笔误,不是故意行为。而我们的家庭出身也维持不变。除了我们的团结外,还有一点可以解释我们的胜利,那就是又有一轮新的政治运动迫在眉睫。赵不想树敌过多,村里已经有不少反对他的人,叫他大为头疼。
我幸运地躲过一劫。太悬了,真可谓虎口脱险!好运气是北京知青同伴给的,村民在这件事中不置一言,沉默得像一座山。直到几星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态度。
几星期后,场部发了一个文,要求下属各生产队选派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选上的人会参加大会,四处巡回讲述他的心得体会。文件还说这位积极分子必须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于是整个生产队聚集在饭堂,干部、老职工、家属、知青,一人一票。黑板上写着几个候选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赫然其中。
不一会儿,投票就结束了,先选两人担任唱票的角色,又有一人负责在黑板上划〃正〃字,一票一笔。
唱票一开始,我就听到我的名字反复被〃唱〃到,很快,大厅安静下来,聊天的声音也轻了许多,人人都竖起耳朵,他们听出了弦外之音,黑暗中,人们眼睛在闪光。我得了这么多的票!我的名字回旋在大厅里,像一阵春风,传递着一个秘密的信息。在场的人,不论喜欢与否,都得到了这个信息。冰消雪融,大地解冻了。多数人心花怒放,少数人垂头丧气,最后我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默默显示了村民抗衡赵和他一伙的力量,他当上皇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不出所料,下一轮政治运动来临时——我甚至都记不得是什么运动了——赵被人从皇帝宝座上拽了下来,免除了官职。往后3年,轮到他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他的罪名之一是迫害知青,相应的另一罪名是干扰学生上山下乡运动。
其他人还在村里与赵斗法时,我已开始在美丽的乌苏里江畔巡回讲用,受到英雄人物一样的礼遇。事情的结局如此,我满意么?当然!但我是否愿意被历史或命运再次选择扮演英雄角色呢?一百个不!
我心里明镜似的,在整件事中,我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傀儡。木制的傀儡受人摆布,却没有思想和感觉,而我清楚知道危险所在。我其实怕得要命,如果说坐过山车令我胆战心惊的话,那么在中国,卷入一场这样的政治风波要骇人十倍。坐过山车,至少我还知道它往哪儿开,也明白这游戏其实是有惊无险,一会儿我就能毛发无伤地从车上下来。而在政治运动中,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保障。几年来,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说真话,那时我就开始厌倦了政治斗争,发誓将来离它们远远的,而且我得小心检查我写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不是闹着玩的!
尽管我决心远害全身,但当我一回到凉水泉,我便知道要退出政治谈何容易!对反叛者来说,半途而废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推翻了赵,还得清算他的影响,他的有些亲信仍占据着重要岗位,大权在手,等他们的主子卷土重来。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主动对新来的严指导员提出去养猪场工作。
这一决定有两重意思:其一,我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力干全农场最脏最累的活儿;其二,去养猪场意味着与陈较量,这几年陈一直是赵的死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得低首下心,忍辱负重,先学会怎样管理猪号,不久我们就会把他取而代之,把权力归还人民。
人算不如天算,我万万预见不到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刚到猪号与陈接触时,我对他毫无幻想可言,他是赵的心腹,与赵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政治上他是我们的敌手,但他又是一个贫农,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一个已婚的40来岁的男人,3个孩子的父亲。在我看来,他是个势力眼、狗腿子,狡猾奸诈,利欲熏心。我应该像很多村民一样对他嗤之以鼻才对。
荒唐的是我在养猪场干了几个星期,竟发现自己整天做着关于他的梦。还不单止梦到他,更梦见那些两人之间夜里才发生的事。这多半在我值夜班的场合,孤身一人睡在猪场当中的小屋里。这儿,炕是热的,是陈和我一起砌起来的,很棒的一张炕!夜深时分,这张炕挡住户外的冰天雪地,使得小屋温暖如春。
一片漆黑,夜无边无际。狗悄没声的,猪也不闹。事先全无征兆,小屋的木门突然开了,他走了进来。我的心凝住了,整个人呆若木鸡。叫喊是没有用的,村里不会有人听得见。他抓住我,把我拽进怀里。他热得像火,而我却软得像水。他的整个儿身体都在燃烧,我的力量挥发殆尽,无力挣脱。他把我压在炕上,重得跟一座山似的,那胀胀的东西擦着我的双腿。他撕开我的衬衫,拉下我的内衣,我赤身裸体,他就要来了!我是刑场上的囚犯,喘着,战栗着,怀着痛苦的想望,等着最后致命的一击。
我的小洞穴有如洪水泛滥。我扭动身子,狂乱地缩紧肌肉,关上那扇门,想把强暴者关在体外,保持我的贞洁!但强暴者硬挤了进来。粗大、炽热、充满野性……现在再抵抗也无济于事,让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巴。我总是被糟蹋了,完事后我得自杀,但此刻我身在九天之上,龙凤纵舞,欢情无限。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我的灵与肉都耗尽了,以后的事,由它去,巴……
如果陈对此有所觉察,他也许会来强奸我而不是老眯子。如果他真的来,后果会怎样?最有可能的是我会动用那把藏在身上的剪刀,让他的血或我的血染红那张炕。谁知道呢?我也许迷了心窍,发生在老眯子身上的一幕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有时我怀疑陈对我的内心活动并非毫无党察,也许这是他预谋的一部分,他设了一个圈套,让我和其他在猪场干活的知青往里钻。又或者我高估了他,他并没有这么多心计,只是猪号活计的性质影响了我们的身心。
在猪号里我们干的什么活儿?每天我们都得密切注意发情的母猪,确保它们和公猪正常交配后全都怀胎。到了产期,我们把猪崽接生下来,为幼猪找到奶头,看它们吃奶……
这活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