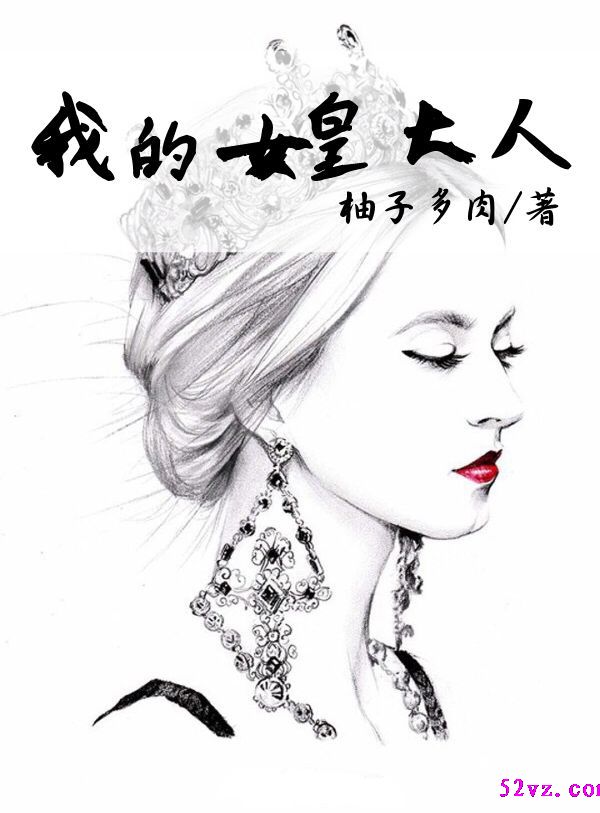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作者:杨瑞-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
〃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因为他们也是爱我的,但他们对我的评价建立在我是否真正优秀的基础上。
二姨对我的爱全然不同。哪怕我命途多舛,哪怕我被法庭判罪,哪怕我遭全世界唾弃,她对我的爱不会稍有动摇。甚至,她会比从前更怜惜我,以补偿我在别人那儿受到的冤屈。她只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从不起二心。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最杰出的。她对我的爱是盲目的,简直不可理喻。人们会说这种溺爱足以宠坏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正是她的这种爱拯救了我。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许,我如何忍心让她失望!
当我明白了这点,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行将灭顶的人突然踩到了一片坚实的陆地,恶梦逐渐消退,宁静重新回归。我不再因别人的幸运而心怀妒忌。他人纵有金山银山,我自有我的一方永不沉没的小岛,在她绿色的港湾里,静静停泊着我的心灵之舟。在她的甘泉滋润下,我可以放松休想,恢复信心,获取力量。以前我也许失去过一个家,如今我又找回了自己的家园,这么安全,这么美好。我知足了。
后来我向二姨坦白了偷钱的事。父母若是闻知此事,那还了得?他们非大发雷霆不可,二姨却平心静气地听完,对我说了朴朴素素的一段话:
〃你需要钱,拿我的去用。不过你得记住:将来要是你不得已跟别人借钱,千万不能忘了,而且你得尽早还给人家。过去我们家很穷,我对这种事特别当心。一个人受穷是她命不好,那也没什么。可一个人要是没有志气,不要强,那她就没出息,一辈子完了。〃
二姨说这番话时轻声细语,毫无造作,却在我心中镂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了我此后安身立命的指针。其实,真正教我如何为人处事的还是二姨自己前半生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耳熟能详,它在不觉中教我什么是自强,什么叫志气。除了自尊自爱,这故事还向我灌输了不少别的东西,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作为女子,贞节操守比眼睛更珍贵。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二姨姓田,名奚贞。一个贞字,暗合了她的品格。她生于1904年,那一年光绪帝还在位,大权却牢牢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二姨娘家上几代都是皇家工匠,他们祖传的手艺是搭席棚。夏季来临或有重要的活动,比如红白喜事,大户人家都要搭棚。在老北京,一家的席棚是否气派,显示了这家有无经济实力。对这类门面上的事,人们可津津乐道了。得了夸奖的人家洋洋得意,被比下去的则会感到颜面大失。
御用的席棚,勿庸置疑,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里也寄托着二姨家祖先的骄傲。〃席棚奚家〃在老北京遐迩闻名。满清时期,奚家隶属内务府,住在皇城外筒子河西边,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这样给皇上家当差的手艺人。
二姨小时候,邻居肯定短不了在背后嚼舌头,说奚家祖上不积德。所以一连生了5个女孩,到最后才得了个男孩,男孩长大了没什么出息,反是奚家这五千金,受了她们母亲的调教,个个心灵手巧。
她们的母亲也是手艺人家的女儿。跟奶奶家不一样,他们不是旗人,无权无势,唯有一技傍身。祖传的手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光宗耀祖之源。只要后辈肯学,家中就不愁没饭吃。在这个意义上,手艺便是这些匠人们的〃铁杆庄稼〃。
二姨的母亲多才多艺,她擅长的并非琴棋书画,而是些居家度日的技能。她有心把这些技能通通传授给几个女儿,但俗话说,〃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二姨的5个姐妹各各只领得了母亲的一招两招。
二姨的大姐长大成了烹饪里手;二姨排行第二,和四妹一样精于女工;二姨擅长裁剪,四妹擅长刺绣;二姨的三妹三十而殁,我还没出生;最小的妹妹做出来的点心则堪称一绝。
回过头看,二姨母亲教给女儿的手艺就是一份无形的嫁妆。若是她们嫁得个好人家,丈夫有身分有才干,那她们就安安分分做家庭主妇,这份嫁妆备而不用;若遇不测之风云,就像二姨的苦命,至少她们还能凭一双手养活自己。
二姨唯一的弟弟鹤立鸡群,从小受父母骄宠,又有五个姐姐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他去学堂读了几年书,因为日后要肩负承接香火和祖业的大任。而女孩则早晚是别家的人,替他人传宗接代。
二姨长到17岁,便许了人——父母将她许给〃饽饽田家〃。这家世世代代在宫廷里制造糕点,跟奚家可谓门当户对。男家着媒人前来提亲,二姨的双亲心中愿意,于是纳彩下定,单等择了吉日完婚。到这时,二姨未来的丈夫长的什么模样还全然不知,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