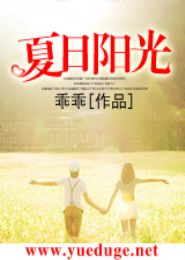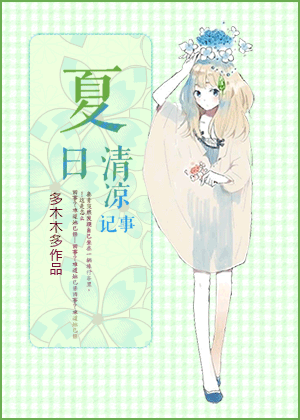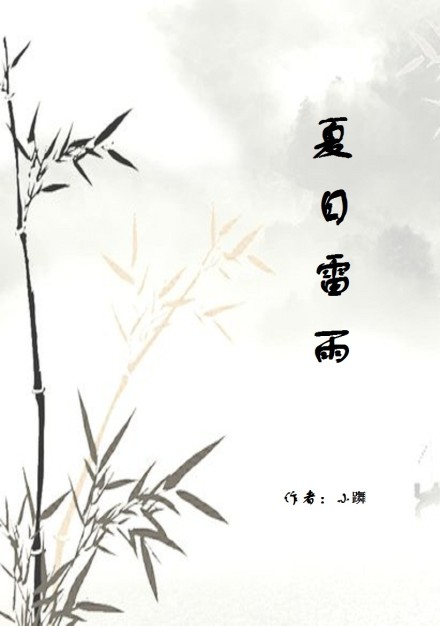夏日的列车 作者:刘惠强-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结婚的写在脸上。
自从铁路实行大提速以后,从铁道部到铁路局,各级领导不厌其烦地要求服务工作要上新台阶,要在微笑服务上下工夫,让旅客有上车跟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样的要求在旅客列车上自然是首当其冲——因为旅客列车是铁路的窗口单位嘛! 其实,窗口单位还有更重要的部位,列车上的重点部位就是软卧车厢。软卧车厢里乘客的身份一般和硬卧和硬座有区别,这里不是首长就是有钱人,层次相对高一些,所以,软卧车厢都要挑那些长得好、素质高的人担当列车员。冯秋云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可人长得漂亮也麻烦,冯秋云担当乘务工作几年来,遇到的麻烦事不计其数,看到的带着些暖昧的眼神数不胜数。有些旅客有事没事总要找她,或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在她的身边蹭来蹭去,好像碰她一下就能得到多少满足似的;更有甚者夜间居然不休息,坐在边座上一眼一眼地看她,那眼神像要钻进她的衣服里似的…”·开始冯秋云觉得这些人挺无聊的,时间长了她也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心想:也难怪,谁让你长得好看呢? 好看还不允许别人多看两眼? 这也是自然规律嘛……
有件事却让她至今难以忘怀。
那回,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乘坐这趟列车,可巧就是冯秋云负责的7 号车厢。那个乘客复姓司马,单名一个文字。司马文人长的没得说,一米八几的个头儿,不胖不瘦,鼻梁上架着副近视眼镜,是一副学者的模样。
这位司马先生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外企搞形象策划,收入自然不菲,他有个叔叔在香港,因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流落到海外,自己在香港经营着一家古玩玉器店。老司马先生经营有方,几十年来,把那个古玩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且越做越大,家产近亿。
只可惜老司马先生原来留在大陆的妻子“文革”
时死于非命,儿子也过早夭折,到了那边后再未娶妻生子,近年自己年事渐高,产业难找一个接班的人,后来他就把家产移到了司马文的名下。
两年后,老司马先生在香港去世,膝下家产全部归了司马文,这位小司马先生一夜间便成了香港有名的大老板。司马文事业心强。又经营着这么一家大的珠宝行,正可谓事业有成。因为生意太忙,司马文在大陆、香港来回跑,所以一直也没顾上自己的个人事情,一晃就到了三十岁。平时司马文到哪儿都是坐飞机,可这次到了北京,看到报纸上宣传说火车不但提了速,而且服务质量也是世界一流,他便突发奇想,要坐火车实践一回,就这样。他与软卧车厢的列车员冯秋云不期而遇……
时间匆匆流逝,司马文与冯秋云越来越熟稔,相互间了解得也越来越多。而且从那以后,司马文又几次乘坐冯秋云所服务的车厢。终于有一次他向冯秋云提出:要娶冯秋云为妻。冯秋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心里一下子没了底。到底自己该怎么办? 看样子这个司马文倒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可这种事她怎么拿得准主意呢? 万般无奈,她把这事和盘托给了徐雅娟,让徐雅娟给她拿主意。
徐雅娟觉得这事也是不好决断,一来那个男人她一点不了解,二来她也不知道冯秋云是怎么想的,所以便没有明确表态。可在徐雅娟的心里却有自己的看法:冯秋云肯定会嫁给那个司马文,这不光是因为司马文长得帅气,更是因为人家还是个有钱的大老板,即使人差点,她冯秋云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 再说,那个司马文看见冯秋云这样的姑娘能不肯花大价钱? 果然不出徐雅娟所料,没过几天,司马文便再次登上他们的列车,这回他居然提着20万美元的密码箱。他说:只要你冯秋云同意嫁给我,就给你在北京或上海开一家珠宝店,你自己当老板。再不用在车上辛辛苦苦挣这一千多块钱。
冯秋云的确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而且还是美元,她当时有点目瞪口呆,一个劲儿用眼睛看徐雅娟,那目光里分明在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徐雅娟不好表态,把眼神挪到了别的地方。
冯秋云见徐雅娟不发表意见,她低下头想了想,很快便平静下来,看一眼司马文,笑着说:这些钱我的确是第一次见到,可我只有一个想法,或者是条件,你要是答应,我就同意嫁给你。
你说吧,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只要你肯嫁给我。司马文说得信誓旦旦。
那好,我嫁给你,但珠宝店我不开,我也不会开,我还要干我这份列车员的工作,而且我永远也不会离开铁路,离开列车。
这……司马文就是想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想到她提出这样的条件。
如果你不能同意这个条件,那咱们只能做朋友了。冯秋云微笑着说。
铁路有什么好,你这样一天辛辛苦苦,一个月才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有钱人的一顿饭钱,你怎么就那么傻? 我给你钱,你当老板,那不同样可以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说不定往后你还会把事业发展到海外,去挣美元,何必要抱着这么一棵小树受穷? 司马文十分不理解地说。
我的想法你不懂,我相信你永远也不会懂,我看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
他们就此分手。
徐雅娟说什么也没料到冯秋云把这事处理成这样,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会想起这件事,也不止一次扪心自问:这事要是放在自己身上,自己能处理得这么果断吗? 从那时起,她对冯秋云另眼看待了。
她曾问起冯秋云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冯秋云忽闪着眼睛笑着说:这很简单呀,我有我的工作,我喜欢,可你看他那个神情,好像觉得有钱什么都能买到似的,我就不信这些,我就是要告诉他,那不是真理。
怎么样,最近跟周俊的事有进展吗? 徐雅娟边走边问。
没有,反正这事儿就得看他的,他那边的事儿处理不好,我也只能这么等着。
唉,也是。
一阵微风吹过,将冯秋云额前的头发吹起一绺,她将头发拢到耳后,笑笑说: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跟姐夫……
小孩家家懂什么? 净胡说! 徐雅娟打断了冯秋云的话。
谁小孩家家了,你以为我不懂? 我什么不懂? 就你这一走好几天,昨晚上还不得好好犒劳人家一下子? 你……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根本就没那事儿。
什么? 没那事儿……冯秋云还要说什么,徐雅娟伸手捂住她的嘴说:好了好了,你哪儿懂那些? 不跟你说这些了,咱说点正经的,跑这趟车跟以前可不一榉,回来咱们就能一块儿去北戴河了,这一路上你多经点心,千万别出什么差错。万一有点闪失,咱可不好交代。再说暑运也快到了,全车的人都盼着这趟北戴河,说什么咱也得来他个万无一失才对。
放心吧,咱又不是头一次跑,我保证这趟车一切顺利,再说,大伙儿都知道这趟车回来就能去北戴河,谁不得经心? 可我这心里怎么老也不踏实呢? 那是你想得太多了,放心吧,保证什么事儿也不会有。
两个人边走边聊,徐雅娟看看时间不早,说:快点走吧,今天咱得早点到才行。冯秋云点点头,两个人加快脚步,朝车站旁边的客运段走去……
三
徐雅娟和每天一样,一丝不苟地站在队列前面,从头到尾将自己的队伍看了一遍。列车员一个不缺,看上去还个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顿时,残存在心底的那点儿不愉快便在瞬间消失了。
列车员出乘前都要在客运段这个院子里集合点名。其实,点名倒没什么必要,只要列车长看看人员是不是到齐就行了。但集合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大家要在院子里整队,然后由段里负责安全的或是其他方面的领导给大家讲讲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通报线路上发生的一些安全问题什么的,好让出乘人员做到心中有数。
一般没什么大事的时候话都由车长代讲,所以就要求车长要比一般同志早到段上一会儿,然后到安全室或是车队上问问情况,把需要通报列车员知道的事简单记一下,然后再传达给班组其他人。
过去客运段的院子挺宽敞,除去两座办公楼外,楼前面是一大块空地,有四五个篮球场那么大。可后来不知什么人看上了这块地方,说是要盖饭店,段上的人都说这不可能,这块宝地怎么能卖呢? 车站前边的地方可是寸土寸金呀! 可你说不可能,天下的事就是这样,越是觉得不可能的事越是有人干,没过多久,果然上边就有人说了话,还振振有词:一个客运段要这么大的地方有什么用? 现在是经济社会,要让每块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上边有人答应要卖,段上领导谁也不敢说不卖,再说段里也的确缺钱,职工们的想法很简单:真要卖出个好价钱,多发点奖金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地是国家的。后来这地就真的卖了,至于奖金却谁也没见着涨。
地占了没多久,施工队伍就开了进来,再没过多少日子,办公楼前就盖起了一栋楼。那楼比办公楼高出好几层,最下边是个饭店,上边是写字楼,从外面看确实挺豪华的,饭店门楣上还挂起一块匾:“聚仙楼”,黑底白字,左下角还刻着一方红色的大印。匾上的字是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写的,看上去挺豪放,再加上从上到下的落地大玻璃明晃晃能照见人影,更显得气派非凡。这“聚仙楼”虽然与客运段一墙之隔,可徐雅娟他们谁也没进去过,一来看那气派不像是为老百姓准备的,进去有点心里没底,再说平时跑车,在家待着的时间比北京春天的雨水还少,一回到段上,退了勤赶紧往家跑,谁还有心思去欣赏什么“聚仙楼”? 这些年北京的大饭店就像雨后春笋,转眼间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名字连记都记不住,中国的,外国的,汉字的,英文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般情况下根本引不起人们什么兴趣。
饭店起来了,看门前那车水马龙的红火劲儿和停在那儿的名牌车就知道生意肯定不错。可客运段里边就惨了,办公楼里四层以下长年见不着阳光不说,外面连个集合点名的地方也给挤没了。每个车班点名就只好凑合着挤在办公楼门口儿那一小块儿地方上,连个队列也没法站直。
好在各班组点名的时间都不长,有事多说,没事少说,越快越好,赶紧上车干活儿完事。
可今天徐雅娟这个车班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这趟车跑完就要集体去北戴河休养,又是全段第一个获得这个机会的车班,段里领导不出面讲讲明显不合适,再说这样的好事多少年来在客运段也是头一回,不在这时好好做做职工的思想工作,鼓动鼓动大家的情绪和积极性更待何时? 就因为这,段长李治国早就定好要亲自出马为大家送行。
徐雅娟知道段长要亲自讲话,把队伍集合起来还没来得及张嘴,段长已经快步从办公楼里来到了楼门口。
段长李治国是个大高个儿,四十几岁年纪,和他那张脸多少显得不太协调的就是他的那双眼睛,挺长,也挺细,因为他的上眼皮特别长,眼球是深深包在里边的,不使劲睁,谁也看不见他的眼球,再一笑就只剩下两条缝儿了。李段长说话声音不大,而且发闷,跟他的个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李治国其貌不扬,可段上人都知道他心眼儿挺多,在管理上也挺有招儿,就连段上那几个谁都觉得不好剃的刺儿头都惧他几分。其实李治国在管理上挺简单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人说话算数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肯帮助人,不像有些领导,表面说得挺热乎,其实就是不办事,总是拿嘴糊弄人。李段长在段上有威信,敢抗上,口碑不错,遇事从来也不怕事。据说有一年全局进行列车工作大检查,检查组查出了几处不合格的地方,铁路局要扣全段的奖金,李治国一听就急了,冲着来人喊:什么? 扣奖金? 工作组在哪儿?带我去! 他跟着来人风风火火赶到会议室,可人家铁路局检查组的人早就走了,他二话没说,叫了车就往铁路局跑。他先是找到局里有关部门,见说不通,便又找到主管客运的副局长,死说活说,软磨硬泡硬是撤销了扣奖金的决定。回到段上他把那几个检查不合格的部门负责人叫到办公室,一通狠赳,骂得那几个头头儿无言以对。
最后他说:就这几个钱儿,本来就不多,你们再不好好控制住,还拿得回来吗?职工们拿的钱本来就少,再一扣,谁还有心思干活儿?你们就不会用点脑子? 一个个像猪似的,就知道吃,心里一点事儿不想? 要你们干吗用? 就这些话一经职工们传就变得神乎其神,把李治国说得像个青天大老爷似的。说他亲自找了铁路局局长为民请命,还跟局长拍了桌子。其实他跟那个副局长是在运输学校上学时的同班,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有了这层关系,副局长总不能一点面子不给,一点旧情不念,但老同学还是丑话说在了前面:如果工作不上一个新台阶,再查出毛病,就要加倍惩罚。
尽管原来是同窗好友,可现在人家是副局长,自己只是个处级的段长,虽说行政级别只差一级,可差一点儿就是一点儿,他不得不在那位老同学的面前好好检讨一番,又说了若干感谢的话才得以过关,免了扣奖金的决定。当然,这些他对谁也没有提过半个字。
李治国对徐雅娟平时是有几分偏爱的。他觉得徐雅娟这个人不仅工作能力强,管理上办法也挺多,工作做得头头是道。自从提拔她当了车长以后,她负责的列车基本上就没有让他操过心。
这还不说,这个徐雅娟还能在年年的检查评比中拿个好分,当车长头一年就夺了个全路红旗列车的奖牌,这就让他对徐雅娟更是刮目相看了。本来段务会议上研究决定,凡是红旗列车班组都要轮流去北戴河休整,可哪一批先去却一直定不下来,最后还是他亲自拍板:就让徐雅娟他们这个车班头一拨儿去,这既是个荣誉,也是对徐雅娟工作的一种支持和肯定,更是对徐雅娟车班全体人员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