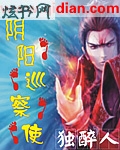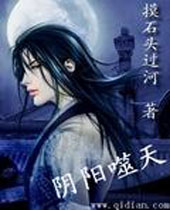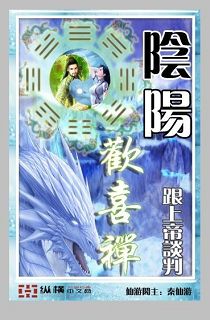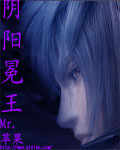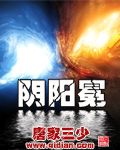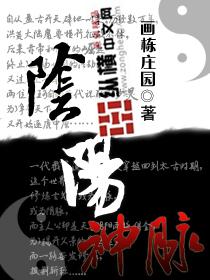阴阳脸-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详尽探讨专制政体下艺术家的人生角色定位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反而被一笔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政治明星,这样的离经叛道与本末倒置确实令人吃惊。任何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轻易发现其时正方兴未艾的佛学精义的影响——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长年斗争,并最终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3)
五
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在并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袁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辞官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应该并无任何夸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劝阻,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亲无人奉养什么的,紧接着又声称自己身患重症,并且已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说情,乞求吏部恩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惜以身试法,租用车辆将妻儿奴仆提前载走,向上司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再不批复,就将弃官出走。从他先后摆出的这些破釜沉舟、形同拼命的架式来看,可以想象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已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可怜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的叫苦连天的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驱,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 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龙司理
“作令若啖瓜,渐人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致湘谭知县何起升
“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已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多少光景,一朝到手,滋味反俭于书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亦若此耳。”
——致李维标典簿
“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
——致安福知县杨适筠
“谁不乐作官?弟有至情万不得已者,虽为亦无味耳。食无味,儿女子皆知吐之,官无味而不知吐,必且呕哕随之,至今身命俱丧无后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箭既离弦,无返回势,幸时察”。
——致吴县徐琴函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夺哉!”
——致丘长孺
六
有些时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里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在文字背后侥幸找到更多的发现。任何或多或少影响后来文学进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显得不同凡响。我们此刻面前的这些书信是明代散文的杰出部分,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怀疑。尽管如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可怜巴巴的陈述,将他所谓的看破红尘与公元二世纪的贤者陶渊明等同起来,仍将被证明不免过于天真与轻率。从表面看,性情萧散不耐政事繁杂似乎是袁下决心挂冠归隐的惟一理由,但通过对他个人全集的详尽阅读,我发现私底下却仍然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比如当时县城里有关他艳事的谣诼,其时发生的“花山讼案”中与上司、同事因处理意见相左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向维护他的苏州知府孙成泰的突然去职,其中尤以平日夸夸其谈无意中得罪当地名闻天下的文学泰斗王百谷张幼于一事最为势恶境迫。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一封致从前的受业恩师王以明的信中,袁扬言“吴中人无语我性命(佛学)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 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 油人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学生给老师戴戴高帽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坏就坏在不该拿自己治下的文艺界的同志来垫背。此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以后,在当地士林立刻激发了普遍的愤怒。而王张二人作为苏州士林的领袖人物,自然很难让他们在这样的轻慢与羞辱面前保持沉默。除先后来信严词相责以外,暗地里很有可能还动用了各自的政治关系进行回击和发难。可以想象如此险恶情势下袁的尴尬与窘迫。其间答友朋书中自然牢骚满腹,一会儿称:“楚人仕吴者若云,独弟以不才,为鬼神所罚。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过丘积,眈眈虎视,谁能厚我者”“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一切文字,皆戏笔耳,岂真与文士角雌较雄邪? 至于性命之学,则真觉此念真切,毋论吴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无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复从而拨之,可笑哉”等等,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但从他后来及时给张幼于(献翼)写了封一千字的长信辨白解释,同时主动与王百谷(樨登)修好,继续保持往来这些事实来看,采取的应该还是相当理智、低调、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不管怎么样,在原本已经为政务忙得晕头转向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倒霉事儿,犹如勉强维持住平衡的生活的天平,突然又一下子失重,并最终向背离现实的一端加速倾斜过去。在吴县的知县生涯看来已使袁彻底心灰意冷,为此他在连写七封辞呈不见批复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落水者或遇难船只的姿态、向自己的朋友兼上司苏州推官朱一理发出最后的紧急呼救信号:“走病实不堪劳,劳则发动,性命敢作儿戏乎?数日内闻赴阎王之招者数人,王子声死,李丹阳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万惟从臾令得早离任为幸。与明公交沥肝胆,若重官而轻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恳切!恳切!”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4)
七
假如能够借用电影手法,将眼前这一连串令人不堪的镜头倒回两年以前,当袁风风光光出京,躇踌满志地坐上背后壁上挂有“明镜高悬”巨匾的吴县正堂那把交椅时,尽管意识到未来繁杂的政事有可能影响自己素常的散漫生活,因此难免怀有担忧与畏惧,但总的来说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何况他对自己的才具与能力又是那么一向充满信心,以至上任不久后他就不无炫夸地告诉自己的朋友汤显祖:“作令无甚难事,但损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吴地宿称难事,弟以一简持之,颇觉就绪”。同时,在向精神老师李卓吾报告行踪的信中,同样也是一派怡然自乐之态,称“作吴令亦颇简易”“令吴无甚难事,无奈近日归兴浓何”?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当然要数与三舅父龚伯敏讨论官场感受的那封长札了,信中他先是毫不客气地吹自己“令吴只得个不忙,无他受用”,然后又以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推出他所谓的持中之论:“今之称吴令者,见乐而不见苦,故每誉过其实。而昔任吴令者,见苦而不见乐,又不免畏过其实。甥意独谬谓不然,故虽苦其苦,而亦乐其乐。想尊者闻之,必大有当于心矣”。然而,当这些得意洋洋的标榜的余音尚在县署的雕案画栋间回旋,另一个更大也更响亮的声音…我前述的那种抢天呼地,叫苦不迭的声音…已经迅速赶上并重重盖住了它们。就这样,在相距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内,这些书信的作者带给我们一连串不同姿势、音容和风采精神的袁中郎,而其中最真实,最可靠的那个,反倒一直在其中隐匿。直到晚年,袁对自己在吴县的人生经历尚始终深怀怨恨,在写给他的继任者,后来担任山东曹县知县的朋友孟习孔的信中,他除了再次使用自己发明的那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吴中犹阱也”(陷井,阱同井)外,还再三宽慰对方,自己与他能从这样可怖的政治深渊里全身而退,已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了,因为“聂令(昆山知县聂云翰)之去任也,疽发于背。江令(长洲知县江进之)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与门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余?”
八.
浙中山水的清幽与天然明丽一向是古代诗文里的不倦话题。从杭州到绍兴、五泄,再到曹娥、剡溪两岸的水色岚光,造物的毓秀与神奇以原始的,令人赞赏不迭的方式表现出来。何况时间上又适逢莺飞草长,烟雨蒙蒙的江南早春。显然,这是一幅与在苏州时险诈庸碌的官场生活所截然不同的风情长卷。对于其时“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致朱一龙司理》)、把妻儿奴婢寄居无锡朋友家中,俨然李白第二,怡然出游的袁某人来说,将其间的变化譬之“割尘网,升俗毂,出官牢,生佛家”(《致冯秀才其盛》)倒也算不上有什么夸张。当时他的行踪大致是这样的:万历二十五年初春辞呈获准后即速抵杭州,与相互慕名已久的陶周望、陶周臣、汪仲嘉、方子公、虞长孺、虞僧孺等浙江文坛的衮衮诸公惺惺相惜,诗酒言欢,并由陶氏兄弟相伴游越,盘桓天目、会稽二月有余。其次溯新安江至徽州,饱览黄山,齐云秀色。返途中又在杭州居停,闲游。然后回到无锡探视家眷。又先后去南京与扬州两地寻访朋友,行吟啸傲,总共花费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将自己纪录此次行程的作品定名《解脱集》,显然蕴有对过去生活的厌恶与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当年秋天当昆山知县聂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见他的旧日同僚在信中简直就像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