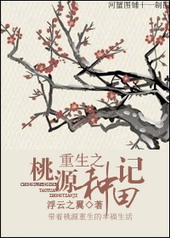破壁记 陈登科-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秦斐的眼泪象决了堤的江水,淹没了她的蜡黄的面容。
五O年的元旦。昔憬特地来看望安东。
安东请昔憬参加了新年联欢晚会。看到秦斐演出的《夫妻识字》,昔憬惊呆了。他拍拍安东的肩:
“这个演员太了不起了,节骨眼里都是戏!”
安东笑道:“你倒是行家!”
昔憬道:“行家说不上,不过,看得出她对新生活的感情。一举一动都有内心活动,一点也不做作……演员嘛,我见过的也不算少,可象她这样唱得好,做得好,而且有独创精神的,实在不多……”
安东:“你讲在点子上了。现在,她对解放后的新生活,真是没法形容地热爱……”
昔憬看看节目单:“她叫秦斐?”
安东点点头。
昔憬道:“可以看得出,这个人在旧社会一定有过极其痛苦的经历。”
安东道:“你这副判断人的眼力还没有衰退呀!怎么样,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好么……”
昔憬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很快,昔憬和秦斐交上了朋友。一有空,昔憬就会从相隔二百多里的另一个城市赶来看望秦斐。每次来,安东都眯着眼笑道:“嗬!跑得真勤快呀……”
昔憬红了脸:“看看你呀!”
安东捶了他一拳:“你呀!能瞒得过蒋介石和戴笠,却瞒不过我……呔!和秦斐闹上恋爱了吧!?”
昔憬搔搔头:“……嗨!几次都没有说出口。”
安东笑道:“那我有什么办法?”
昔憬道:“你和夏雯是哪个先开口的,…”
安东道:“这种事,当然应该咱们主动进攻!别废话了,今天天气多好!你就进攻吧。”
昔憬笑着,鼓足勇气,一口气跑到秦斐的宿舍,也投有敲门就闯了进去。秦斐正趴在桌子上看书,转过脸嗔道:“看你里连门也不敲就闯到人家女宿舍里来了……”
昔憬红了脸,憋着的一肚子话都丢到爪哇国里了。秦斐端了把椅子给昔憬,又泡了一杯茶,转了笑脸:“怎么又来了?……”
昔憬打着掩护:“有事,顺便来看看你……”
秦斐:“每次你都说有事……”
昔憬顺着这话便道:“这桩事,是大事,每次来都没有办成……”
昔憬觉得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了,便说道:“今天非办成不可……”
秦斐:“那到我这儿来干吗?”
昔憬:“因为……我……我喜欢你!”
秦斐脸飞红了,眼里浮起一丝痛苦的阴云。
昔憬结结巴巴地说:“原谅我!我真的喜欢你……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还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人。不过,你不要痛苦……看你……怎么皱起了眉头……唉……我不说就好了。我看出来了,你……你并不喜欢我……。不要紧,我这就……就走,你只当我没有说过这话。……该死!都怪安东!……唉,不进攻倒好,我还能象朋友一样来看看你,现在可难为情了……”
最后,他的话已经变成自言自语。他生怕秦斐回答个不字,掉过头就走。就在拉开门的一瞬,一只温柔的手拉住了他。秦斐正用一种异样的神采打量着他,而且轻声地说:“你别走……”
昔憬站住了。两个人的目光对峙了半晌半晌。昔憬第一次看到秦斐乌亮亮的大眼珠里变幻着这么复杂的色彩。他冷静了,又冷静到做情报工作时那样,观察站在他对面的女人从眼睛的窗户里透出来的内心的酸甜苦辣。
秦斐叹了口气:“你喜欢我什么呀?”
昔憬呐呐地:“喜欢就是喜欢……”
秦斐:“是不是我长得还算漂亮……”
昔憬谕纳地辩解:“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秦斐:“是不是可怜我,同情我……”
昔憬不知如何回答,抓住了她的手。
秦斐挣开了:“我不需要别人恩赐的同情。”
昔憬实在无法解释,不顾一切地拥抱了她:“秦斐!你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精神负担……”
秦斐:“共产党是大救星,我比哪个都体会得深。不过,假使你作为一个救星那样可怜我……这不是喜欢,不是爱……”她没有挣脱昔憬的搂抱,“我也喜欢你,但是我怕象我这样的女人没有权利喜欢别人……我怕你对我讲爱我,喜欢我;可是又等着你讲爱我,喜欢我……”
昔憬只觉得发烫的面颊上,沾着两颗冰凉的泪珠,不由得感到一种沉重:“她……心上的皱褶是多么深啊……”
秦斐也感到了他的心声,抽泣起来:“我的心已经在苦水里泡得麻木了,原谅我吧!”她突然热烈地吻了他的脸,又突然推开了他,扑到床上,痛苦地呜咽起来,“我不能……不能!我……不是清白身子……”
昔憬慌了,坐在她身边:“安东把你的身世都对我讲了!我……我们结婚!结婚吧!”
房里,一架老式的台钟,敲了十下。一声声清脆的钟声把沉重的空气敲开了。
秦斐转过脸,望着钟,心里在叨念:“这也许是我真正幸福的时刻。”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站在烟囱顶上的秦斐望着海关的大钟。大钟发亮的钟面,时针指着八点,一声声沉沉的钟声敲着她的心房……
“还有两个钟头……”秦斐的手又情不自禁地交叉成一个十字。
烟囱下,无尽的人潮在汹涌澎湃。
两只探照灯雪亮的光柱,也交叉成一个十字,在烟囱顶上扫瞄,终于变成一个焦点,投在秦斐身上。她一动不动,就象是塑在烟囱顶上的一尊雕像。
嗡嗡的议论,从这一堆或那一堆人群中响着:
“唉!这个女人真想寻死!”
“死了也是白死,人家照样刷她一条大标语:‘死有余辜’”……造孽!”
“她也够可怜的了……”
“可怜个屁!”
“简直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示威!”
“喂!话也不要说得太绝,我看秦斐是有委屈……”
“本来嘛!哪个人不想活呀……”
是的!好心的人都在希望她活。
人们把体育馆里的软垫子抬来了,密密麻麻地叠在烟囱周围。
有人还张开了建筑工地上用的安全网……
好儿辆救护车都开来了……
四、五部广播车朝着烟囱顶上狂喊乱叫:
“下来!下来!”
“秦斐!要想开些!”
“秦斐!秦斐!我们在救你……”
但其中最响的声音把其他的广播声压倒了:
“秦斐!你不要执迷不悟,不要死得轻于鸿毛……”
人群里发出“嗤!嗤!”的轻声咒骂和嘲笑……
秦斐还是象塑像似的一动不动。
她呆滞的目光注视着海关大楼的时针,指针在缓慢地移动,她的思潮在急速地翻滚……
如果能走近看看她此时此刻的脸,谁也不会想到,秦斐的嘴角竟会挂着一丝笑容。下面的一切声音都象风一样,从她耳边吹走了。在秦斐的耳膜里,依旧响着一生中最悦耳的钟声。
秦斐的双手,两枚食指就象粘上似的,一直是那个十字。
秦斐和昔憬,就是选择在晚上十点钟结婚的,那是一九五O年十月一日。
结婚的当夜,宾客散尽了。只剩下他们俩人时,昔憬问她:“为什么你这么怪,偏要挑晚上十点钟?”
秦斐笑道,“你不记得么?那次,我们表示爱情的时候……”
昔憬摇摇头:“从我这个侦察员的眼光来看,这意思似乎还要深些……,
秦斐点点头:“旧社会在我的心上划了两刀,留下了好深的伤痕,新社会把我心上的创伤填平了。……有一天,我如果死了,你打开我的心来看看,一定有一个十字形的伤疤。”
昔憬把她的嘴捂住了:“不许你这样说!”
秦斐生活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她文化程度并不高,几乎是从头学文化。更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但却从自己的经历中准确判断出旧社会与新社会,国民党与共产党,恶与善,丑与美的区别……她的艺术青春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发出光彩。
秦斐成了名演员,当上了省的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从性格上讲,她和昔憬并不完全相似。她热情,而且因为是被旧社会的烂泥封闭起来的热情,所以一旦冲出地面,就象滔滔不绝的温泉,恨不能把所有温暖都给别人。而他比较冷静,就象在惊涛险浪中冲洗过的岩石,并不认为生活的大海永远是平静的。
于是秦斐和昔憬,也常常闹点矛盾。矛盾,常常是从对人的看法上引起的。
秦斐剧团里有一个老和她配戏的小生,叫何亮,是他们家常客。
但几次来过,昔憬就不大理睬他了。
秦斐生气了:“看你,大咧咧的,连客人走都不站起来送送……”
昔憬哼了一声:“他每次来不是说刚从李部长家吃了饭来,便是说马上要到王书记家去吃饭……我这里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秦斐道:“不管怎么说总是我的朋友,也要照顾影响嘛……,再说,人家倒总说你了不起,佩服你……”
昔憬说:“我有什么好佩服的……”
秦斐道:“他知道你过去在蒋介石鼻子底下干过的惊险的事呀!”
昔憬皱皱眉头:“你告诉他的?”
秦斐道:“他说要把你的斗争生活编一个戏呢!”
昔憬火了:“是不是还有点票房价值?”
秦斐看见自己心爱的丈夫竟会发这么大脾气,惊呆了:“你……你怎么啦!”
昔憬也觉得对她不应该这样,便抚摸秦斐的头:“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不过,我总隐隐约约感到,在生活里把你捧上天的人,也可能是把你摔得最重的人。”
秦斐想了想,不大理解地说:“现在是在新社会,而且是革命队伍里……,
昔憬忍不住地笑了:“你呀!过去么躲开所有的人,认为都是坏的;现在嘛,又认为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都是好的……”
秦斐撅着嘴,不咬声了。
矛盾归矛盾,也始终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这个家庭还是美满的。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学绘画,大女儿学音乐,十来岁,便都分别考取了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的附中。
昔憬笑着对秦斐说:“好罗!两个大的都跟你学搞文艺了,小的两个得归我了……”
秦斐也笑了起来:“看来也差不离。你看老三,成天板着脸,准是跟你一样,当判官的料……”
昔憬:“判官也不见得都板着脸,这都是你们戏文里公式化的表演。党的监察工作,应该最通情达理,通人民之情,达人民之理……”
秦斐:“你还通情达理呢?!何亮几次想来采访你的经历,你都拒绝了!”
昔憬哈哈大笑起来:“好!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谈一次。不过,不要写我的真人真事。文艺么,要讲个典型概括,对么?”
秦斐高兴得抱住了昔憬:“你真好!”接着,连连在他的腮帮子上吻了又吻。
昔憬更乐了:“咦!老夫老妻了,给孩子看见了不贱味……”
秦斐挽住他的膀子:“明天我就把何亮找来,好不好……”
昔憬指指她的鼻子:“看来,我上次拒绝了他之后,你心里存着个大疙瘩……”
秦斐嗯了一声:“本来嘛!我看见别人扫兴,心里就不好受。”
第二天,秦斐买了一条大鲫鱼,亲自做了几样好菜,还打开了一瓶昔憬最爱喝的香雪酒。
何亮老早就来了,硬要帮着秦斐杀鱼剁肉,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曲子,高兴得不得了。秦斐说:“你是客人,哪能让你来干活?”
何亮系了条围裙,笑道:“我何亮能做你秦斐的下手,还不光荣?在台上,我也是你的配角么!嘻嘻……,秦斐,咱俩是老朋友了,讲句不见外的话,你这副嗓子,如果在外国,甭说活着的时候能轰动世界;死了,人家也会争着出百十万美金的大价钱买了去解剖……”
秦斐笑骂道:“你这人呀,就是这点不好,讲啥都要用钱来称一称。等一会见了老昔可不准讲这样的话。”
“那当然罗!象老昔这样的老干部,真是难得,又有文化又有风度。……秦斐,你这辈子找到这么个丈夫,真是够本了……”发觉说漏了嘴,他连忙转了口,“看你,眉头又皱起来了。我这人身上旧习气太重,又是本呀,利呀,说得太俗气了……今天哪,你得多鼓动鼓动,我就只管记。”
秦斐洗洗手,领着何亮到昔憬的书房里,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照片。何亮一看,是昔憬作为地下工作者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的时候照的。昔憬穿着国民党少校军装,站在蒋介石的左侧,边上还有白崇禧、陈诚等一帮人。照片是在解放南京后,从总统府里找出来的。
秦斐:“你看老昔,还保存了这个作纪念!”
何亮:“这简直是历史文献,了不起……”
秦斐:“要不是他那段出生入死的经历,我都恨不得把它撕了……看看他当年的样子,在鬼门关里跨进跨出,到现在我还替他捏一把汗……也真亏他……”
“把这段编个戏,嗨,准能轰动!”他仔仔细细地盯着照片,笑得合不拢嘴,“戏名字我都想好了,叫《魔窟历险记》或者叫《最高统帅部的秘密》。”他乐得手舞足蹈,“保险打响!不是吹牛,什么《虎穴追踪》、《英雄虎胆》都不在话下!秦斐,你今天一定要让老昔讲得仔仔细细……”
秦斐:“你看,我不是准备了酒了么,他呀,喝几盅酒,劲头就来了……,
何亮乐得抖开围裙,转了一圈,跑了个龙套,嘴里还打着锣鼓点子:“哐哐哐……啼啼,哐哐……”
昔憬正好回来,何亮也正好站住,一个亮相:“来将通姓报名……”一看昔憬站在门口,顿时涨红了脸,尴尬地笑着。
昔憬一看这模样,也不由得笑了,握了握何亮的手:“你好!戏台上的规矩,你这么一转,就是十万大兵,我可受不了啦……”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
秦斐悄悄地拉拉何亮的袖子:“哼!猴年马月都听不见他开一句玩笑,今天情绪可不错!”
这一顿饭吃了足足三个小时。昔憬也果然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