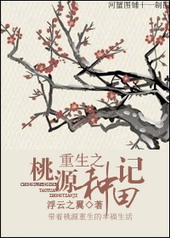破壁记 陈登科-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秦斐是黑帮。”
“胡扯!我们不是阿斗……”
“她有问题。……”
“有问题?什么问题,摆事实讲道理……”
“你们看大字报……”
“呔!这种大字报,除了血口喷人还是血口喷人!还亏是你们有文化的人写的呢……”
“不行!退票!退票!”
“不退票,把剧团给砸了……”
秦斐蜷缩在天幕的后面,吓昏了……
后台有些人在讲:“这帮流氓肯定是秦斐邀来保她自己的,不要脸!”
一听这话,秦斐揭开天幕冲到台上,用几乎哭的声音,朝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喊道:
“同志们……我求求你们!……我……不能演出!我在接受群众的批判……”她慌乱地朝下面摆着手,“我求求你们……也谢谢你们……”
雪亮的灯光照着她晶莹的含着眼泪的大眼睛。
台下的一群观众看见秦斐出来了,顿时欢呼起来:“秦斐!你唱一段,我们便算数!”
“秦斐!唱呀!唱呀!”
“怕什么!大胆地唱……”
又有一部分人吹着惚哨,朝秦斐吐着唾沫。
“快滚下去!”
“谁要你这骚娘儿上来……”
“嘘……”
秦斐站在台上,脑子里嗡嗡响。她的所有的神经都麻木了,象白痴一样站着,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她听见两种不同的喊声愈来愈大,后来发展成为互相的咒骂,再后来是椅子劈劈啪啪折断的声音,双方竟打起架来。天幕和大幕都撕毁了,台上台下,一片惊恐的叫喊……
从这件事以后,对秦斐的革命行动逐步升级了,她甚至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批斗、游街、抄家……,秦斐都经历过了,每一种革命行动的第一次,都是使她胆战心惊的,但以后也处之坦然了。她每天都挂着一块五、六斤重的木牌,低着头站在刺骨的寒风里。第一次,她感到羞耻,甚至想一头撞在墙上死了拉倒,但后来竟会主动地把牌子套在颈子上。……有时,她突然产生了一瞬间的想法:我秦斐在旧社会还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呢!但一转眼,就会痛苦地谴责自己思想的犯罪,连忙嘴里叨念着毛主席的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于是,感到了一种安慰。宿舍里的箱箱柜柜,已经被戴着红袖章的什么造反派搜罗得干干净净,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留下。……她反而舒了口气:“这下好了,总能证明我秦斐是好同志了。”所以,头几天,每到晚上回来一看这空落落的屋子,秦斐就感到难言的苦恼;每夜枕头都是湿的,而后来反而宽慰了,让他们检查吧!我的日记,昔憬和孩子们朋友们的信,哪一页不都流露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
这毕竟是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政治概念,秦斐背得烂熟。她以一种宗教徒似的虔诚,拚命在自己灵魂深处挖“污泥蚀水”,一点一滴都写在思想汇报上。她拚命地劳动,打扫剧场,打扫厕所,最脏最累的活都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倒在床上。她合起眼皮时,还留着一丝笑容:“明天,总能对我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然而,明天还象昨天一样,她一早起来依旧挂起牌子,站在寒风里请过罪,又重复着和头一天一样的笨重的劳动,重复着和头一天一样的思想活动及企望。
有一天,她正爬在剧场的十来米的灯光架上,擦着聚光灯的玻璃,一截高压线的胶皮脱落了,一个念头闪电一样在她的脑际掠过,只要一只手这么一抓,另一只手拉住钢梁半秒钟,就什么都完了。……但她马上又为自己这个死有余辜的念头感到犯了罪似的沉重,禁不住惊叫了一声。
何亮正好从下面走过,看见秦斐爬得那么高,便把她喊了下来。秦斐最近已不大愿意看见何亮,但何亮每次看见她总很客气,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不一样。
“哪个把你支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工作的?岂有此理!”何亮掸掸秦斐身上的灰生,“唉!秦斐,看见你这样,我很难受……”
秦斐以为何亮看穿了她的心思,脸色苍白,呐纳地说:“你现在代表组织了。我……我不能隐瞒你,刚才……我有一个危险的念头,唉……这简直是错上加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何亮十分同情地:“……那就把你的这个思想写在思想汇报里。我……想帮帮你忙,可是,你知道,我们是老朋友……”
秦斐:“我也不愿意连累你……”
何亮:“我对你是了解的,可别人不了解呀。你详细写个自传,好么?!”
秦斐点点头,眼睛里又浮起了希望。她壮了胆子:“老何,难道我真有那么大的罪?……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呀?”
何亮:“我也常常在文革会上这样问。可是……群众运动嘛……再说,昔憬已经关起来了,你知道吗?”
秦斐惊呆了。
何亮低声说:“文革首长已正式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
秦斐为自己的事,从来没有申辩,可为了昔憬,她是决不允许别人损伤他一根汗毛的。她又气又急地嚷道:“这不可能。是造谣,是污蔑!”她哭起来,哭得比任何时候都伤心。因为在自己丈夫被关起来之前,他们连晤一次面的机会都没有。而且,责任全在于自己。因为十月一日,他们结婚第十六周年的时候,秦斐还是自由的……
何亮叹了口气:“我也不大相信老昔有问题!”
秦斐呜咽着:“你采访过他的经历,……当然了解他了。现在,只有你,是我唯一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老何,看在朋友面上,你照顾照顾我的四个孩子。……你要对他们讲爸爸妈妈的历史,他们都是好人。……老何,老昔过去对你有时不礼貌,你原谅他一点。……”
何亮看看周围没有人,大胆地握了握秦斐的手。从汗津津的手心里,秦斐感到这个朋友的激动心情,也感到许久未有的同志的温暖。
何亮走了。秦斐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叨咕:以前觉得他有点俗气,有点圆滑,现在还真是亏了他。
白天劳动,晚上写自传,秦斐很快被折磨得苍老憔悴了。尤其是自传,写旧社会的遭遇,秦斐简直是蘸着眼泪写的。那个宋委员,那个保安大队长,那个方绍武,那一个个流氓、地痞、恶棍,象恶狼一样,又浮现在她的面前,围着她狂吠,嚎叫,张开了吃人的血口。她一面写,一面哭;一面哭,一面写。这样的身世,哪个看了,会不给予同情?
一天演出,秦斐又被支派在灯光架子上。几千度的强光灯,烤得她心里直想呕吐。台上的喧闹的锣鼓点子,敲得她晕头转向,她累到了极点,拚命支撑着。但踩着的那块木板,却象浪里的舶板,愈来愈颠晃……
该转换红光的时候了,秦斐还紧闭着眼,竭力使自己保持平衡。只听得一声吆喝:“你这个黑帮分子,想捣乱么!换光,换……”
秦斐一惊,一撒手,从十来公尺的钢梁上栽了下来……
秦斐的腿跌断了,胸前的肋骨也断了三根。她被送到了医院,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全身打了石膏。
第四天,她微微睁开了眼,大概因为折磨久了,尽管这么重的伤,倒也清醒了过来。隔着屏风,她听见了何亮咳嗽的声音。看来这位朋友一直在关心着她,使她十分感激,不由得睫毛下渗出了一滴眼泪。她想喊他,可连轻轻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便又闭上了眼。
这时,又听到另一个人的说话声:
“你应该明白,你这个文革副主任是谁栽培你的……”
何亮还是咳嗽,这种咳嗽正是想讲什么又不大好开口的搪塞。
那人问道:“她能活么?”
何亮这才开口了:“你没有见我一直守在边上?!医生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那人有点生气了:“得!得!什么大概,大概……,你一定要保证救活她。这个女人,现在对我们来说,不是死活的问题,而是要她的口供,你知道么?!”
何亮又只有轻轻的咳嗽了……
那人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在斥责何亮:“你这个人哪!我早就知道你是油缸里的泥鳅,滑上加滑,是属锅贴的,哪个镬子热朝那个上面贴。说热么,现在谁还能热得过我这个一月革命风暴里冲杀出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当心!我会象捏死一只跳蚤那样,把你捏得扁扁的!你拍昔憬的马屁,抱安东的粗腿,谁不知道?!把你和秦斐一样抓起来,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爪牙,决不亏……哼!不过么……我……我还不会这样。老子抬举了你……可你这几个月还和秦斐勾勾搭搭……还想留条后路是不是……?告诉你!你一定得按照我的意思,让秦斐写一个口供,还要签字画押……”这个人发了一阵火又渐渐软了下来,“老何!人抬人,人帮人,现在咱哥儿们里,只有你干这件事最合适呀……”
何亮还是没有吱声,从不断的咳声里,表现得胸有成竹。……
后来,听得出两个人的脚步声远了……
秦斐不知道那个口气很大的人是谁。可是隐隐约约觉得声音和说话的腔调似乎有点熟悉,她也顾不得追究了。何亮已送客回来,走近她的床边,看见秦斐还闭着眼,眼角挂着泪水,便亲自检查了一下吊针和葡萄糖。他又咳嗽了一下,秦斐微睁了眼。此刻,朦胧的月光里,何亮竟如此高大,真象舞台上的郭建光了。
但何亮却微微一怔,他想的是刚才的讲话,她是不是听见了,便问道:“你……刚醒?”
秦斐点点头,又摇摇头,她从来不会说谎的。
何亮又一怔,这心思,秦斐是决不会知道的;他吁了口气,幸亏自己没有说什么。
秦斐用信任的目光望着他:“刚才那个人是谁?……”
何亮:“是省革委会的一个委员……”
秦斐说:“我怎么觉得他的声音有点耳熟?……”
何亮的眼睛闪了一下,暗暗思忖:“这位大委员为什么特地赶来找秦斐?而秦斐又感觉到声音很熟悉,这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他没有表露声色,笑眯眯地说:“秦斐,你好好的养伤。你的自传我看了,写得真不错。我是完全相信你的……”
秦斐急急地问道:“我不担心自己。昔憬他……他怎么啦!你没有把我受伤的情形告诉他么?我想见见他……不!不要他来……也不要告诉他。等我出院之后,无论如何准我几天假,去看看昔憬,看看孩子们……”
何亮很慷慨地点点头。
秦斐感激得想去拉何亮的手,甚至想挣扎着起床来送他,可是除脑袋和上肢能动弹之外,全身都埋在石膏的棺材里了。她苦笑了一下,喃喃自语:“我一定要好好的养伤,我可以看看昔憬了……看看孩子们了……”
果然,秦斐以惊人的毅力,配合着医生的治疗,好得很快。两个月以后,便撑着拐杖,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了。
这期间,何亮又来过儿次。每次来,都问起秦斐写的自传的细节,尤其问到三十年前,怎么认识方绍武,又怎么被方绍武骗了的时候,连方绍武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都问得仔仔细细。秦斐都一一回答。但回答之后,又感到象吃了一条蛆虫那样腻味和恶心。这个在她痛苦的记忆里已埋了三十年的魔鬼,还把它挖出来干吗呀!不过她相信,这正是组织上在详细调查她的历史,那么搞清自己的问题也就快了。
一天,她又在花园里撑着拐杖练习走路,看见一辆小汽车驰到病房大楼前停了下来。何亮陪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走出汽车。当然是找她来的。秦斐便一拐一拐地追了上去。可是这两个人没有到病房,却走进小会客室。接着,医生捧着病历表,也进去了。
秦斐退回到花园里,站在冬青树丛里,隔着玻璃窗,又听到了那个很熟悉的声音:“我不必见她,只是想了解一下她的伤情……”
医生的回答:“方组长,最多再隔两个礼拜,她便能出院了……”
一听这个人姓方,秦斐的头脑顿时象炸开似的轰轰乱响,眼前也金星乱飞,她浑身哆嗦,好不容易才遏止了自己的激动,悄悄凑到窗边。从窗帘的缝隙里望进去,那个坐在中间沙发上的人,正是三十年前的方绍武……
秦斐再也支撑不住,跌倒在地上,拐杖也丢了。这次,不是昏迷,也不是晕倒,她好象被银环蛇咬了一口,神经已经失去知觉,但头脑是清醒的……
小汽车又开走了。何亮走了过来,扶起了秦斐。只见她嘴唇发乌,牙齿打战,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何亮脸上,半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这……这魔鬼……骗子……!他……刚才那个人,就是方绍武……”
何亮的眼睛里陡然闪出一道闪光:“啊!果然是他!你没有看错么……?”
秦斐肯定地点点头。
何亮出乎意料地高兴起来:“好!你小子,靠着军代表的支持,爬上省革委会委员的宝座上倒阔气,我也不能让你这么舒服……”他转过身便跑。
秦斐又为何亮这种侠义行为感动了。她的一生的弱点就是只知道舞台小天地。以为戏文里的郭建光,此刻一定是带着十八位好汉去向方绍武讨逆去了。哪知道在天地这个大舞台,这位“郭建光”竟在生活中扮演着另一个角色。
方绍武在三十年前卷款潜逃之后,就改名方为,跑到了当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在顾祝同手下,混了个军需参谋。又因克扣军晌,被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几个团长打了一顿,连顾祝同本人都包庇不住了,只得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但没等开庭,审判官就悄悄地放了他。他就过江来投奔了新四军。而后,他拿着军事法庭的传票当作自己叛逆蒋介石的证据,混入了革命队伍,甚至混到了党内。新四军北撤,他又开了小差。在苏北、上海跑单帮。解放后,重新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因为一件政治诈骗案,落到了昔憬手里。昔憬向司法部门起诉,判了他七年劳改。刑满释放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的暴风雨把埋在社会底层的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