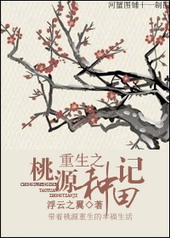破壁记 陈登科-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听着,心里乱糟糟的。正好又翻到《木木》这一篇,伤心、委屈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滚动。
晌午时分,男同学也陆续回来了,敲着洋磁碗,到我们宿舍里来咳喝着:“今天谁值班做饭……菜都没有洗……”
哎呀!坏了!该轮着我做饭!我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正要夺门而出,迎面撞着昔蕾。她手里拿着《红楼梦》,气呼呼地冲着我便嚷嚷:“好啊!这是我家的书,怎么到你手里去了?原来,抄‘四旧’都抄到你家腰包里去了……”
我一愣!昔蕾讲的不错,这是她家的书。不过,是霁霁叫我偷偷地保存着,准备将来还给他家的,可是现在怎么讲得清呢?
昔蕾一眼瞥见我没有关严的箱子里还有好多本小说,便干脆把箱子里的东西全抖了出来,气得脸煞白:“你们大家看看,书上都有我爸爸的图章,还有我哥哥的……”
我浑身发抖,我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贼。我哇地大哭起来:“蕾蕾!你,……你污蔑我!”
“什么!我污蔑你?不要脸!你们家把我们家都占了,什么都占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暴发户!政治上的扒手,经济上也是扒手!”
我能申辩什么呢?我几乎晕倒了。她的嘴里喷出来的全是火。我只有张着嘴,眼泪哗哗地淌,舌头象打了结。我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死了拉倒。我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个字:“……不——!”
这一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来了,他们把昔蕾拉出了门。
我听到昔蕾一声揪心的哭喊:“你们讲不讲理呀——!”我也听到一个干部的大声训斥:“胡闹!”底下什么话我听不清,反正是训蕾蕾的。
我真想冲出去,喊道:“不!蕾蕾骂得对!骂得好!我家是扒手……”
这时,石亦凤来了。她二话不说,双手捧着我的脸蛋,掏出手绢,擦干了我的眼泪。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不开口的女人,目光里含着严峻的温和。第一眼是严峻,第二眼是温和。我宁可严峻,也受不了这种温和。
眼泪又象断了的线,在我腮帮上徐徐淌着。
蕾蕾的哭声已远去,显然是被那个训斥他的于部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个下午,宿舍里面都是对我和蕾蕾的议论:
“太不公平!为什么要昔蕾写检讨?!”
“就因为她老子是‘特务’!”
“今天你们看到了吧:芸芸人家是有来头的,惹不得!”
“现在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一下午都呆呆地坐在我常来坐的溪边的石头上。这些都是李秀芹来对我讲的。我相信她没有坏心,因为她说:“怪我!都是我闯的祸!”她还告诉我,“同学们口气不是对你,而是……”她即便快嘴,也把这没有说出来的话咽了下去。我把她没有讲出口的话接了过来:“……而是这场文化大革命!”
她吓得连忙捂住我的嘴,说道:“你说不要紧,我们说,就要揭一层皮了……”
“为什么?”
“你是上头有人打过招呼的,要照顾你……”
晚上,我就领教了这种照顾了。
公社的武装部长把我请了去:
“小郑,你今天受委屈了……我们肚里有数的!今后,你要多注意你们知识青年里的活动。我们公社里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再加上这些被揪被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就更加复杂了。今天,昔蕾对你的态度,就是一种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姑念她还年纪轻。不过她一定要深刻检讨,还要向你赔礼道歉。现在,你要关心她的行动,她经常到石亦凤家去。石亦凤,知道么,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程磨子的老婆。我给你一个任务,你要想办法弄清他们之间的活动,……嗯……?”
我明白了:舅舅已把任务布置到公社里了……
那就将计就计吧!
我对那个武装部长说:“既然你要我这样,便不能让昔蕾检讨,更不能让她向我道歉。她一检讨就更恨我了,就不会搞好关系……”
那个武装部长咯咯地笑了起来:“看不出你年纪虽小,倒怪有心机哩!”
三月二十日
昔蕾看见我时还是以前那副态度,随她去吧。
其他同学看到我,好象比以前亲切了些,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心理的:“惹不得!”“有些地方还要小郑帮帮忙呢!”但大多数是因为看见我主动和昔蕾打招呼,大事小事都帮着她一点,尤其是我把那些书包好了,塞在昔蕾的床下面。
那个武装部长真以为我在照着他的心思办,也很满意。问我,我就回答道:“大家天天累得话都讲不出,倒在床上就睡了……”
因此,我倒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也慢慢知道了同学里和公社干部之间的一些“复杂”的关系。
这个公社,真正当家的是那个武装部长。他叫王德发,是程璞从小拉扯大的。五八年因为在山里红公社违法乱纪,程璞整了他。这件事情至今许多社员还暗暗叫好。后来王德发靠成跛儿翻了案,一下子变成了“英雄”,反过手来整他表叔,一直整到把程璞关进监牢。这是一条狼,连自己的亲属都要吃掉的狼。据说,他的母亲开始偏在儿子一边,后来看到自己的表弟被折磨得太狠了,也劝过儿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革命亲属,大家都要讲个阶级感情。”惹得他大发脾气,抽手打了她一拳。从此,她一病不起,最后吐血死了。王德发反过来却讲他娘是给程璞气死的。
王德发调到这个公社才两年,十个社员里就至少有六个社员挨过他的拳打脚踢。他动不动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许下大话,要把桃花潭打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他上面通着省革委会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两年就调换了三个领导班子。现在,他虽是公社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但其他的公社书记,主任,在他面前都得捏着鼻子过日子。
知识青年是他亲自管的。王德发一有空便朝我们女宿舍里钻,嬉皮笑脸地拉拉这个,捏捏那个。看到他来,女同学都连忙缩到被窝里,假装生病。晚上,早早把门门上了。在我记日记的时候,已经夜里九点半,又听见他的脚步声了,我连忙把灯熄了……
三月三十一日
秀芹悄悄告诉我:她姐姐和罗铭有点意思了。
我的脸忽然红了:“对我讲这个干吗?”
其实,我也看出点苗头了。
前天,我还是一打过晚饭,便端了饭盒子一个人坐到溪水边的石头上,慢慢地吃,这是我一天最安静的时候。
桃花开了,又快谢了,一片片花瓣飘落在溪水里。我望着这些花瓣,似乎是一张张风帆顺着激流穿过峡谷。这峡窄的溪水和一块块岩石,在我的想象中,忽然宏伟险峻。我脱口而出地念了一句李白的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哪知这一念,从桃花林里惊起几只斑鸡。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罗铭和秀萍,匆匆忙忙地穿过林子。他们跑得这么快,以至秀萍的手绢都掉在溪水里。手绢顺着水流,淌到我跟前。我把手绢拾了起来,把它洗干净了。
昨天,我把手绢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秀萍的枕头下。她看见我,脸唰地红了,眼皮垂了下来,轻轻地说了声:“谢谢!”秀芹对我讲时,担心地说:“唉!真要命,才来一个月……给别人知道了多不好!知识青年是不准谈恋爱的!”我看她的目光是试探性的,这潜台词我也明白。晓得我看到了前天的一幕,招呼我不要汇报。
为什么老是把我看成打小报告的人呢?我带点生气地说:“不要对我讲,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知道……”秀芹见我这种态度,便嘟嘟囔囔地说:“其实他们是早就认识的,也都二十二、三岁了。犯什么法?不过……唉!我姐姐怕……,可又没法抗拒这种感情。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有了爱情,觉得一切都那么可爱。’罗铭和她讲,他想要组织一个科研小组,要把这山沟沟里的农林竹茶业用科学武装起来。我姐姐也说,她早就琢磨过,想设计个小水电站,不能把桃花潭的水白白放掉……,嘻,这会儿都焕发出青春来了,本来嘛,青春……”她自己都神往起来,歪着脑袋自言自语,“爱情真有这么伟大的力量?”
我说:“……因为爱情是花朵,理想是蜜蜂……”说完,羞得我蒙起了脸。
秀芹亲热地搂着我,急急地问道:“是准讲的?”
“记不起来是谁的诗。”
“小妮子!你才十七岁就这么坏,”
我臊红了脸,打了她一掌。
罗铭和秀萍的爱情和理想,竟然会驱散了压在我心头许久的阴云。至少,他们开始信得过我了……
四月二十日
蘑菇了三个礼拜,王德发居然同意我们成立科研小组了。大家都知道是我的功劳……
我第一次找王德发谈,他正从哪儿酒醉饭饱后回到办公室,一面打着饱嘱,一面挥着手:“胡闹!……嗯!等一等……我想想看,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新动向!”他眯起眼,扳着指头数着一个个人名,好象有所发现似地说道,“……呵呵!都是‘臭老九’的子女,这是他们要夺权。好象我就不懂科学种田。哼!十年前,我在山里红公社,就放过‘高产卫星’……”
我简直哭笑不得。
第二次,我学聪明了点:“王部长,在你领导下搞一个科研小组,保你会得到上面的表扬,说你会抓革命促生产……支持新生事物!”
大概这顶高帽子蛮合适,他嗯了一声,眨巴着眼睛笑了笑,不讲什么新动向了。
第三次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小郑!行!咱们要搞一个科研小组!这就是‘卫星’!我到省里去开了两天会,一谈这事儿,成组长和你舅舅都夸赞我,说我有政治远见。现在有人骂我们不要科学,我这一着正赶在火候上!”
呔!倒好象他立了头功!
知青们都很高兴,唯独昔蕾不吭声。
我叫秀芹找昔蕾谈谈,希望她也参加进来,哪知道她冷不丁丁地说:“我不上当!”
四月二十八日
我哪里知道,成立科研小组的第一个会,竟要我们先来个大批判。批判的靶子是程璞,还叫他的老婆石亦凤也要发言批判。
程璞是特地从监牢里用汽车押送来的。
省革委会政工组的成跛儿居然亲自参加,把个王德发忙得七荤八素。沿路都插着红旗。民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一看到那个跋子,我马上想起霁霁游斗的情形,想起木木就是在他指使下被打死的。
我才意识到昔蕾讲的上当了。
各个公社都派了代表来,把公社的礼堂塞得满满的。我第一次看到程璞,大概因为我太恨成跛儿了吧,看到这个被他关进监狱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陡然产生了一种尊敬。
这次会上,成跛儿满脸笑容,开场白就是他讲的:
“同志们!桃花潭公社成立科研小组是一件了不起的新生事物,我代表省革委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看罗铭、秀萍他们简直是感动了,使劲鼓着掌。
“……今天所以要开这个批判会,因为这个站在台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程璞……”他转过脸,扫了程璞一眼,和程璞的目光对上了,他不由地微微颠动了一下瘸腿,“让程璞坐下嘛!我们要文斗,讲道理,真理在我们手里,不必要拿枪拿棒的动武嘛……。记得十年前,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我们放高产卫星四万八千斤是不尊重科学,现在就让他亲眼看看,我们是多么重视科学实验……”
底下的话我全没听见,我头脑里嗡嗡响,只注意着这张讲话的面孔,心里想:人的面孔怎么会变得这样快……
成跛儿的讲话后,接着是一个个公社的代表发言。都是照稿子念的,干干巴巴,台上台下,一片浑浊的声响……
王德发从人群里挤到我面前,说:“你快快准备一下,代表科研小组上去批判几句……”
这真是突然袭击,而且还要去突然袭击程璞。我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左推右辞,王德发已经有点火了……
正在这时,台上传来一阵笑声。
原来是山里红公社的一个代表提高了嗓门质问程璞时,程璞竟趴在桌子上睡熟了,打着好响的呼噜。
他老婆站了起来,冷冰冰地说:“我发言,他就是这个样子!碰到叫人打磕睡的报告,扯起呼噜来,都能震得人耳朵发麻……我都讨厌死他了!”
引起了哄堂大笑。
程璞被人捶了一拳,醒了,揉揉眼,还打了个哈欠,望望左右:“完了?那就该我下班了……”
在一片大笑声中,我感动得淌下了眼泪,因为他救了我。只有一个心地坦荡的人才会这样。
五月五日
今天是马克思的生日,我们把马克思的一条语录:“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抄出来,贴在科研小组的墙上。昔蕾走过,哼了一声:“你们真以为王德发让你们搞科学了……别糟蹋马克思了!”
这意思我只理解了一层,哪知道还有一层。
下午秀芹慌慌忙忙来对我讲:“昔蕾讲,当心王德发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在动我姐姐脑筋……”
这一说,我们两个都吃了一惊。转眼一想这话不是没有根据。
王德发近来一天到晚在科研小组里转,看见秀萍,眼睛就焊在她身上了。有一次,秀萍拿着试验管,做培养松毛虫白僵菌的试验。从背后伸来一只手一捏住了她的手。她回过头一看,是王德发,慌得连试验管都跌碎了。王德发涎着脸笑道:“秀萍,当心农药烧了你的手。哎呀!这农村里的劳动活都把你的手磨得粗粗拉拉了……”秀萍忙说:“不!不!这不是农药,我们来接受再教育,不要紧……”那时,试验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吓得她赶紧跑了出来。当她告诉我和秀芹时,心还在突突地跳。
秀萍不敢告诉罗铭,因为这小小的科研小组的屋子,是她和他的可怜的天堂。
唉!科学?……
五月十一日
王德发对秀萍的窥觑,已经到了馋涎欲滴的程度,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