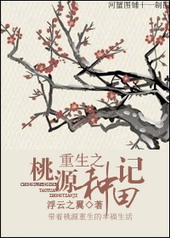破壁记 陈登科-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友?”
“对!都是蹲班房的……”
啊!原来他是刚释放的囚犯。因为程璞伯伯是“囚犯”,霁霁也是“囚犯”,现在我对“囚犯”这个名词并不反感……。对他那副油里油气的样子也原谅了。
赖文光很坦白:“不过我是真犯了罪的。当过小偷。现在,有时手还痒痒的。……你到市里公安局打听打听,讲二赖子,他们都知道……”
“二赖子?”我想起来了,程璞伯伯放出来之后,我去看他时,他讲了霁霁的许多情况,曾提到过二赖子这个人。我便问他:“你认识程璞伯伯?”
“噢,程磨子!”他竖起大拇指,“甩在地上当当响的一条好汉!他批评我,骂我,即使捅我一刀子,我也服帖。因为他是清官——老百姓都这样讲。牢里的牢头禁子都惧他三分。因为他清,就显出我浊得没出息了。至于那些贪官,去他球,跟老子差不离。有时我还觉得比他们强。干我这一行,跟电车,跑商场,提心吊胆,一天最多开十来扇‘气窗’……嘻,真叫本性难改,说溜了嘴锣!开气窗,就是扒人家口袋。有时扒着外地出差的小干部和走亲戚的乡巴佬,看人家寻死上吊哭天嚎地的,我心里还咯噔几下。可那些贪官,坐在家里,不用出门,自有大把大把钞票送到手里。大罗马,飞鸽牌,缝纫机,电视机,想啥有啥。他们红过一次脸吗?呸!”二赖子吐了一口痰,“这次出来后,我提了两瓶沪州头曲到劳动局走了一趟,无非想图个好一点的差使。程磨子知道了,把我骂了一顿:‘你这叫改恶从善了?!吹!没出息!过去你当小偷,现在是在喂大偷。’我一听,从皮里臊到皮外。他娘的,骂得痛快!我记得收了我两瓶酒的那个什么干事,一面看着我的档案,一面哼哼哈哈:‘赖文光呀!你现在还算人民内部矛盾。以后要痛改前非,你年纪轻轻哪来这套旧社会的旧习气呀!’嘻——!他倒是新社会的新习气了。我嘴里不说,心里想,你倒把老子生活费的三分之一痛痛快快偷去了。行!……回来的路上,我又差一点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所以没有下手,还是因为我想起了程磨子。因为他那双眼睛实在厉害。在他跟前,做不得幌子。是鬼装不了人。我还想做人……”
他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好容易我才插上嘴:“赖文光,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什么都对我讲。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二赖子哈哈大笑:“什么都讲?早呢,如果你们大学开一门社会学,请我来讲课,保险比什么批儒尊法的狗屁文章叫座。好罗!你有什么麻烦事儿找我,昔霁打过招呼的。他说你很懦弱。不过程磨子却夸你很有种,时世造英雄嘛!”他掉转头就走了。
因为碰到了这个二赖子,今天的日记记得这么长!怪事!每一次的报告会我都没有记满十句话……!
五月十七日
我一直想花点笔墨,记述一下这个劳动大学。今天难得有点时间,便写了一点,留作将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作为一种畸形的资料吧。因为它的全名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但这和毛主席写过信的那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作为“大学”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南北二十里,东西三十里,占了六个山头,穿过四条大河流。耕地一千五百六十一亩。这些数字,是在新生入学的报告会上,必定要提到的。
除了一个挺象样的礼堂之外,找不到一间教室,看不到一张书桌,更看不到老师了。
听说以前还在宿舍里上点文化课,自从张铁生交白卷以后,一节课也不上了。这也合乎逻辑,既然可以白卷进大学,当然也应该白卷毕业。
春夏秋冬,唯一的课程就是“大批判加大劳动”,这是我们副校长的名言。副校长就是成跛儿。正校长据说是省革委会熊主任兼的。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面。成跛儿自己也是每逢新生开学典礼才来一次。一来便讲: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大批判加大劳动——肯定的,他是很为自己的这句颇有独创的警句洋洋得意的。我们在实践中,深深领教了这两个大字是如何结合的。
举一个例子吧。去年收麦子的时候,两台联合收割机早已准备好了,可偏偏不准使用。不仅不准使用,还要我们在收割机面前开个现场批判会。说什么用机器收获不能代替思想的收获,所以非得用镰刀不可。二百多亩小麦,好不容易抢收了一多半,还没有脱粒,一场大雨,全沤烂在场上。据午收简报上评论,思想上的收获是大大的。不错,我们连着半个月尽吃用霉烂的麦子磨的面。
历史上记载,西汉初期就发明了铁犁。那是可以从汉墓的石刻上看到的。我们的劳动,如果也有人刻成石刻,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误认为是早于西汉的。人跪在稻田里,用两只手来拔草,还能比这更原始么?
不知谁在大门口的校牌上添了“原始”两个字,变成了“原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案便成了建校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案件。拍照,查笔迹自不必说了,居然还牵了几条警犬,跟踪追击查了几个月,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抓走了三个嫌疑分子。抓走的人除一个吓得大哭之外,其余两个暗自庆幸。因为即使误判劳改,也比在这个大学里强。三年五年,指日可待,总算有个出头日子了。
这里原来是劳改农场。现在农场划归大学。管理人员大多数还是原来管劳改犯的干部,这也算是鄙校的一大特点吧。难怪同学里暗暗嘀咕:“苦海无边啊!”
不过,对一些新贵们,这里就不是苦海,而是甘泉潺潺的水沟。新贵子弟们送进来,咬紧牙关(其实是舔舔舌头就行了)混上一年半载,就搭上了分配工作的跳板。混得好的还可以突击入党,出去便大小是个头目了。
到这里来的学生,被请来的就是“跳板系”。他们单独成立一个连队——这也是将来搞史料的人不可缺少的注脚。原始的劳动,军队的编制。
除了“跳板系”,还有两种人。一种是组织分配来的,大多数属于“调皮捣蛋”的。还有一种是骗来的,“大学”这个名字对青年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跳板系”和“调皮捣蛋系”的人为数都不多。大多数的同学是受骗上当来的。要划分左、中、右的话,当然“跳板系”是左派,“调皮捣蛋”的是右派,上当的是中间派。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超度众生的大权操在学校的政治部和市劳动局。现在,成跛儿派来执政的是我名义上的舅舅,而我的名义上的妈妈又是劳动局的副局长。照例,我是当然在“跳板系”的。然而,因为到北京为秀萍告了状,我又是货真价实的“调皮捣蛋”派。
自从我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之后,有的同学说我傻,否则早就进“跳板系”了。
我那个“舅舅”现在难得看到我。看到我也不说话,不过他的眼神我是明白的:“哼!看你老实不老实?!不老实,就叫你在这儿累死,苦死,永远甭想毕业!”
我决不理睬他,也决不投降。我要留在这里,再看透些黑暗……
六月十四日
昨天夜里,牛棚失火。害得我们一夜没有合眼。今天又到山冲里插了一整天的秧。每人一亩,少一分也不行……
回来的路上,经过医院,我拐进去看了看小朱——就是那个拿硬币算命的小朱。他是我们队里的“颓废派诗人”。“诗人”的称号是因为他喜欢写诗。据说六八年考进这所大学(其实应该叫骗进这所大学)时,一开批判会,他必定要写几首诗参加批判。逢年过节,出什么墙报,也几乎由他一个人包了。现在还能在礼堂的山墙上看到他的“旧作”。因为贴得太高,风吹雨淋,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孤本”了。我因为喜欢文学,仔仔细细地看过那“孤本”上仅存的几行:
这里充满了共产主义的阳光,
这里翻腾着劳动神圣的波浪,
啊!我是骄傲的海燕,
在阳光下展翅,在波浪上飞翔……
经过礼堂时,我常常拿小朱开玩笑:
“诗人,你现在的翅膀怎么聋拉下来了?!”
“唉!”小朱苦笑了一下,“……你知道么,我刚来的时候,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才能睡觉!”
“唷!积起来都可以出朱雅可夫斯基选集了!”“朱雅可夫斯基”是别人给他起的浑号。
哪知道,这个浑号传到了成跛儿的耳朵里。他居然在一次开学典礼的例行训话中,引为例子,板起了脸,训道:“……你们这里居然还有人自称朱雅可夫斯基,这得了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朱雅可夫斯基是谁?是苏修的颓废派诗人……”听的人莫名其妙。大家只知道苏联十月革命时期有过一个马雅可夫斯基,列宁称他革命诗人。要么我们孤陋寡闻,要么副校长弄错了。台上有人拉了拉成跛儿的衣襟,对他说:“校长,你讲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吧……”成跛儿一颠脚,骂道:“管他猪呀马呀的,反正都是畜牲……”哄堂大笑之后,小朱成了“颓废诗人”了。
从此,每期毕业就都没有小朱的份了。尽管他干活干得比谁都凶,算起命来却永远是“伍分”朝天……
可是,昨天晚上牛棚失火,他成了阶级斗争的英雄。据他自己说,昨夜走过牛棚,只见一条人影从里面闪了出来,朝东北方向跑去。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引起他的注意:莫非坏人破坏?他连忙推开牛棚,发现牛草已经着火。他一面拚命大喊:“不得了啦!牛棚失火啦!有坏人破坏呀!”一面便脱下身上的衣服去扑火。火势越来越猛,他实在压不住,便冲到火里面救出了七条老水牛。那时他已浑身烧伤,可是想到槽里还有一条才一个月的小牛犊子,便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火中……。等我们赶到时,牛棚已烧掉一半,小朱躺在地上昏迷不醒。那条小牛犊也确实蹲在他的身边,睁着惊慌的跟睛。
我在秧田里劳动时,已经听到广播里一遍接一遍播送着小朱的英雄事迹。学校政治部还附加了一个按语:“朱一勤同学的英雄行为,证明了我们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已培育了成千上百象朱一勤同学那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优秀青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昨夜的事,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牛棚纵火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保卫科正在严密追查……”
我拐进医院,到病房里探望小朱时,他的胳膊和背上都缠着纱布。保卫科的干事,学校“简报”的记者,把病床围得严严实实。我从人缝里望了小朱一眼。他的脸上挂满着汗珠,眼睛睁得滚圆,显得那么紧张,一迭声地问:“破坏分子逮到没有?……谁?”
我看他伤势不那么严重,就没有招呼便退了出来。在门口撞着二赖子。他朝我眨眨眼,耸耸肩:“赶明儿,我也来当一次英雄。他妈的,老子就是背时,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他做了个鬼脸,“真亏!我和那个‘颓废诗人,是前脚后脚。晚几分钟,这英雄就摊我来当了……”他伸了个懒腰,“乖乖,你们这儿干活比我在红庙里还累。这腰板都快断了……就冲这个,让老子在病床上睡儿天也值得……”
唉!这人……
六月二十四日
大概因为二赖子不止在一个人面前讲,他和现在当上英雄的小朱是前脚后脚,因为在小朱走过牛棚之前,他也从那里经过。就因为这个理由,他成了纵火偷牛的嫌疑犯……现在已经定案。据政治部的人讲,二赖子伙同附近的生产队里一个叫宋宾发的人,共同作案的。宋庭发是过去开过牙行、现在仍受群众监督的四类分子。二赖子当然更不必说了,是刚刚刑满释放的惯偷。在现场还拣到二赖子的烟头——这就是纵火的罪证。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话好说?还据说二赖子的态度极坏,死活不承认。说自己到生产队去过是不假,和宋庭发打过交道也不假,但都是农场派他去的。因为我们和生产队有一段灌溉渠道是伙用的,前一阵闹过水利纠纷。坏就坏在二赖子拍过胸脯,说歪理正理,全靠两张嘴皮。他自告奋勇愿作解决纠纷的谈判代表,和宋庭发只有两面之交。第一面是宋庭发听说他是农场的工人,托他捎双鞋给他的一个外甥;第二面就讲不清楚了,大概两人喝了一杯吧……
案情是从宋庭发身上突破的。他供认和二赖子喝酒的时候,阴谋策划了偷牛。至于纵火,完全是因为二赖子没有掐掉烟头,是无意的。
有声有色,有情有节,当然可以定案了。二赖子抗拒从严,真够他受的。……
广播了,今天提前吃晚饭,吃过饭整队到礼堂去参加公审大会。同时,要发给奖状,奖励小朱的英雄行为。
我只好挤着晚饭前的一点工夫,记下这点,开罢会回来,肯定深更半夜了……
果然已经深更半夜,但激动的心情不由得我又重新打开今天的日记……
我哪想去听这种会?!可是我们是连队编制,开会当然也点名,报数。得!到了会场,再溜到门口,即使歪在墙角打个磕睡也算对付过去了。何况是送二赖子重返“红庙”——我也学会了几句他们的切口了―一得给他一点交情。
会场内外,民兵和正儿八经的公安部队都布了岗,门口还停着囚车,这些都见惯了。新鲜的倒是今天的台上。一幅大红标语:“向活的雷锋朱一勤同学学习!”一幅白底黑字的标语:“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是红白大事一起办了。从后台走向前台的,也是一红一白。左边是戴上英雄花的小朱,右边是戴上白牌子的赖文光,中间当然是主席台了。我坐在头几排,先打量一下左边的英雄。小朱的伤还未痊愈,光着一条臂膀,还包扎着雪白的纱布,更显得有点英雄色彩。可惜他那张脸太不争气,在强光灯下毫无血色,嘴唇直打哆嗦,不断地揩着汗,尤其是两只眼睛,“诗人”的气质半点儿也没有了,只剩下了颓废。
再看看右边的罪犯。虽然低着头,却挺着胸,腰杆儿笔直,眼睛滴溜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