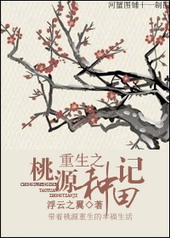破壁记 陈登科-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乘坐我的专机飞往上海执行机要任务。切切勿误,此谕……”
一看是蒋中正的签字,机场哪敢怠慢,而且又知道昔憬是委员长目前最贴身的人,连忙奉迎侍候,不到半个小时,飞机已经发动。
蒋介石打完牌,已是晚上七点钟,送罢客,宋美龄赶到美国大使馆去参加舞会了,这才发现昔憬不在外间。他按了几下电铃,进来的是许立。许立一进门便立正报告道:“戴笠将军再要我请示委座,对下午那份电报……”
蒋介石挥挥手:”“不就是日本又调来一个师么?……”
许立一愣,连忙回复:“不!是上海发现了共产党的重要线索,需要立即行动……”
蒋介石“唵”了一声,连忙进屋,找出那份电报来一看,大吃一惊。为了掩饰自己被一个贴身的副官捉弄了的窘相,他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娘希匹!都是吃干饭的!统统是娘子的儿子,混帐!……唵?还站着挺尸!昔憬呢?马上把这小子给我抓来……!”
许立笔挺地立着,心里却在暗暗高兴:“这下子证明了究竟谁才是贴心人,哼!那个小白脸,等着我来收拾吧!”
退出委员长的官邸之后,许立立即寻找昔憬的下落,从车库追到了机场,听说昔憬是伪造“手谕”,乘了蒋介石的专机飞往上海去的,马上又赶回来,向蒋介石报告。
这时,蒋介石连火都发不起来了。他懊丧地在屋里一圈又一圈地踱着步,最后一屁股埋在沙发里,叹了口气,说道:“我命令你,挑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连夜坐飞机赶到上海,一定要把昔憬抓到,要抓活的!”想了想,便提笔写了道货真价实的手谕,写完,扔下笔,叮咛许立道:“这件事,只准你知道,连美龄跟前也不许讲。问起来,只说是我差遣他去执行特别任务去了。要绝对保密!这意思……唵?”
许立当然是懂得这意思的: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居然钻到蒋介石身边来了,太丢脸。他啪地一个立正:“是!坚决执行任务!”转过身,就要走,蒋介石又喊住了他:“只要能捉拿到昔憬,赏金五万块。再说一遍,一定要活的。我要亲自审问,当面问问这娘希匹,我对他这么信任,这么好,他为什么还要参加共产党来反我!?”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上海静安寺路上弟弟斯咖啡馆门前的霓虹灯还亮着。
天空飘着雪,霓虹灯下的雪片映衬着这个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
咖啡馆里,中国人已经不多了,而外国人舞兴正浓。咖啡座中间的不大的舞池里,还挤得满满的,乐队正在奏着一曲“探戈”。
西北角那个僻静的火车座里,有两个穿西装的中国青年人,正在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轻声地交谈,嘈杂的音乐把他们谈话的声音掩盖了,只有他们互相能听得见。
这两个人就是昔憬和安东。
“出了叛徒,安东。你必须立即离开上海。”昔憬显然已经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安东。
安东拿着小勺,不停地在咖啡杯里搅拌着。他的心情很复杂,望望眼前的灯红酒绿,更想着大批大批的工人住在棚户里正饥寒交迫。革命需要他继续留在上海。杨浦区的工人,正在他领导下酝酿一次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的目的是声讨蒋介石的独裁卖国,要迫使他停止内战,要向他讨还民主和自由。这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安东想此时突然离开,不是临阵逃脱了么。
昔憬是深知安东此时的心情的,便用几乎是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必须转移!这是为了整个上海地下党的长远利益。蒋介石是心狠手毒的,我们要记住‘四一二’的教训,保存党的骨干,就是胜利!”
安东道:“我总得回去收拾一下……”
昔憬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回去!需要通知的人,组织上会设法通知他们……一切全由组织上来联系!”说罢,取出一张身分证明和一张船票,交给安东,“这是你的证明和到青岛去的船票,轮船明天早上六点整开。安东,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服从,绝不能有丝毫犹豫……”
安东接过船票和证明,说道:“我身上只有几毛钱……”昔憬不等他说完,便从身上摸出七块钢洋塞在安东的口袋里:“这里虽是洋人的租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在敌人的心脏,每一分钟都包含着危险……”
安东仍很平静地说道:“这个咖啡馆要到午夜两点才关门,这里看来还是安全的……”
他们俩又都要了一杯热咖啡……
昔憬端起杯子放在唇边正想说话,眼稍向门口一瞄,只见玻璃门被推开了,闪进来一个人,原来是许立。
昔憬原来估计天下雪了,即使蒋介石以最快的速度调兵遣将,至少也得在明天早上才能追到上海。哪料到许立竟会在大雪纷飞的夜晚乘着飞机冒险追来。这桩案子对蒋介石来说,严重紧迫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典型,分成英租界,法租界,日本人的地界,真正中国人自己管辖的地盘并不多。国民党特务要到租界上抓人,必须和外国的巡捕房配合,不然,就是秘密绑架。
许立赶到上海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他并不知道昔憬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个老牌特务为了在租界绑票和搜捕共产党方便起见,从各个租界巡捕房收买了一批包探,作为内线。他到弟弟斯咖啡馆来,是要和一个内线接头,并不知道昔憬和安东就在眼鼻子底下。
冤家路窄,事情有时偏会这么凑巧。
许立一进门,还没有和内线碰头,却一眼扫到西北角那个僻静的座位,和昔憬吃惊的目光迎上了。他心中暗自祷告:“上帝保佑,我许立真是官运财运双喜临门了!”但他也暗暗着急,这里是英国租界,由不得他随便抓人;秘密绑架嘛,又没有布置好,目前的对阵是二比一,许立是一个人来的。
许立脸上的神情没有瞒过昔憬的眼睛。昔憬此刻只想着如何掩护安东脱险,一面盯着许立,一面迅速判断周围的形势。
安东是背靠着许立的,可从昔憬突然中止和他的谈话,眼睛里射出吃惊的光芒的变化中,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情况。
许立一步一步地逼近了他们的座位,嘴角浮起一丝冷笑,目光正在各个座位上寻找他的内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焦虑。昔憬看见许立走近,镇定地站了起来,摆摆手:“请坐!老许,动作真快呀!”
许立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只手脱下礼帽,坐在安东边上,阴沉沉地问了一声:“这位便是安东先生吧!小昔,作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我佩服你有几手。好吧!咱们谈谈交易吧!”
昔憬也笑了笑,招招手,马上来了个侍者,他招呼道:“给这位先生来一瓶白兰地,我付帐!”随后转过脸,对许立讲,“其实应该你汇钞才是哩!诺,我,还有他。”昔憬指指安东继续跟许立讲:“委员长不会少出钱的……哈哈哈……”
白兰地送上来了。昔憬打开瓶塞,给许立斟上满满一杯,也给安东和自己倒了一杯:“来!干一杯,为许先生官运亨通!”
许立呷了一口酒,慢腾腾地说道:“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们两个是跑不了了。是大家识相一些呢,还是……嗯?……”他的一只手始终在大衣口袋里,而且清楚地听得见他在口袋里扳开了手枪的机头。
昔憬大笑起来:“老许,我们肯定可以跑掉,就在你面前跑掉,怎么样,打个赌……十五分钟以内。”
许立嘴角抽动了一下,冷冷地说:“好吧!打个赌吧!赌什么,你说吧……”
昔憬在侍从室的时候,就晓得许立是个财迷。昔憬手上戴着一块宋美龄亲自送的欧米茄金表,作为昔憬给她设计的小别墅的酬礼。金表后面,刻着:“昔憬小弟存玩”,还有一个宋美龄的亲笔英文签名。这块表,惹得许立馋涎欲滴。这时,昔憬就把金表从手腕上脱下来,放在许立面前:“赌这个!怎么样……”
许立一看这块羡慕已久的金表,眼都花了,夺过来就戴在自己手腕上,冷笑道:“你输定了!嘿嘿嘿嘿,我还你的将是一副手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已有了足够把握,因为隔着玻璃门,他已看到一辆汽车停下了,从汽车里走出来几个浑身穿黑长衫的彪形大汉。这种人,过去在外国人的巡捕房里称做“包打听”,既是地方上的流氓,又是洋人手下的奴才,大多数又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挂着钩。在租界里迫害、逮捕或暗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全靠这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杂交出来的特殊品种的警犬。
昔憬也看到了,还没有等这儿条警犬进门,就在许立稍一转脸的时候,拿起白兰地酒瓶猛地朝许立头上砸去……许立朝后一仰,血流满面……
咖啡馆里顿时乱了,经理、侍役赶了过来。昔憬抓住许立的手腕,叫道:“请看,他偷了我的手表!”一面说,一面脱下许立手上那只欧米茄金表,朝拥挤在周围的顾客说:“这是宋美龄亲自送给我的,表盖上还刻着字。”他摸出了自己的身分证,让大家看。
趁着一片混乱,安东跑了。
那几条警犬挤进了咖啡馆的门,只听见有中国人的说话声,也有外国人的说话声。
“这家伙,穿得挺讲究,竟会是个贼。”
“Oh!美龄女士送的。这位先生很了不起!”
咖啡馆的经理一看昔憬的身分证,哪敢得罪。亲自陪着昔憬,左一个道歉,又一个赔礼,并请他到后边经理室去。昔摄大摇大摆地在人丛中走过,朝那几个“包打听”扫了一眼:“你们地盘上的事情,还不关照关照……”
那几个穿黑长衫的人本来只是来接头,并不了解什么任务,看看一头歪在座椅上的许立,半片脸全是血,昏迷不醒,再看看昔憬那副派头,又是蒋介石身边的副官,宋美龄还亲自送他手表,一早就猫着腰,摘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跟在后边,送他走进屏风后面。
停顿的乐队又吹奏了起来。
等许立稍稍苏醒过来,晃了晃脑袋,记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望望站在他身边的那几个穿黑长衫的人,气得一拳捶在玻璃桌面上。
等许立抹去脸上的血,包扎妥当,冲进经理室时,昔憬早已坐了出租汽车,远走高飞了。
昔憬离开弟弟斯咖啡馆,连夜把安东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尤其是对必须转移的重要线索和接头地点,一一作了安排。第二天一早,又赶到码头,亲眼看着安东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直等到轮船离开码头,才吁了一口气。
现在是自己的去向问题了。
落了一夜的雪。江南的雪本来是积不住的。第二天,时晴时阴,上海人称之为乌糟糟的天气,马路上也是乌糟糟的。残雪、泥水,一塌糊涂,走路的人都换上了套鞋,昔憬那身打扮,尤其是一双贼亮的皮鞋,十分惹人注目。
更加糟糕的是,不到九点钟,上海滩上的十来种大小报纸都刊登了昨晚弟弟斯咖啡馆发生的事情。经过记者们的添油加醋,有的把昔憬描写成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有的写得象福尔摩斯探案那么离奇,反正昔憬的形象和名字,已在街头巷尾传说开了。
他必须立即离开上海,可现在身边只剩下两枚银角子和十几个铜板。
昔憬觉得局势十分严重:许立不是笨蛋,这些小报上的消息,又帮了许立的大忙。昔憬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包围网,象他这样,混不到天黑就一定会落到许立的手心里。他从外滩走到南京路,浏览着一个个百货公司的橱窗。从橱窗的玻璃里,可以窥视前后左右,判断有没有盯上“尾巴”。从永安公司到先施公司,斜穿马路时,他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注意上他了。
他立即跳上了一辆电车,那两个人也跳上了电车,这就更加证明他判断的正确:尾巴!一定是尾巴。
电车开了两站,在跑马厅,他跳下了车,掉过头又跳上回头的车,那两个人也跟着上了这辆车,但就在车门快关上的时候,昔憬从另一扇门跳了下来,门关上了,电车响着铃挡驶去了,这两条尾巴暂时甩掉了。
他不敢怠慢,马上叫了一辆黄包车,向虹口方向奔去。那个拉黄包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苏北人。过了四川路桥,昔憬就和他攀谈起来,知道他是三一年发大水时,从苏北流浪到上海来的。便有了共同语言……
昔憬自己也没有一个目的地,只顾叫黄包车一回儿穿这条路,一回儿拐那个巷子。黄包车夫很奇怪,便问:“先生,你到底要到哪儿去?”
昔憬想了想,大胆地说:“你只顾走,我老实告诉你,我身边只有两角钱,你看拉到什么时候够你的车钱,你就停下……”
黄包车夫停了车,回过头上下打量了昔憬一眼,心里明白了一半,便道:“先生,再过去便是提蓝桥,那里有巡捕房,我看您还是顺着苏州河走……”
这一问一答,彼此心里都有数了。昔憬认定这是可以依靠的群众关系,便道:“我俩是老乡,你能帮个忙么?”
黄包车夫道:“你说吧!”
昔憬道:“我和你换一套衣裳,好么?”
黄包车夫先是一愣,而后想了想,说:“先生,你信得过我的话,前面就是我的家。我家就是一条破船,你把身上的衣服换一换。凭你这身穿戴,坐在车上走街穿巷,是遮不住人的耳目的。你要信得过,就把衣服存在我的船上,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来取。我的破衣裳也由着你挑!”
昔憬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黄包车夫把昔憬带上了他住的那条破船。黑稠稠的苏州河里,这样的住家大半是从苏北逃难来的,上海人叫做江北船棚。换过衣服,昔憬把手表也脱下来交给了黄包车夫,说道:“老乡,你不要问我姓甚名谁,我也不请教你高姓大名……”他握着黄包车夫的手,拍拍他的胸脯:“你心好,相信我也不是个坏人就行了。”
昔憬离开破木船,再回到四川路桥时,只见一大堆人围着桥墩子,争着看一张刚刚贴出来的通缉令。通缉令上印着他的照片,下面写道:“……如果有人捉拿到要犯昔憬,赏洋五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