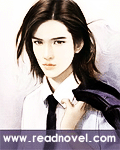劳碌岁月-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周狗子便与老婆走出来,那女人眯缝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直端详了年轻女子好久,那女人笑了。“好美呦……”女人发出赞叹的声音,走上前来拍着她肩膀说:“你虽破了,但仍是年轻俊俏,不过人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你就在这里嫁个人怎么样?”
她望着这个中年女人,她终于擦干了眼泪,但目光里以有几丝疑惑,她说:“可,可以的不过是真的么?”
中年女人放肆地笑了,周狗子也嘿嘿地笑着。
于是他们便领她到本村一户姓纪的人家,那纪家儿子,口吃,但忠厚老实,甚直竟有些痴呆。
纪家是那村的富户,父亲早丧,有于一个老母亲,只有一个儿子,那呆里呆气的儿子也取过几个老婆,但都因为不生孩子而被休掉了。
纪家母子见了姜小玉都非常高兴,她年轻俊俏,就像春天里盛开的梅花儿,那纪家儿子见了她竟若获得至宝一般。
他很爱姜小玉,他把她当做最美最神圣的女人,他甚至崇拜她。
但她并不以为然,她只把他当做自己的救命恩人,她要替他生个儿子,她也像纪家以前的媳妇一样——不会生孩子。
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教书先生,他告诉她,她丈夫有玻她才恍然大悟,她笑了,无奈地笑了。
她竟一下子爱上了那个教书先生,他有文化,有知识,温柔而懂情意。
有一次她偷偷地随他到村后林子里去,她吐露了爱慕之情,他紧紧拥抱并亲吻了她。
她是多么喜悦和快乐,她如春天的小鸟般又唱又跳。
后来,她就与那个教书先生逃跑了。
他们跑掉了,那纪家儿子万分的痛苦、他一生中最爱那一个女人,但是她走了。?
她走了,纪家儿子却一直在想念她。后来,他虽然又娶了妻子,但他并不爱妻子,他只把妻子当做朋友,以致妻子与人睡在了张床上,他也并没有多么痛苦。
后来,妻子生了儿子,但儿子并不是他的,是一个叫做阮木儿的男人的。
讲到这里纪德就流下泪来,他哭了。
木柯平望着纪德悲痛的样子,他再也不想听纪德讲些干什么,他站台票起身子,有些尴尬的笑着告辞要走。?
木柯平离开了纪德家,他走在小路上,他思索着那个故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只让他感到阵阵伤痛。
11
木柯平亲身经历了那个痛苦时代,那个狼烟四起战火纷纷的时代,他与他的部队在那个时代苦苦为保卫祖国流血与牺牲。?
现在他们把侵略者驱逐出了自己的国土,他们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木柯平的心并不能平静,木柯平与他的部队并不能歇息,他们马上要投入到另一场战斗跳动产。
在战斗的前夕,一切显的那样紧张。
木柯平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在想金子,那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子,他的未婚的妻子,她在做什么呢?
战争使他们不通音讯,战争使他们遥相隔离。
有多久没有相见了?金子的一频一笑在木柯平眼前浮现,他心忽然就充满了惆怅,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他长长的叹息。
战争,令人生厌的战争,令人恐惧的战争,就像魔鬼一样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战争一旦到来,你就必须去战斗,必须在枪炮声中拼死冲杀。
木柯平是一个军人,是一个不畏战争的人,但他想念那个令她魂牵梦萦的女孩子。
他又想起了秋野叔叔与姨娘,想起那无限慈爱的面孔;想起了生身爹娘。
他又要带领他的部队出发了,飞越黄河到江南去,在机如鸟群的轰炸里求得生存。
他现在好好活着,明天也许他就死掉了,并且像一狗一样被随处地埋葬。
这并不让他感到悲哀,他悲哀的是自己死了也许金子根本就不知道,金子还会苦苦等他。
不过他还是尽量不去想那些。“明天又要出发了,”他想。他透过窗子向外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他忽然觉得自己被抛弃在荒无人烟的地带,一阵风吹来,有瘦黄枯干如鸟羽的叶落下么?一如一声琴音倏地飞逝。
他笑了,面对荒凄他有了一丝笑意。
他早已熟悉了这荒芜,尝过了这被抛弃的滋味。
战争就在那个夜晚开始了,他指挥他的部队渡过了黄河,在南岸歼灭了他的敌人。
在兄弟部队的猛烈攻击下,敌军开始全县溃退。
但在战役中他受伤了,他被送进了部队医院。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上战常后来新政府成立了,他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功臣。
他与金子结了婚。
一个月若金玉的夜晚,他携金子走在省城的街道上,那是秋天,枯叶飘若摇曳的琴声,他们穿行在枯叶纷零中,他伸手搂过她的肩,她挣了一下,没挣开,却低下头羞涩的笑了。那个时间他们还没有结婚。
他望着满天的落叶,她望着美好若娇艳少女的月亮。他说:“金子,我带你到一个没有落叶的地方去。”她望着他,她的眸子晶莹而清澈,就像一汪活泼的泉水。她天真的问:“那儿有月亮么?”他哈哈的笑,他说:“我不告诉你。”
她就冲撇撇嘴一下挣开他,她向前跑去,一边跑,一边回头冲他笑,他便追她,她竟跑的飞快,一会儿在树后隐藏了,一会儿又跑在了前面。直至到了郊外,他一下子抓到了她。两人面面相觑着,气喘吁吁。他忽然就搂住了她。她任他搂了,互相凝望着对方,彼此躯体之间有一股热血奔流。他低下头去吻她娇艳若樱花的唇,她的身子起了一阵颤栗,她情不自禁,她迎合他她的身子开始扭曲,她双眼朦朦胧胧若一缕水,他吻她的劲、她的胸,她抵抗不了,她忍不住呻吟,后来他们拥抱着躺在了那块坡地里,他们绞缠在了一起……木柯平与金子结婚了,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与他们的父辈所结婚的时代不同,他们拥有了自由,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幸福。他们的生活安安静静,在星期天假日他时常带她到公园或者郊外或者……他们活得那样滋润,他们高声赞美着世界、赞美着生活。
后来,他有了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中华,又叫甜甜,真的,那时他们脸上总露着甜甜菜的笑,以至几十年后,他想起带着儿子在城外放风筝的事,他脸上还会浮起那发自内心的对生活赞美的笑。
他带着儿子在草儿刚刚冷清的田野上奔跑,他们不时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声,而金子远远望着他们、望着他们手中的风筝脸上也流露出会心的笑。
只到有一天,大街上出现了游行的人群,出现了批判和纠斗,他们家忽然闯进了一群毛孩子,极其蛮横地翻箱倒箧,他之被那群孩子带走了,在被纠斗一番以后,他被关进了监牢,开始了一段暗无天曰的生活。
天空布满灰尘,他看不到阳光,看不到阳光下青草的生长。他不知道窗外发生了什么。
他想念金子,想念金子。
他愤恨,但他无可奈何。
在冰冷漆黑的夜里,他望着冰冷漆黑的牢房,泪顺着他的双颊滚淌下。
在战场上,在生死的杀里,他没有流过一滴泪。
但现在一种悲痛让他难以忍受,悲痛让他泪落如雨。
甜甜年幼,甜甜也踢着那些人到处纠斗了么?甜甜也受到迫害了么?他的妻子,他爱的金子也一定在这动荡的岁月里受苦受难。?
“这世道又怎么了?”他想。
夜,漫漫的长夜,他身边只有漫漫的长夜了。
这夜会不会过去,明天能否迎来新的曰出呢?他相信。他的朋友师长亲人会来营救他,他们正在与那颠倒是非的人作斗争。
后来,他回想那段岁月,他铭心刻骨,那段不再生产不再前进到处批斗到处斗争的岁月,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
那是一场恶梦,十年恶梦,受尽非人折磨。
十年里,甜甜有一件让他一生都感觉羞愧的事,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是非不清的他竟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他与那些是非不清的人们一样叫骂着去纠斗与父亲共同出生入死的人,去纠斗那些曾为共和国的建立而赴汤蹈火宁死不屈的人。他们把那些人拉到人群中间、骂打,牵着去游行,然后送进牛棚或监狱,有些人受不过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就那样悲惨的死去了。
他是罪人,他是那个时代的罪人,他与父亲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感无地自容,他对不起自己的名字,他没有让父母实现在他身上的希望。
他的父亲原谅了他,当父亲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那一刻,当千万缕灿烂阳光照射在父亲身上的那一刻,父亲那坚毅的脸上泪水纵横,父亲的脸瘦,明亮的眸子深陷。他哭了,十年里,他的父亲老了,头上有白发了,十年里父亲,坐过多次监禁让父亲的心都快破碎了。
当他回想起那段岁月,他的心就莫名的烦燥,他就难以平静,在后来的日子里那段岁月成为他心灵里最深的伤痕。
那是一个不平静的痛苦的年代。
12
阿光走过那片土岗子去,他的心像被捕的鱼一般乱跳,西边的夕阳若樱桃般鲜艳、田野里吹着晚来的凉风,玉米苗儿翠绿,被风一吹像火苗子一样飘动。他走过土岗子去,在那个大水坑边的野苇丛边,他要见到春梅。
春梅咯咯的笑着,她笑什么呢?那个春天,温暖的阳光像瀑布一样,她的眸子也若瀑布一样秀美满布活力,他靠近春梅,他问:“你笑什么呢?”她指着他的头,他笑个不停,他便很疑惑地伸手摸摸头顶,竟摸下了许多桃花瓣儿,他也笑了,脸上涨出一大片红来,想不到那桃林的花儿竟落了他一头。她的眸子若瀑布般秀美,在那个月色如水的春夜里,她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们相爱了。在这个夏日黄昏,她约他到这片芦苇丛边。他望着她、他的心还在怦怦的跳。他问她;“你爹娘让你出来了么?”她摇头,她说:“我偷偷来的、爹娘知道了会打骂我的”他抓住她的手,她说:“那怎么办呢?不能总偷偷摸摸的呀。”她叹了一口气,眉头皱了皱。她说:“这样吧,你们差人到我家求婚吧。”他想了想,便点头,然后把她抱在了怀里。这时候他们彼此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可以嗅到对方的气息,可以解摸到对方的渴望,他吻她颤栗的芬芳诱人的唇,吻她的颈与胸,她要摆脱但怎么也摆脱不掉,她几乎是在挣扎但又是在迎合。他慢慢解掉了她的上衣纽扣。他们翻滚着躺在芦苇丛里……谁也无法忘记好一天,那一天土地承包给了每个人。那一天纪德望着天空笑了,儿子阿光也笑了。纪德拍着阿光结实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好干吧,只要,只要、上面政……政策不变,我,我们就好过了。”
阿光是在那一个春天认识了春梅,邻村的春梅,水灵灵若春葱的春梅。
阿光的生活中另有了一种温馨和向往,有了一种甜滋滋的幸福。
阿光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他心就像那麦苗一样向上狂长。
白天他在里拼命的干活,晚上他会等她,在小河边,在林子里,在村后的土岗子上都留下了他们携手并肩身影。
但后来春梅的爹娘发现了他们,村里的人开始议论他们。
他们被限制了,他们无法再见面。
而这个黄昏他们彼此彻底献给了对方,灵与肉没有丝毫的保留。
当月亮慢慢升起的时候,月光若银练一下洒在了田野里,洒在了水面,洒在了芦苇丛里,洒在他们的躯体上。
黄昏是那么宁静,只有风窃窃地拂过。
他们穿好衣服,她躺在他怀里,她说:“阿光,我的人都成了你的,我一辈子都跟定你了。”他说:“我会娶你,我一辈子都要你。”她幸福地笑了。他再次亲吻她光洁细嫩的脸庞。如同精心呵护他的花朵,唯恐她会被风雨打碎。
但是他求婚没有成功,他的媒人被春梅爹娘驱赶出了家门。
他有多么恨,阳光是照射在庭园里,但竟若一缕缕火焰燃烧,哔哔剥剥的声音在满世界里爆响。
他围着村子乱转,而他的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
他的父母变的沉默无言,他们不想说些什么。
他哭了,他发现自己的泪珠竟若乒乓球一般大,满地的乒乒乓乓。倔的心乱了,他列心干活了。
只到有一天他发现村口的老井被人埋掉了、发现别人的庭院里有了压水井,他了现别人骑着闪亮的自行车在眼前晃了。
他的心有一种莫名的浮躁。
他好像在做着梦,他在床上翻来覆去。
谁家的向日葵在墙内艳艳的举出来,如幸福灿烂的笑,他笑,他却骂了一句,然后他又睡去。
他睡去了,他看见春梅一个人走在一条小路上,那路窄窄的就是铁丝一般。路两边是滔滔浊水,他惊呼,春梅回头看,却一下落到水里去了。他到处乱抓,终于似乎抓到了什么,是春梅的头发,但仔细看时又没有。他只闻到了一股香气,像兰花一样幽幽地,像满含凄怨的瞳孔,而那瞳孔扩大扩大,直把他的心笼罩了。他就一下醒来,他只看到天空中高高的太阳,若同一把毒伞般罩着。
他翻身下床走出门去、看见年老多病的娘从田间背着一筐草歪歪斜斜地走回来,他心就要碎了。他替娘接过那筐,默默地,他叹了一口气。而娘说:“阿光啊!你别呕气了,地里的活还得你干呀、我们老了,没有用了……你与春梅那妮子就散了吧,哪有那么如意的事呢?我与你爹也不是一辈子过来了吗,人就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纠缠不清呢?
阿光望娘,他仍然不说话、仍然叹气。?
“阿光、你不要叹气了吗,”娘说,“你要听娘的话、娘不会害你的。”
他便哭了出来,泪水俨若河水般控制不住,他发现自己像风中的枯草了,没有了根基似的,摇摆不定了。
他只感到有一阵风吹来,风吹来了、他顺着那嘶嘶的风声走去,他走在田野里闻无人迹,人呢,人呢?他问。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去了风,还是风在吹,但树与草都没有摇动。他一个人走着,没有任何目的、他的心是空的、空洞洞口的,他只是向前走,他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