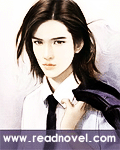劳碌岁月-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雪莲嫁给了纪德,从此她有了一生的痛苦。
我们说雪莲是弱女子,相信命运也无力反抗,她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普通的下层女人。
纪家为了延续烟火竟使她被人强暴,她的生命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她竟说不出来,她弄不东什么是幸福,即使后来她的儿子阿光给了她温暖,她也时时沉浸在悲伤中。
她一生都在面对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一生与这样一个男人厮守,有时她会怀念与阮木儿相处的那段美好时光,那却是心中最沉的痛。
她的一生是美好破灭的一生。
而纪德在这世上活着是一种悲哀,他最爱的女人与人私奔,他身边守着他不爱的女人,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连他的儿子都是别人的。
他活的很懦弱、痛苦、悲哀、无奈。
他的一生是被囚锁的一生,但更多的是美梦的破碎。
纪德马上要死去了,他躺在煤火烧得热热的炕上,他却发觉自己躺在冰冷的雪地里,不仅是他躺卧的地方冰冷,一切都是冰冷的,包括人们的声音与行动,那一切又好像是他很遥远,他像是在梦里,他在梦里走着,两面是黄土墙,街上没有人,落叶若人声一样喧嚣,他迷迷糊糊地走着,走进一家院子,他似乎很熟悉,但他又不能辨认,有个人在厨房里劈柴,阳光洒在那人的脸上,竟无法看清那人的面孔,他走过去,想与那人说些什么,但他还是无法看清那人的面目,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瞎了,就到院子望,看见了落叶飘飘,他的心一下抽紧,莫非见鬼了么?霎时毛发皆张起来。他伸手出来在上面狠狠咬了一口,竟真的不见血水流出,他吓得呆立在那里,那人从厨房里走出来,一阵风吹去,像有人影飘过似得,那人的脸上露出微笑来,他看到他的心就要从腔子里蹦出来,那人竟是他早已死去的爹,而爹的模样很年轻,微笑着站在那里,“纪德,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爹问。纪德全身颤抖着没有回答,而爹就过来拉了拉他的手,他就感到些温暖,他说:“爹,你是人,还是,还是鬼?”爹仍然在笑,却没有回答他的话。他看着爹,发现爹脸上的笑是红色的,越来越红,竟若有血液在流动,但这次他没有害怕。爹拉他到一个房间里,他就见到了娘,娘躺在床上,不过那床上还有一个男人,娘与男人都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娘显得年轻、漂亮、娘不断亲吻那那男人,亲吻的声音很响,他就有些恶心,而爹的脸上依然有红,他知道爹仍在笑,他就想呕吐了,他叫:“娘,娘!”娘才知道他来了,慌忙地穿衣服,那男人也慌忙地穿衣服,穿好了衣服,娘就问:“纪德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有说话,摆出很冷漠的样子,娘就笑,娘的脸上出现了粉红,很害羞似得,娘说:“这里就是这样子的,这是规矩呢……”娘是说她与那男人的事,而纪德就不信,娘也不再跟他说些什么,而是拉他到另一个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里他见到了爹,爹怀中搂着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爹正在那剥那女人的衣裳,而那女人则搂着爹的脖子热烈地亲……他就走出那房子,他的心里说不出是伤心还是悲愤,而娘跟随他出来,娘对他说:“你还要雪莲吗?不要可以自己找的,找一个你爱的而她也爱的女人,这是规矩。”说完了娘就走了,而娘的声音却像刀子一般在他心扉上刻上了回声。
一刹时,他竟不知如何选择了,什么是规矩呢?他更加弄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是个很守规矩的人,所以他娶了雪莲,而现在呢?他应怎么办?
他走进了一间房子,那房子里有几个美丽的女人,而其中一个正是雪莲,他望见她的时候笑了,而她也笑了,但他竟从没有见过她笑的那么美,那么甜蜜,于是他痴痴的站在那里,他想他还是娶雪莲吧。
于是他就娶了雪莲,但后来的故事就是重复叙述纪德的一生了。
纪德不会明白,也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雪莲。
纪德是不了解雪莲的,但他要娶雪莲。
直到后来,那是他死去以后,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了他的孙子、孙女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年轻的孩子们,他见到了林箕天,见到了白玉宛,见到了他们的生活,看到了他们的沉醉一疯狂,他才在无限感动之后有了一次彻底认识,但他那时已经死了,他的灵魂却不会安宁。
他在天空中飞翔,在风中飞舞。
他自己装上长长的脚,但这脚不会在土地上留下什么印痕。他的身子是轻的,轻的似羽毛一般,甚至像风,对,就是风。
他看到自己的孙子纪春富,他也看到了木青,他看到他们正在争吵。(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做着许多孩子,而木青则在另一面讲着什么,据说那个大房间是教室。)纪春富与木青在争些什么,后来木青甜甜的笑着倒在了纪春富的怀里,他觉的好像是木青战胜了自己的孙子。
有时他能想起木伟,教书的木伟,以及想起木伟的那间不大的教室。
他看到了白玉宛,她瘦弱的身躯在风里走,她哭,但笑的时候更多,她紧搂着林箕天的肩。
他也看到了林箕天,林箕天默默思索着什么,不管外面有多么大的风雨,林箕天都坚强地没有动,林箕天紧紧搂着白玉宛的肩。
他会想起他的儿子阿光以及阿光爱着的春梅,他会想起春梅的死,他会流下动情的泪。
他看到了孙女纪春敏,纪春兰,他看到了春敏的灵魂,他想告诉她:“春敏,你要守规矩。”他看到了纪春兰,十七岁的兰兰正在与一个男生谈恋爱。
他甚至看到了林泉,林泉正撕扯着妻子的衣衫,而林泉的妻子就大声地哭泣,林泉是不爱妻子的。
他笑了,他不知自己笑些什么?
他笑自己么?他笑别人么?
他飞走了,他死了。
在一个雪花飘飘的黄昏,他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他的子孙都跪在他的灵前,直到这时他才彻底想起了什么。
他想起了他的儿子阿光及阿光的故事。
20
词典上说,青春指人的青年时期。而人们又普遍认为青年时期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对于每一个人讲他或她都有自己的青春,但对于每一个人讲青春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当我们谈起纪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青春是在乱纷纷的战争时代渡过的,他的青春就是逃难就是痛苦,甚至可以把他的青春诠释为屈辱和懦弱,他无法与他的后悲相提并论,这一点直至他死去以后才清醒地认识到,他才知道自己的青春是一片死寂。
但不管怎么样,纪德已经死了,连同他那死寂的青春都被彻底埋葬了。
死寂的青春死了,也葬掉了,但他或她留下了些什么……阿光含着泪跪在纪德的墓前,他想起爹在他印象中的所有脸孔,那些脸孔重叠在一起,悲喜、忧欢、苦乐……构筑成爹极为平凡的一生,但这些竟似砸破了五味瓶并且让他尝到了。
其实他与爹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有些东西根本无法分辨清楚。
他哭了,声音嘶嘶哑哑,是在哭爹的死,还是在哭他自己命运中的苦?
那时候残阳照耀着雪地,北风抽打着老树。
那时候白玉宛在老树下等林箕天,她与林箕天一起到铁文家去,铁文是她村的小学语文教师,三十多岁,爱好文学,“秋野”文学社社员,《乡韵》杂志编辑。
铁文属于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
铁文喜欢安静,在静静里构思与创作。
铁文的思想又绝对开放,许多乡下人不能接受的思想,他绝对能接受,乡下人不去想的他去想。
铁文的妻子艳萍,三十岁,读过几年书,并不爱铁文,她与铁文的结合是因为看中了铁文是教师,是因为教师拿着国家的钱。
艳萍是爱着铁文的名声,爱铁文能挣到国家的钱。
而铁文却是爱妻子的,甚至是非常的爱,他不知妻子是轻贱的女人,竟背着他在外面与别的男人相好。
直到后来,他听到了风声,他询问艳萍,艳萍颤抖着跪在他的脚下,说她再也不敢了。
而他已经知道艳萍其实并不爱他。
他笑了,笑的宽容而潇洒。
他知道自己爱着不爱自己的女人了,他时刻准备着艳萍的离去。
而这个夕阳照着残雪的黄昏,林箕天与白玉宛携手来到他的家里。
他望着这对年轻人,这对恋人,他深为赞叹。
他没有想到在这乡下竟还有这样一对人儿,他们勇敢、坚强、忠诚,为他们的美好生活而不屈不挠。
他让林白二人坐下,给他们倒水,而艳萍也从里间里走出来,冲他们笑了一下,径自走向院子里,院子里栓着一条黄色的狗,艳萍是爱狗的,她径牵了那狗走出门外去。
白玉宛从自己乳白的皮挎包里取出一沓稿件来,白玉宛对铁文说:“这些我们都看过了,年再看一遍吧。”
铁文点点头,把稿件收好放到书橱里,他问:“你们最近有什么新作吗?”
白玉宛望一眼林箕天,她说:“箕天正准备写一个中篇呢?”
“是么?”铁文说,“箕天,你谈谈看。”
林箕天笑了一下,林箕天说:“还在构思当中,现在也仅仅开了个头,主题是写一些腐败现象,想把农村不道德,不文明的东西拿出来让人看。”
铁文也笑了,铁文说:“写吧,写完后我先睹为快。”
“嗯,我还没告诉你们,”铁文又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新人,很有才气的,姓陈名莫,是个女孩,十八九岁的模样。”
“是么?”白玉宛说:“她家在哪里?”
铁文说:“她家很远,在市区,有一百多里吧,她是在市文联主办的《春水》杂志上读了我的小说而来找我的。”
白玉宛就笑,白玉宛说:“你艳福还不浅呢,竟招惹十八九岁的姑娘?”
铁文却显得严肃,“不要开玩笑了吧,我都是有老婆的人了,”铁文说。
而林箕天也笑,“做你的妹妹吗,”林箕天说。
铁文就瞪了他们一眼,铁文说:“我对她写的东西很有兴趣,我拿来让你们也看看。”说着他从另一个书橱里取出几页稿纸来,递给他们。
那稿纸上的字很清秀,那是两首短诗很有些灵气也很有些艺术品的样子。
读完那两首诗,白玉宛与林箕天都很称赞。
而铁文也笑了。
铁文说:“这两首诗在本期《乡韵》显要位置刊登你们有没有意见。”
他们摇头,“不过、我想见见她,”白玉宛说。
铁文望了一眼白玉宛,铁文说:“也许她还会来,不过你可以给她写信的。”
“有电话吗,给你留电话号码了吗?”白玉宛就问。
铁文犹豫了一下,终于又说:“好像留了,不过我得找一找。”
白玉宛与林箕天听了便相对了笑。
电话号码几乎是没用找就到了。
铁文把电话本给白玉宛,“也许她过几天就会来呢。”铁文再一次说。
“是吗?”林箕天问,“让她到文学社去吧,我也想见见她呢?”
白玉宛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便与林箕天起身告辞。那时候太阳落下山去了,满地的雪仍把天地之间映的明晃晃的。回来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一片林子,他们拉着手走过那片林子,他们忽然听到了男女的嬉笑之声,他们看到了,铁文的妻子艳萍正躺在村长的怀里,而村长就要亲她,她正笑着躲。
白玉宛心里一沉,就赶忙拉着林箕天走避了。
他们想是否回去告诉铁文呢?
他们回去了。
而铁文只叹息了一声,就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了。
他们就劝慰他两声,而后匆匆告别了。
晚上八点艳萍牵着狗从外面回来,她见自己的丈夫坐在沙发里,他一脸的冰冷、而他的脚下有许多烟蒂,有的还散发着烟气、房间里就充满了香烟味。
“你怎么了?”她小心翼翼地问,她心就像一条鲤鱼般乱跳。
他没有说话,又点燃了一支烟。
她慌忙拿扫帚替他扫去脚下的烟蒂,但就被他制止了。
他说:“艳萍,你坐下,我与你说件事。”
她就坐下,躲避着丈夫望过来的眼睛。
“艳萍,你想跟我离婚吗?”他忽然问。
她的脸忽然变的苍白,她惊恐而无措的样子,许久,刀子才说:“你开玩笑吗?”
而铁文摇头,铁文说:“不。”他很认真声音很有力。
“你想跟我离婚吗?”他又一次问。
她低下头去,她说:“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了?”
“我不想约束你,不想给你带来不快,”他平静地答。
她不再说话,她忽然就好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物器了。
铁文却继续说:“我们还是离婚吧,我们还没有孩子,会很轻松,你可以提出你的合理要求的,包括财产或者其它什么的。”
她抬头望了他一眼,她眼角闪烁着亮晶晶的东西。
她忽然发现一切都不现实了起来,她好像是坐在了梦里一般,什么破碎了,连她的身子都在破碎声中有了破碎的感觉。
铁文望着她,铁文说:“你考虑考虑吧。”
铁文站起身来走到书房里写东西去了。
她就呆在那里,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了。
她忽然想笑,但她无法笑出来。
她弄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卑鄙与下贱了,她竟流下泪来。
她哭了,无声地泪淌落她的脸颊。
她与他离婚以后,她又怎么办呢?村长是有夫之妇,又怎么可能要她呢?她只不过是村长的小情妇而已,她还是些什么呢?
但铁文是要跟她离婚了,如她不同意的话、铁文也会离开她,他会选择别的方法让她同意。
她深信铁文会那样做。
她走回卧室里,躺在床上,望着房顶,她的身了就若被抽空了一般。
而后来她去找村长,村长一把抱住了她,亲她,她挣扎,她说:“我怎么办呢?”
村长笑,村长说:“我会有办法的,你着急什么呢?”说完一下把她按倒在了床上。
那个晚上她很晚很晚才走回家去,那时候铁文仍坐在窗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