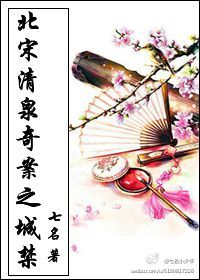清泉石上流 石绍河著-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吧,身子要紧。他见我给他递钱,忙推辞说:我来这里不是向你私人要钱的,你们拿工资的,一个月也就那么几个死钱,上要孝敬父母,下要供孩子上学念书,钱不经用啊。我的困难,如果政府能帮助一下更好,实在帮不了,也只好自己慢慢想办法。说完,把钱推还给我。
我见他不收,便劝道:我们拿工资的虽然钱不多,但比你目前的日子好过多了。这点钱帮不了什么忙,却能帮你填饱一顿肚子,你就不要推脱了。他见我完全出于一片真心,也就收下了,而且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几乎要流眼泪了。
中年男人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出了我的办公室,走下了楼梯,走人了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茫茫人海里,他多么不起眼。又有谁知道他是一个急需帮助的人,又有谁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正饥肠辘辘,在为全家生活发愁呢!
我用20元钱轻易地收获了许多感谢的话,但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没有急着下班,也没有再去整理案头的文件,而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内心一阵阵颤动。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是多么地朴实,多么地可爱。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把信赖、把期待、把梦幻都托付给了人民政府,在他们心中,只要有人民政府在,什么难关都可以渡过,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政府是他们不倒的精神支柱。他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那么善解人意,替别人着想,宁愿自己承受一切痛苦和厄运,哪怕是独自一人承受不了甚至濒临精神崩溃,也不怨天尤人,自叹自艾。而我们有些食着人民俸禄的公仆,豪车美食,投机钻营;麻木不仁,巧取豪夺;不讲奉献,只图索取;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这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那中年男子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时刻在警醒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上存在着困难,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你没有资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懈怠,你没有理由捞取自己份外的收入,你更没有权利站污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好好做人吧!好好工作吧!
捕鼠记
我家住在四楼。去年刚对房子进行过简单装修,敞开的阳台装上了铝合金窗框茶色玻璃防盗网,只要把门窗关严,蚊子也是难得飞进来的。
一天夜里,我在一片啃噬声中醒来。两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是什么声音?我躺在床上屏息静听。这声音就来自门后,格外刺耳。是什么动物在门后捣乱?我摸索着拧开床头灯,就在灯亮的刹那,我发现一只老鼠蹲在房门后,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望着我。我怒从心中起,可恶的老鼠搅了我的好觉。我顺手抓起一只拖鞋朝老鼠砸去,老鼠“嗖”的一声从半开的卧室门里跑进了客厅沙发下。
我懒得去理会老鼠,熄灯继续睡觉。没过多久,老鼠又啃咬起来,声音刺耳,令人悚然。我开灯,砸拖鞋,熄灯,再开灯,如是数次,好好的觉被一只小小的老鼠搅得不能睡踏实。
早晨,我正在酣睡,妻子把门拍得山响:快起来,老鼠已堵在客厅里,赶快抄家伙。显然妻子也受尽了老鼠折磨之苦,意欲除之而后快。我和女儿被叫起来,趿着鞋来到客厅,然后关好客厅通向其他房间的门窗。
妻子迅速作了分工,我和女儿站在不同方向把守,任务是老鼠跑到面前后不要命的捕打,妻子负责在沙发下翻寻追赶。我拿着拖把,女儿抄着苕帚,妻子则持一根细木棍,按照分工严守阵地。妻子见我们准备好了,便用细木棍在沙发下“噼噼啪啪”地搅动。藏在沙发下的老鼠便鼠头鼠脑地溜出来,向我女儿把守的房门边逃窜。女儿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不及用苕帚扑打,慌忙用双脚去踩,不仅没踩着,老鼠反而从她脚背上跳上了电视柜,再溜进沙发下,女儿吓得惊叫起来。
第一个回合没有捕住老鼠,我们便调整策略,由女儿在沙发下搅,逼老鼠逃出来,我和妻子各守一方,伺机捕杀。女儿在沙发下搅动了一阵,就是不见老鼠出来。我急了,跑拢来,把靠墙的沙发向客厅中央挪动,发现老鼠静静地蹲在沙发靠背的一根横档上。狡猾的家伙,它在以静制动呢!沙发一挪开,老鼠见藏不住身,便“嗖”地一声窜上窗台,在窗玻璃上碰壁后掉在地板上,等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老鼠又钻进了电视柜底部。
我们缩小了战斗面,满怀着对老鼠的痛恨,再次向老鼠发起了进攻。当老鼠从电视柜下探出头来,准备故伎重演的时候,我用脚狠劲踩住了它露出来的尾巴。就在老鼠掉头准备咬我的关键时刻,我用拖把压住了它的全身。妻子女儿拥上去,照着拖把踹了几脚,老鼠便没了声息。一只搅得我们一夜不得安定的老鼠,在我们全家合力围歼下,终于倒地毙命了。
事后,我认真查看了阳台上的窗户是否关紧,恰恰是妻子傍晚浇花后一扇窗留有小小一条缝隙,老鼠便趁隙而入了。
面对鼠尸,我不禁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句成语的缺陷。如果这只老鼠,我们一家三口只喊打而不动手,又怎么灭得了。对老鼠这类传播疫病,危害社会的动物,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人喊打”的份上,而且要人人都打,老鼠才无藏身之地。行笔至此,我不由得联想到政治经济生活中孽生的一种名叫腐败的老鼠,啃噬着社会主义大厦,其危害已远远超过自然界的老鼠。对于腐败,我们是深恶痛绝的,就象见到了过街老鼠一样,没有人不会不喊打。但现实的情况常常是喊打的人多,动手打的人少,以至于腐败这种老鼠招摇过市而不伤皮毛。这不得不令我们伤感,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房子再严丝合缝,也会有缝隙让老鼠溜进来,制度再健全完善,也会有空子可钻而滋生腐败。老鼠溜进来了并不可怕,关上门齐心协力捕杀就行了;腐败滋生了并不可怕,象捕杀老鼠一样下得手就可以了。问题的关键是:捕老鼠人人上阵,容易动员,因为老鼠就是老鼠,没有伪装,其危害人人明了,个个清楚,该捕该杀,绝不含糊,捕杀之后,对人对己都十分有利。就象进我家的老鼠被捕杀后,晚上全家就可睡上一个好觉。反腐败就会牵涉许多人,而腐败分子又善于伪装,往往喊反腐败的人,说不定自己就是腐败分子,就不会象看见老鼠那样一目了然了。因此,反起腐败来,也绝没有捕鼠那么容易,要费心费神得多,很多时候常常无功而返,弄得不好还要遭报复,落埋怨,其结果是好人受气,坏人逍遥。
不管怎样,人民群众对腐败是恨之入骨的,对反腐败的期望也是很高的,这是我们反腐败的坚实基础。作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绝不会容许如老鼠一般的腐败分子存在,对腐败会象捕鼠一样见而诛之。不希望产生腐败的人们,也要象捕鼠一样,不仅人人见了喊打,而且要人人动手打;不仅要人人动手打,而且要分工明确,严把关口,各守阵地,不把老鼠灭掉不罢休。老鼠灭掉后,还要把门窗关严,防止别的老鼠再溜进来。诚如是,老鼠何愁不灭?腐败何愁不除?
我差点害了父亲
一九七一年秋天,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由于我的好奇和无知,竟把父亲保管的一份重要文件悄悄带出去,害得父亲因此差点丢官坐牢。
那年国庆节才过,在村里(当时叫大队)任支书的父亲,参加乡里(当时称公社)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带回一份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文件上说的是林彪仓惶外逃、叛党叛国、机毁人亡的事。
父亲回来后,连夜召开村里的党员会议,学习这份文件。第二天,又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学习文件。林彪,这个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党叛国的千古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的大人们见面就议论着这件事。我当时混沌初开,听大人们说到“三叉戟”什么的根本不懂,也从没有见过飞机之类的航空器,心里还怪怪地想:这林彪也太自私了,临逃跑时还提着三只鸡,结果呢,三只鸡从天上掉下来把人也摔下来了。父亲等群众大会散了,便把文件带回家中。家里没有文件柜之类的物什,仅有的一口上着土漆的木箱,也因被老鼠咬了几个洞而弃之不用了。我无意中发现父亲把文件摊平,很仔细地放在他睡觉的枕头下,用双手使劲压了压枕头,然后出门做事去了。
凭着孩子的好奇,我想把林彪提着三只鸡逃跑摔死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吃过晚饭,我见父亲还没有回家,便溜进父亲的卧室,从枕头下取出那份文件翻看起来。文件中很多字我不认识,认得的字也似懂非懂。于是,我便想到已上五年级的表哥,这些字他可能认得。我把文件揣在怀中,径直去了表哥家。表哥一家正在吃晚饭,等表哥吃完饭,天已全黑了。我一手把文件递给表哥,一手端着煤油灯,说:“表哥,这文件里都写了些什么,你给我念念”。表哥对文件里的事并不感兴趣,随便翻翻,又还给我说:“就是讲的林彪跑了,从天上掉了下来摔死了,没多少意思。”我接过文件,猜想:可能是表哥对文件里的好些字也不认识而糊弄我。因为他的语文成绩并不好。我把文件依然揣进怀里,便随表哥表弟出门邀村里其他伙伴去捉迷藏。
我怕晚上捉迷藏不知不觉把文件弄丢了,便装着要撒尿的样子,跑到一户农家柴草堆旁,把文件塞了进去,想等回家时再取。
我们一群小伙伴疯玩到半夜深,直到上下眼皮打架了,才各自回家睡觉,我早把文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酣睡,父亲急急忙忙地把我摇醒,问我是不是拿过他那份文件。我看着父亲那愠怒的脸色,知道事情不好,但我不敢承认,便装糊涂地说:“什么文件,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信了我的话,不再追问,回到自己卧室仔仔细细又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父亲在翻找的过程中,一直铁青着脸,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粒。我悄悄溜出门,来到柴草堆旁,想把文件取出来。可是奇怪,明明清楚地记着放在什么位置,等我扒开柴草堆一看却傻了眼,里面不仅没有文件,连巴掌大块纸片也没有,我反复扒开柴草堆寻找,就是不见文件的踪影。
我悻悻而回,正碰着父亲黑着脸从大队部出来,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赶忙低头走开了。
中午,公社来了两位干部到我家,一位是公安特派员,一位是副社长,原来父亲已把文件丢失的事通过大队部的摇把子电话向公社作了报告,公社就派出他们来处理这件事。公社干部一坐下来就问父亲文件是什么时候丢失的,样子十分严肃。我见把事情惹大了,心里非常害怕,便藏在屋后的竹林里不敢露面。
后来,表哥告诉父亲,是我昨晚把文件带到他家看后不知放哪儿去了。父亲心里有了谱,寄希望我能说出藏文件的地方。父亲好一阵找,终于在屋后竹林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我。我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揍我一顿,可是他没有。他蹲下来,好言好语劝我,让我想想文件放在什么地方了。我盯了父亲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文件放在一个柴草堆旁,可是今早我去看却没有了。”父亲把我拉起来,自己蹲下来,背起我就走。父亲背着我来到昨晚藏文件的柴草堆,放下我,仔细地找起来。我看见父亲满头大汗,热气腾腾,他顾不了这些,只想赶快把文件找出来。父亲找了好久,几乎失望了,却在柴草堆尖上覆盖的一块杉木皮下发现了那份文件。父亲捧着失而复得的文件,好久没有动。我一直在想,明明藏在柴草堆底下的文件,怎么会跑到柴草堆尖上去。唯一的可能是,我因晚上光线太暗,藏得不好,第二天过路的人看见后,发现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怕人拿走丢失,便藏在柴草堆尖更隐蔽的地方。既不让外人知道,又便于藏文件的人多费些功夫就能找到。这真是一个有心的好心人。
当那份重要文件毫发无损地找回来后,两位公社干部原本严肃的脸孔也灿烂起来。副社长摸着我的头说:“小鬼,今后可不能随便把文件带出去了。这份文件如果找不回来,你老子不仅当不成书记,还有可能要坐牢呢!”丢失文件有那么严重的后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仅仅有这一次就足够我刻骨铭心了。
我小时候一次无意识的过错,竟差点害了我尊敬的父亲。
瞬间
那年夏天,我刚十八岁,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忽然一位村干部跑到学校捎来乡学区的口信:要我后天上午到县城参加民办教师录取师范学校的考试。
我所在的学校距乡政府有十八里山路,乡政府到县城有一百六十里,每天有一趟客班车往返。按照常规,一天时间我完全能赶到县城,不会耽误参加考试。
我把工作向一位老师匆匆作了交代,在学校财务室借了20元路费(当时我每月只有16元的补贴)。第二天一早,我怀揣着妈妈给的几个烤红薯上路了。乡村的山间小路,野花铺地,薄雾缭绕,鸟儿啁啾。露水沾湿了我的长裤和打着补丁的解放鞋。我急着赶路,无心欣赏这一切,也顾不了这一切。
到了乡政府,一打听,才知道前几天发山洪,距这儿约五十里路的一处公路被冲跨了,客班车已有几天没进山了。明天就要考试了,我急得想哭。旁边几位看我着急的样子,问明情况后,便帮我出主意:你今天走路赶到陈家河,那里有趟歇班车,清早进城,兴许能赶上考试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迈开双腿往陈家河赶。一路上,有许多跑短途运输的拖拉机,我想让他们捎带一段路,扬手拦了几次,竟无人理踩我。
傍晚,我终于拖着灌铅一样的双腿走进了陈家河。此刻,我又累又饿。但我顾不了这许多,忙着打听歇班车停放的地点。我看见歇班车静静地停在一个院子里。我去询问师傅:明天早晨什么时候开车?师傅说:“清早六点”。我一算时间,如果六点钟准时出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