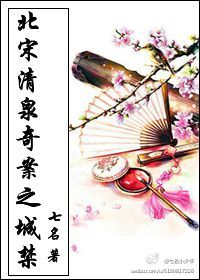清泉石上流 石绍河著-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光屁股上挨了重重一下,痛得“哎哟”一声掉下来。我一边爬一边骂,等看清站在我面前的竟是我父亲时,我张开的嘴半天合不拢。父亲怒气未消:“你把树烧死了,我剥你的皮!”说完,忙搬来稀泥把树洞堵得严严实实的。那一刻,我知道了寨人对古楠的感情,我懂得该怎样对待古楠了。
香楠不仅自己遭遇着种种磨难,也阅尽了人间的悲欢。
寨里的无数游子,就是在她的注目下,一步步走向山外。无论是发迹者,还是落魄者,只要回到云龙寨,她都一样敞开胸怀接纳,不偏不倚,不褒不贬,公正无私。香楠永远是默默的月下红娘,记不清多少有情人在她的荫庇下终成眷属,既成就了父亲也成就了儿子,既成就了母亲又成就了女儿。
但香楠也有无人知晓的痛楚。有一对苗哥哥苗妹妹,自小青梅竹马,俩小无猜。在他们知道男人需要女人,女人离不开男人的时候,俩人在楠树下海誓山盟,私订了终身。可苗妹妹的父母嫌弃苗哥哥家穷,高低不同意女儿的这桩婚事,还私下把苗妹妹许配给远房表哥的儿子。苗哥哥天天忧忧寡欢,形销骨立。苗妹妹整日以泪洗面,不思茶饭。还有十天,苗妹妹就要远嫁为人妻了。这是一个月光溶溶的晚上,苗哥哥苗妹妹下半夜相约来到私订终身的古楠下,相依相偎,默默无语。满月躲进了云层。夜莺停止了歌唱。夜露浸湿了衣裳。就这样,他们相拥着坐在古楠下,直到天亮。当朝晖洒遍他们全身的时候,寨里人发现这对痴情男女挂着幸福美满的笑容,美丽潇洒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楠树目睹了这一切,但无法挽回这一切。只有发出“沙沙”的乐音,为这对矢志不渝地男女演奏着招魂曲。
楠树是神树,寨里人这么说。有人告诉我,一九七六年春天,香楠没有象往年发新枝绽新芽,一幅无精打采的样子,好象人的气数将尽一般。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年,楠树老枝新芽,一派生机。寨里人方才醒悟,楠树的兴衰疏密,与国家的大事吻合着。后来,他们用心观察,果然又验证了几回。一次是一九八九年春天,另一次是一九九八年春天,楠树的新叶没有往年稠密茂盛,夏天真的就有了政治风波,有了罕见的洪水灾害。我虽然不相信这些,但寨中乡亲说得那么言之凿凿,我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反驳他们,就让他们永远保存着那份对楠树的崇拜吧!
一九九八年夏天,云龙寨突发山洪。竹溪两岸的农田、道路、房屋被狂泻而下的洪水吞没卷走。幸亏寨口有这两棵古楠树,保住了人户稠密处的河堤,洪水才没有决堤冲进寨子来,大多数乡亲免受痛失家园之苦。洪水退后,我回到了云龙寨,发现乡亲们对楠树的仰慕和崇拜更加深了一层。我独自一人在洪水留下的沙砾上徘徊,累了,坐在楠树突兀裸露的树根上,听风吹树叶发出的翠响,似乎读懂了楠树的心声:日月轮回,我俩终究有一天将老去,光把我俩当老祖宗保护可不行啊,要紧的是保护好我们的子孙,让他们都长成参天大树,洪水才不敢肆虐,家园才永远美好!我的心一颤:我亲爱的乡亲,洪水过后,你们都象我一样,听懂了古楠树发自内心的声音吗?举目四望,光山上有了许多绿意,我相信乡亲们的悟性。
我到县城工作后,到过不少地方,但还没有看见象云龙寨这么大的香楠,也许是自己孤陋寡闻。去查林业部门的古树保护名录,居然没有这两棵古香楠,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但转念一想,上不上名录,有不有名份,那些都是次要的,只要寨中人心里向着她们,爱护呵护她们,让她们得以延年益寿,不就足够了。
我心于是释然。
摆小摊的婆娘们
两条鸡肠子似的小溪,从大山褶皱里牵出,走到一处叫独木桥的地方汇合,然后顺山脚甩下一个大弯,河湾里有坝有田有寨子。寨中央过去是一座祠堂,好多年前已改成小学校。学校的两侧顺溪岸是一溜高矮不齐但一色青瓦作顶的吊脚楼,吊脚楼前散乱地铺着青石板,自然形成一条小街,蚯蚓般延伸,极不规则。
学校的大门依然是古槽门,厚重的木门每天咿咿呀呀地响上无数次。出得大门,是与围墙脚平齐的河堤,河堤宽约三四米,既挡洪水,也作道路。河堤外边是一行垂柳,春天,柳絮翻飞,常迷入眼。夏天,绿荫匝地,树下常散乱地堆放着几条汉子。不知名的小鸟也在枝叶间上窜下跳,吵闹个不休,把一坨坨鸟屎朝地下乱扔。
山里居住分散,伢崽上学一天只吃两餐饭。夏日苦长,伢崽好蹦跳,刚下午学,有的就肚子咕咕叫,便满山去寻野果子吃。少数有钱的几个伢崽,常跑到寨子里唯一的小商店买上几块硬硬的饼干或一块有霉点的发饼,满嘴粉末地“喳喳”嚼得有滋有味。
寡居多年的张大婆,看到伢崽满山寻野果子吃,心里便有了一个小小的主意。一天,她给栏里的猪添了食,笼中的鸡撒了包谷后,把自家屋前屋后已熟的毛桃子,摘了一背篓,背到学校古槽门前的柳树下来卖。刚放下来,一泡鸟屎落在一颗硕大的毛桃子上,张大婆懒得拿到溪里去洗,顺手抓几根枯草擦擦,又用不很干净的袖口揩揩,仍旧放回背篓里。下午学的伢崽一走出校门,看到鲜嫩的毛桃,呼拉一下围上来。张大婆忙招呼:“一角钱三个,快来买呀!”伢崽看的多,掏钱的少。这天,张大婆只卖得一块多钱。
第二天早晨,好多伢崽缠着大人要钱,说是作业本写完了半截铅笔弄丢了一块橡皮被偷了,理由充足得很。兜里揣着钱的伢崽,一心只盼下午学。这天,张大婆的大半背篓毛桃转眼就卖完了,而且在忙的时候,几个鬼精的伢崽还乘机把毛桃拿走了好多颗,张大婆却浑然不觉。
从此,张大婆天天出现在学校的古槽门前,卖的品种也多起来。有山里摘下来的毛桃酸李子木瓜子枇把狗屎柑,有从山外进来的苹果鸭梨蜜桔甜橙。
这几年,打工潮也汹涌着这个小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发疯似的天南海北跑,好多人真的寄回不少钱。上学的伢崽每天兜里都揣有几毛块把钱,张大婆的小本生意更红火了。
看到张大婆天天赚钱,把孙崽送进学堂后闲着无事的向二婶,也在张大婆的旁边支起一孔铁皮油桶改成的小灶,架起一口小铁锅,倒上一瓶茶油或菜油,把大米磨成的浆和上萝卜丁葱花之类后放在油锅里炸灯窝盏,一天能卖完好几斤米。起初,张大婆也乐得有人作伴,无事的时候,便帮向二婶劈柴生火。向二婶也时不时递上一个炸熟的灯窝盏要张大婆尝尝。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张大婆也常抓几个梨桔之类的让向二婶试试。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既不寂寞,又赚了钱。
不久,玉香姐也炸起了灯窝盏,冬秀嫂摆起了水果摊。一个挨一个,好长一溜,粗粗一数,已有七八处,古槽门前好不热闹。虽然小摊增多了,品种花色增多了,但伢崽没增多,伢崽兜里的钱没增多。伢崽买了水果就没钱买灯窝盏,买了灯窝盏就没钱买米糖。于是,炸灯窝盏的与炸灯窝盏的之间,卖水果的与卖水果的之间,炸灯窝盏的与卖水果的之间暗暗较着劲,无形中就成了竞争对手。为了赚伢崽的几个钱,她们之间便有了龌龊,有了攻讦。
尽管生意不兴旺,但婆娘们都顽强地坚守着阵地,不少人企盼着他人遭遇不幸或生意蚀本而败下阵来。因此,张大婆为一个伢崽先准备买水果,后来被向二婶一哄二吓拉去买她的灯窝盏,和向二婶放肆吵了一架,祖宗几辈子的丑事都被她们当众翻了出来。玉香姐与向二婶为灯窝盏的价格干上了仗,冬秀嫂与张大婆争摆摊的地方接了手。真是三个婆娘一台戏。
吵归吵,闹归闹。闲着无生意可做的时候,她们耐不住寂寞,常常三三两两扎堆摆龙门阵,张家长李家短的评头品足,互相传播着是非,似乎忘记了她们之间曾经吵过闹过红脸过。一天,向二婶没有来摆摊,说是到小镇邮局去取小女儿桂桂打工汇来的钱。其他人在摆摊闲扯的时候,七扯八扯扯到了桂桂身上。张大婆说:“不晓得桂桂打工做么得(什么)?几个月寄一次钱,钱还不少嘞。”玉香姐听了后,抿嘴一笑,说:“你不晓得?卖淫呗。”张大婆不晓得卖淫是什么,疑疑惑惑地问:“她哪来那么多银子呀?”玉香姐忍俊不禁,捧着嘴巴把头扭向一边。冬秀嫂接过话头:“蠢卵,卖淫就是卖那个。”说着往张大婆裤裆里指了两指。张大婆如梦初醒,哈哈嗔道:“砍脑壳的!砍脑壳的!”
下午,向二婶从小镇上回来,张大婆说:“桂桂那么找钱,你还炸灯窝盏搞么得。”样子怪怪的。向二婶不知就里,以为又是张大婆嫌她抢了生意,故意这么说的,没有理睬就走了。
张大婆到城里去进水果。向二婶见她没来,抛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张大婆和土改是老相好呢。见众人不信的样子,向二婶又说:有天晚上,有人从张大婆屋后过身,只听得床板子吱吱嘎嘎响个不停,忙跑去听壁脚,听了半天,才听到张大婆说:“你下来”。土改气喘吁吁地说:“还没出水呢”。张大婆“扑哧”一笑:“你老得象个虾公,只怕出不来水哒。”向二婶边说边夸张地做动作。
众人捧腹大笑起来。
后来,那些婆娘们有意无意地经常当着张大婆的面,说些“出水”、“不出水”之类的话。不知是谁给张大婆提了醒。张大婆怒从心中起,把向二婶的摊子掀了个底朝天,向二婶也不是省油的灯,反过来把张大婆的水果摔得满地乱滚。
莲香的米糖卖完后,想邀个伴去进货,但都才进货回来,只好独自一人去。刚下车,遇上一伙卖猪药的骗子,胡吹海侃,说猪药了得。莲香糊里糊涂地把进米糖的五百元钱买了猪药,回到家才知道上了天当,气得几天没起床。冬秀嫂不知怎么打听到这个消息,忙告诉摆摊的张大婆向二婶们:莲香那个蠢卵,到城里进货,被一伙卖猪药的搞了,还倒贴上五百块钱。她们并不关心莲香是不是被人搞了,只是见莲香摆摊的本钱都玩掉了,幸灾乐祸了好几天。
日子就在她们的龌龊攻讦中东升西斜着。
玉香姐的丈夫岩头从外地打工回来,不知听谁说玉香姐在家里有相好。岩头不问青红皂白,揪住玉香姐就打,逼着她承认相好是哪个。玉香姐死不承认,最后被岩头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几天没起床。摆摊的张大婆向二婶们,听说后气得要命,一副义愤填膺地样子:“这不是给我们摆摊的抹黑么!”这天生意都不做了,七八个婆娘一齐寻上岩头的门来,把岩头堵在屋里,扯的扯耳朵,揪的揪头发,向二婶还来了个“栏里捉猪”,捏着岩头的“小老二(生殖器)”。张大婆双手叉腰,面对着岩头质问:玉香哪点对你不起?又是牛又是猪,又是山里又是屋里,还要做生意,成天累得象只狗,还有心思找相好。只怕你自己长癫子怪别人,玉香天天跟我们一起做小生意,我们都替她讲得索利话。你把她打得这个样子,你讲啷门搞?”岩头一看这架势,好汉不吃眼前亏,忙低头认错:“我错怪了玉香,今后再也不打她了”。
张大婆向二婶们这才放手,气昂昂地去摆小摊。
夏天的一个夜晚,大雨倾盆,山洪突发。冬秀嫂家临溪而建的吊脚楼,被洪水连根拔掉了。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冬秀嫂欲哭无泪,几近绝望。这时,玉香姐腾出一间屋子,把冬秀嫂一家安顿下来了,张大婆送来了被子和腊肉,向二婶背来了大米和衣物。
那天,张大婆收摊晚了些。也许是人老眼花,在回家的路上,不幸摔了一跤,左大腿骨折。她寡居多年,一个女儿远嫁四川,身边无人侍候。向二婶们便轮流给她换药送饭,过去的前嫌旧隙一下了抹平了,好象原本她们就是一家人。
张大婆伤好后,身子十分虚弱,从此再也没有摆摊了,但只要有空,也会到古槽门前坐上一阵子。
摆小摊的队伍,不断有婆娘们退出,不断有婆娘们加入。不断看到她们为蝇头小利吵架干仗的情景,不断听到她们为同行姐妹打抱不平,互相关照的传闻。
这是些可恼可恨可敬可亲的婆娘们。
黑狗
乡下人都喜欢喂狗。为了看家守屋,图个毛孩子拉屎撒饭方便。
我很早便想喂一条狗。左察右访,先后从亲戚家弄得几条小狗,不知是饲养不当,抑或与我无缘,喂不上几天,都夭折了,我也有些灰心,那念头便也不怎么强烈。
去年暑假的某一天清晨,我还没有起床,隐隐听得一阵抓门声。我拉开门,不由得一惊,门槛上蹲着一只半大、不很壮实的黑狗,毛湿漉漉的,眼睛里仿佛噙着泪花。
黑狗瘸着腿走进屋,蹲在火塘边,定定地瞅着我,乞求似的眼神里,闪烁着信任的柔光。我想不出这是谁家的狗一一从来没看见过,但我可以猜出,它一定受了什么委屈。我将剩饭倒了一些与它吃,吃完之后,它便在我小女儿的木摇窝下蜷伏着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连几天,它都没有要走的意思。妻子说:“狗不嫌家贫,它投到我们门下,我们就把它喂起来,这比侍侯小狗强多了”。母亲来得更实际:“猪来穷,狗来富,活该是我们的财喜,好生喂着吧”。我虽然不相信“来穷”、“来富”
之类的话,却还是有心把它喂起来。
这是条聪明的狗,非常招人喜爱,没几天,它就和我们混熟了。家里不管哪个人外出归来,它都老远地摇着小尾巴,蹦蹦跳跳地奔过来,亲昵地用头撞你的脚,在你身边打滚,还不时直起身子用两条后腿走路,惹人发笑。我们全家也特别喜欢它,总要喂它一些好饭菜。我那蹒跚学步的小女儿,经常扶着黑狗的身子,从地下站起来,慢慢挪动脚,黑狗很通人性,也用同样的速度往前走,小女儿不致有跌倒的危险。
暑假过去了,我要到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