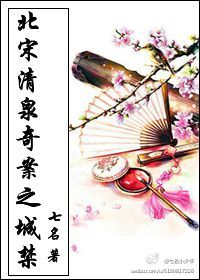清泉石上流 石绍河著-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知道大哥干事的认真劲,寨里人给我讲的这些丝毫没有夸张。
大哥告诉我,他计划再通过几年的努力,开发到100亩,自家的地不够,就准备把与果园连成片的几户人家发动起来,他出技术和种苗,受益后按比例分成,走规模化、优质化、多样化的路子。承包的责任田解决吃饭问题,店子和果园解决用钱问题。到时候,不会比在城里上班差到哪里去。他还信心十足地说:“你如果哪天下岗了,就回来和我一起搞,你的文化比我高,一定能干出名堂。”
和五年前的大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有了新的事业,我痛悔的心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衷心地祝愿大哥早日成功。
大哥还算不得富裕人家,但他心里正灿烂着漫山梨花。
燕儿呢喃
突然,我的头上传来一阵“唧唧”的声音。
抬头一望,哟!不知什么时候,一对南归的燕子在我斗室的门楣上筑了一个新巢。
从此,我结识了一对新伙伴,有了一双新邻居。
我生性孤僻,却独爱上了这有灵性的动物。伏案久了,我便揉揉昏花的眼睛,搬一把小木椅,坐在阶沿上,翘着二郎腿,极有兴致地着它们衔泥、筑巢,有时竟呆呆地看上一个多小时乐此不倦。燕子呢,仿佛也乐意我欣赏它们的劳动,不时回过头来瞅上我几眼,那目光是柔和警良的。有时还亲昵地叫上几声,是向我问好抑或是跟我谈心,那声音委婉动听。谁说人和动物没有共通的东西,我和燕子不是相处得也很默契么?
一次,我忽然觉得,应该为燕子做点什么。我便特意弄来硬纸片和竹片,找来梯子,钉在门楣上它们的巢下,以尽地主之谊。它们呢,似乎理解我的美意,随时都给我唱上几句“唧唧”歌。
别小看这一对燕子,它们筑巢的速度是很惊人的,一个漂亮的巢只要十来天便可落成,这对它们来说,需要耗费多少精力,付出几多辛劳。我发现,不管刮风下雨,无论赤日炎炎,它们天天都在忙碌着,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决心,停止自己的劳作。天亮而作,天黑而息。实在太累了,它们也只在电线上或晾衣绳上小憩一会儿,梳理梳理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的羽毛,然后又是来去匆匆。当我惰性滋长的时候,那委婉的“唧唧”声,那轻捷的剪影,响在我的耳边,掠过我的眼前,提醒着我,警策着我,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打开尘封的书,拿起搁下的笔
多少个夜晚,“唧唧”声是我的催眠曲;
多少个凌晨,“唧唧”声是我的起床号。
一对小小的燕子,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然而,谁料得到,一场无辜的灾难却降临到它们的头上。
那是六月的一天,我出门家访,傍晚时分才回到学校。当我走近我的斗室时,看见地上散着许多泥土、粪块、羽毛、青苔、硬纸片,还有几个打碎的蛋,一群绿头苍蝇叮在上面,见我走近,“轰”的一声飞开了。看着这狼藉的景象,我心里一颤,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仰头一望,果然,那对燕子苦心经营的巢,现在只粘着一些残泥。几根白色的羽毛,被蛛丝网住在那里摆动。我扭过头来,看见那对燕子正木然地站在电线上,呆呆地望着过去温暖的家,全然没了往日那种活泼劲。没多久,双双便斜刺里消失在薄暮中。我心头一沉:长夜中,哪儿是它们的栖身处?
给它们带来灾难的竟是一群顽皮的孩子。
我默默无言。
晚上,下起了雨,我躺在床上,耳边消失了那种“唧唧”的委婉的催眠曲,只有雨水的滴嗒声,单调而枯燥,心里有一种失落感,惆怅得很。我失眠了,老是惦记着这对小生灵,在这风狂雨猛的夜晚,它们是那么弱小,黑暗会将它们吞噬吗?我默默祈祷:但愿它们平安无事。
不知过了好久,我朦朦胧胧睡去了。可老是做梦,全是关于燕子的。唉!这一对让人牵肠挂肚的小东西,为何命运这般多舛呢?
醒来的时候,已是霞光万道。忽然,门外传来几声“唧唧”声,极委婉,极柔和。拉开门,是一对熟悉的身影。
我一夜都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
云龙寨人物五题
岩妹
来到了这个南方滨海城市,住所面对着一片海滩,沙白水清浪柔。
傍晚,房间里燥热闷人,我独自一人,迎着带腥味的海风,向海滩走去。血红的夕阳,一半悬在天际,一半浸在海里,归航的渔船,披一身金辉,缓缓向岸边驶来,海滩上人头攒动,奔波劳累一天的人们,此刻都在怡然地接受着海风的轻抚和海浪的轻吻。我避开众人,站在一棵高大的椰树下,面对着波澜壮阔的大海,看奔腾欢卷的浪花,听海潮击岸的涛声,借以隐去心中的烦燥和不安。
就在我痴迷大海之际,身后传来一声轻柔的叫唤:“石老师!,,在这遥远的滨海城市,谁会认识我?该不是错觉吧?我转过身,只见一位高挑少女,微笑着向我款款走来,海风高高撩起她的披肩长发,白色长裙像一面旗帜在飘。我警惕着向我走来的少女。大概是发现了我的紧张神色,少女在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操一口乡音问我:
“石老师,您不认得我么?”
她是谁?我在脑海里快速过着镜头,但跳不出她的形象,只好摇摇头。
“我叫岩妹,六年前,您给我上过语文课,您的课生动风趣,大家都喜欢听。”
经她这么一说,我的脑海浮现出那个叫岩妹的学生,扎着羊角刷,一幅腼腆的样子。她因父母身体不好,隔三岔五地丢课,升中专时差五分落榜,一双眼睛哭得像两个水蜜桃。毕业后,我就不知道她的消息了。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打工呗。”她轻轻地说,“我初中毕业后,先是在家里帮助父母种地,使牛打耙,轻活重活样样都干,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年成好,全家勉强能吃饱肚子,年成不好,肚子都填不饱。我看这样起早贪黑不是日子,便悄悄邀寨子里的几个姐妹,趁寨里人深夜睡着了,赶几十里山路搭班车进城打工,当保姆呀,当服务员呀。后来受姐妹怂恿到特区,我们又来到深圳、珠海,先在私人工厂里干,因厂里不景气,两个月前又来到这个城市。”
“你一个女孩子出来做事,容易么?”
岩妹轻轻吁了一口气:“当初,我们以为沿海城市遍地黄金,钱很容易挣,出来以后,才知道挣钱很不容易,全靠自己闯天下,有时好长时间找不到事做,像一个流浪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岩妹读到我紧张关切的神情,很感动,她朝我笑笑,“不过,打工也挺磨炼人的,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靠自己想办法。”
我掐指一算,岩妹不过二十出头。二十岁,家乡的贫困促使她成熟,孤栖异乡又让我暗暗担忧。
岩妹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换了话题:“石老师,我在这儿遇上您真高兴,您一出现在海滩上,我就认出来了,就是不敢叫,一直悄悄跟着您。这儿海滩很美,我陪您走走吧。”于是,我们并肩向无人的沙滩走去,沙滩上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你在这儿做些什么?”我忍不住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什么都做,唱歌啦,跳舞啦,游泳啦,只要能挣钱。我现在最缺的是钱。”她说得坦率而坦然。
“打工就做这些?”我有些愕然。
岩妹见我不解,歪着头,两眼火辣辣地盯着我,反问道:“这些不好么?”在我的意念中,这些事至少不是我的学生能做的。但岩妹不会骗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低着头,默默向前走。
岩妹见我低头不语,有些伤感,幽幽地说:“连老师都不理解我,难怪家乡人说我们女孩在外打工,钱来得不明不白!”
我抬起头,看见她眼里有泪花闪耀,忙掏出一叠餐巾纸递过去,她很随意地擦了擦。待情绪平缓后,恳切地说:
“老师,您出来一趟不容易,应该好好看看,这儿有很多内地人暂时不习惯或看不惯的东西,我们那儿太闭塞了。其实,唱歌、跳舞、游泳,在这里已成为一种职业,这也是社会需要,不应该把这些当怪物看。”
岩妹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也许,我骨子里传统的东西太多了。
一时间,我们都陷了入沉思,只听见脚踩在海滩上的“沙沙”声。
为了打破沉闷,我关切地问:“跳舞、游泳经常会遇到一些难缠的事吗?”
岩妹紧走几步,侧身面对着大海,说:“这海水看起来清亮清亮的,其实里面有好多泥沙,人的世界就跟这海水一样。不过,老师您放心,我从事的工作接触的人多,哪个是不是花花肠子,一看就知道,我有办法保护自己,我会自尊自重的。”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早日结束这漂泊的生活。我现在最大愿望是多挣钱,干个一两年,带一笔钱回去,把通往寨子里的路修好,然后建一个开发基地或办一个厂子,把寨子里好多人都带富起来。”
我被她的这种设想鼓舞着,由衷地说:“岩妹,好好干吧。你的这些想法很美很好。”
夕阳已完全沉入海中,岸边的灯火次第亮起来,岩妹看看表,略带歉意地说:“石老师,舞厅快开门了,我要上班去了,对不起!”
“没关系,你去吧!”
岩妹转过身,朝来路走去,我目送她融入五彩灯光里辣椒嫂
“屙痢屙血的,剁脑壳的,砍千刀的,吃上路食的”我小时候,常看到寨子里一位中年妇女,一面指手划脚,一面骂朝天娘。她便是云龙寨有名的辣椒嫂。
辣椒嫂骂人出了名,人们便送她这绰号。
这也难怪她,35岁那年,丈夫撇下她和三个孩子撒手去了。吃大锅饭的年头,孤儿寡母容易熬么?偏偏又有那么些人不识相,不是放猪拱了她园里的菜,便是几棵指望换点油盐钱的果树,果子还没掉灰,一夜之间只留下几根光光的枝丫。辣椒嫂悄悄流了好多泪。
越是忍,越是让,别人越得味。辣椒嫂心一横---骂!
说时容易做时难,这个老怕得罪人的寡妇,要真骂人还难开口呢!头两回,她站在自家屋檐下,骂人像讲悄悄话,声音怯怯的,调儿低低的。
你骂你的,他行他的,隔三岔五,辣椒嫂家还是丢东掉西。她没办法,咬着牙放着胆子去骂娘。如是几次,方明白只要撕破脸皮,她还是极会骂娘的,骂来骂去,竟能一次骂三个钟头娘不翻重。因此,寨子里有一句话:不怕辣椒嫂横眉竖眼,就怕辣椒嫂张嘴骂娘。
辣椒嫂这着真灵,从此谁也不敢沾惹她。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今年三月,父亲六十大寿,我特地从老远地方转回云龙寨。刚进寨子,就远远看见一栋吊脚楼前围着一堆人。一问,才知道是麻狗哥和顺佬哥为地界扯皮。人圈中,传出一个琅琅女声:“麻狗、顺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你们还扯哪门子皮,乡里乡亲的,闭眼不见睁眼见,为了几尺宽的地界也值得伤了从小长大的和气?麻狗,你那条条地干脆让给顺佬,他的成块好照拂,我家野猪弯有块地,你种上。”
我踮脚循声望去,认出说话的竟是多年不见的辣椒嫂!
麻狗哥和顺佬哥互望了一眼,点点头,算是表了态。
回到家,我跟妈讲起这件事。她“啧啧”连声:“田土分到户后,寨子里再也听不到辣椒嫂骂娘的声音了。有时碰到寨里人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扯皮,她反倒出来劝架。有人问她,那时节下狠心骂人为哪样?她说:‘那时是穷得心躁,如今哪个还要我那几棵烂菜,我也没功夫半天半天去骂娘了。’前年她选上了村上的妇女主任,去年又被大伙推举为民事调解员,她那张嘴,骂娘时硬是操出来了,讲道理也是一套一套不翻重,三讲两讲,人家心里就亮堂了。”
寨子里的人还是喊她辣椒嫂,那称呼里没了讥讽,添了敬重。
龙哥
龙哥当了四年消防兵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云龙寨。寨里人发现他和出去的时候稍有不同的是额上多了一条两寸来长的褐色伤疤,他说那是在一场灭火战斗中,掉下的砖块砸的。看着寨子里先后出去当兵的吴二狗学会了开汽车,李三佬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有些势利小人便很瞧不起龙哥,说当消防兵那算当啥兵呢?龙哥听了这些话,只当没听见。
一天晚上,北风呼呼地刮,像鬼叫似的。龙哥帮舅舅家去砌房子,很晚才回来,洗完脚倒头便睡。后半夜,龙哥迷迷糊糊听得外面一片叫嚷哭闹声,他一个鲤鱼打挺竖起来,从窗户里往外一看,只见寨东头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龙哥拔腿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出事地点,原来是独门独户的张木匠家因薰腊肉而引起的大火。大火已烧了快一个时辰,此刻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干燥的杉木和松木哗哗剥剥地燃烧着,人站在二十多米外还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浪。张木匠夫妇呆在一旁嚎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龙哥急得捶胸顿足。
这时,忽然听到火中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声,张木匠夫妇才想起自己六岁的儿子还躺在床上,便疯了般从地上爬起来往屋里冲,幸亏几位年轻人眼疾手快死死拽住他俩。听着张木匠夫妇“儿呀!”“宝呀!”的呼唤,龙哥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提起来,兜头泼在自己身上,扔下桶朝浓烟滚滚的门口冲去。他一脚踢开了紧闭的大门,朝发出孩子哭声的地方寻去,浓烟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双眼直流泪,什么也看不见。他摸呀摸呀,好不容易在床下摸着了打滚哭叫的孩子。当他抱着孩子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蓦然“咔嚓”一声,屋上的檩条烧断了,椽皮、瓦片铺天盖地向他砸来,他忙趴在孩子的身上,一阵“乒乒乓乓”响过之后,他感觉到一股液体从头上直流到嘴里,热热的,咸咸的。他却顾不了去摸一下脸,抱起孩子就往外冲,从火海中钻出来了,但他脸上糊满了血,头发烧得焦糊,冒着一股股难闻的青烟,身上的衣裤有几处还在燃烧。就在龙哥钻出来不到一分钟的光景,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