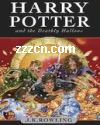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研究的逻辑》第77节中)。我非常重视这个错误;那时我不知道甚至爱因斯坦也犯了一些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认为我的过失证明了我的无能。我听说爱因斯坦的错误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科学哲学大会”以后。根据理论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科夫的提议,我受到了尼尔斯·玻尔的邀请,在他的研究所里逗留了几天进行讨论:先前我已为我用来反对冯·魏茨泽克和海森堡以及反对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作了辩护,前两人的论据并不使我十分信服,但后者的论据确实使我信服,我也和梯尔林以及(在牛津)和薛定谔讨论了这个问题,薛定谔告诉我,他为量子力学而怏怏不乐,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因此当玻尔告诉我关于他与爱因斯坦的讨论——他后来在施尔普的《爱因斯坦》卷中描述了那些讨论——时我是处于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我并没有想到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安慰:即根据玻尔的说法,爱因斯坦和我一样犯了错误;我感到我失败了,并且我不能抵制玻尔个性的巨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玻尔无论如何是不可抗拒的。)我多少还是屈服了,尽管我仍然为我对“波包收缩”的解释作辩护。韦斯科夫似乎乐于接受它,而玻尔却过于渴望阐述他的互补性理论,以致不能对我为宣传我的解释所作的微薄努力给予任何注意,而我也没有坚持这一点,因为我满足于学习,而不是讲授。当我离别玻尔时,他那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积极热情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也几乎觉得无疑他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能自信我理解了玻尔的“互补性”理论,并且开始怀疑是否有别的什么人也能理解它。虽然有些人显然已被说服,认为他们是理解了。正如爱因斯坦后来告诉我的,还有薛定谔也有这种怀疑。
这使我去思考“理解”问题。玻尔以某种方式断言,量子力学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古典物理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不得不顺从这一事实:量子力学只能部分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古典物理学的中介去理解它。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通过古典的“粒子图像”达到的,大部分是通过古典的“波图像”达到的;这两种图像是不相容的,它们就是玻尔称为“互补性的”。没有希望去更充分地或更直接地理解这个理论,要求的却是放弃要达到一种更充分理解的任何试图。
我猜想玻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理解持十分狭隘的观点之上。看起来玻尔想到的是用图像和模型理解——用某种形象化理解。我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了,我终于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即要紧的不是对图像的理解,而是对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的理解,就是说它的说明力,它对有关问题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多年来,我在讲演中发展了这种观点,我想第一次是在阿尔巴赫(1948年)和普林斯顿(1950年),在剑桥一次关于量子力学的讲演中(1953年或1954年),在明尼阿波利斯(1962年),后来又在普林斯顿(1963年)以及其他地方(当然也在伦敦)。这个观点可在我新近的一些论文中找到,虽然只是一个梗概。
关于量子物理学,数年来我一直是不抱信心的。我不能忘却我的错误的思想实验,并且,虽然我认为为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感到痛心是对的,但现在我认为我过分重视这个错误了。只是在1948或1949年,与一位量子物理学家阿瑟·马尔赫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我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引用了他的《论量子力学基础》一书的观点),我似乎才重新鼓起勇气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又深入研究了原有的论据,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A)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问题
(1)不存在任何反对决定论的特殊的量子力学论据。当然,量子力学是一种统计学理论,而不是一种乍一看就是决定论的理论,但这并不意昧着它与一种乍一看就是决定论的理论不相容。(尤其是冯·诺依曼对这种所谓的不相容性——所谓“隐变量”的不存在——的著名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戴维·玻姆以及前不久由约翰·S·贝尔以更直接的方式表明的一样。)。我在1934年达到的立场是:量子力学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论点:决定论被反驳了,因为它与量子力学不相容。从此以后,我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想法。
1951年,戴维·玻姆提出的一个模型表明:乍一看是决定论的理论的存在,确实在形式上是与量子力学的结果相容的。(构成这个证明基础的基本思想是由德布罗意先提出的。)
(2)在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可靠的理论断言决定论在物理学中有基础;实际上存在着反对这种断言的强有力的理由,正如C·S·皮尔斯,弗朗茨·埃克斯纳、薛定谔以及冯·诺依曼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理由都引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牛顿力学的决定论性质与非决定论是相容的。此外,虽然把乍一看是决定论的理论的存在解释为以非决定论的和概率的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理论是可能的,但反之却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于概率的前提才能推导出有价值的概率结论来(并因而得到解释)。(在这方面,朗代的一些十分有趣的论据应该予以考虑。)
(B)概率
在量子力学中,我们需要诠释概率计算。
(1)概率计算是物理的和客观的(或“实在论的”);
(2)概率计算得出的概率假说能接受统计学的检验。此外,
(3)这些假说可应用于单个事例;以及
(4)它们与实验设计有关。
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我发展了概率计算的“形式主义”诠释,它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从那时起我已对这种诠释作了改进,用“趋向性解释”来代替了它。
(C)量子论
(1)实在论。虽然我不反对有关“波粒子”(波与粒子)或者类似的非经典的实体的原理,但我没有看到(现在仍未看到)有任何理由去偏离经典的、朴素的和实在论的观点,即电子等等就是粒子,即它们是定位的,并且具有动量。(当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表明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是正确的。)
(2)海森堡的所谓“测不准原理”是对断言统计学散射的某些公式的一种曲解。
(3)海森堡的公式没有涉及测量;他的公式暗示目前流行的全部“测量量子论”都充满了曲解。根据海森堡公式的通常诠释被“禁止”的测量,按照我的结果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实际上还要求对这些公式本身进行检验。然而,这种散射关系又与量子力学系统状态的准备有关。在准备某种状态时,我们总是要引入一种(共轭的)散射。
(4)对量子论来说确实独特的是概率的(依赖时相的)干扰。可以设想我们也许不得不把这一点当作某种最终的东西来加以接受。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早在波动力学产生之前,当人们在反对康普顿对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判决性检验时,杜安就于1923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量子定律,这个定律可被看作是类似普朗克能量定律的动量定律。杜安的动量量子化定律不仅可以应用于光子,而且(正如朗代所强调的)也可应用于粒子,因而它也对粒子的干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虽然只是定性的)解释。朗代进一步论证波动力学的定量干扰定律,可以从简单的补充假定中推导出来。
(5)因此,许多哲学幽灵现在可驱除了,并且关于主体或精神侵入原子世界的所有那些使人惊愕的哲学断言现在也可以消除了。这种侵入主要可以解释是由于人们对概率计算的传统的主观主义曲解所致。
无尽的探索19.客观性和物理学
19.客观性和物理学
在前一节中我强调了《研究的逻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来工作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与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我对量子论的观点上甚至也起了一种辅助的作用。我认为,我摈弃爱因斯坦的实证主义使我避免受到海森堡早期实证主义的影响。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第6节,注[31]和[32]间的正文),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既没有强调也没有批判观测的观点,而是帮助我理解狭义相对论问题(我以通常非历史的方式担心,这是迈克尔孙和莫雷的实验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与我讨论了闵科夫斯基的解决方式。可能正是这种指引才使我始终没有认真对待同时性的操作主义观点:一个实在论者阅读爱因斯坦1905年的论文时,可能根本不注意“观察者”;反之,一个实证主义者或操作主义者阅读这篇论文,可能始终注意这个“观察者”及其所作所为。
有趣的事实是,爱因斯坦本人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他后来摈弃了这种诠释:他在1950年告诉我,他犯过的任何错误都没有像这个错误这样使他感到懊悔。这种错误以真正严肃的形式表现在他的普及读物《相对论:狭义和广义理论》一书中。在那本书的第22页上(德文本第14页以后)他写道:“我要求读者在他完全确信这一点前,别再刨根问底了。”简言之,这一点就是必须给“同时性”下定义——并且用一种操作的方法下定义——因为否则“我允许我自己被决定……当我想象到我能够把某种意义赋予同时性的陈述时,我就是允许自己受骗”。或者换言之,一个术语必须用操作方法下定义,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一句话,这就是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影响下,并以非常教条的形式,被维也纳学派后来发展了的实证主义。)
但是在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境况不过是,对于任何惯性系统(或“静止系统”)来说,事件是同时的还是不是同时的,就如它们在牛顿理论中一样;并且以下的跃迁定律(Tr)也适用:(Tr)在任何惯性系统中,如果事件a与b是同时的,b与c是同时的,那么a与c也是同时的。
但是,一般说来(Tr)不适用于任何三个间隔遥远的事件,除非a和b在其中是同时的这个系统,与b和c在其中是同时的这个系统是一回事:它不适用于发生在不同系统中的间隔遥远的事件,即发生在作相对运动系统中的间隔遥远的事件。对作相对运动的任何两个(惯性)系统来说,这是光速不变原理的一个推断,即允许我们推演出洛伦兹变换的原理的一个推断。这里我们甚至不需要提及同时性,除非为了警告我们不要忽略洛伦兹变换与(Tr)之应用于发生在不同(惯性)系统中的事件的时限是不相容的。
可以看到,在这里没有必要引入操作主义,更谈不上去坚持它了。此外,由于爱因斯坦在1905年——至少在他写作他的相对论论文时——不知道迈克尔孙实验,因此他手头只有不充分的光速不变的证据。
但是,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都受到爱因斯坦操作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操作主义是相对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爱因斯坦本人在长时间内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操作主义碰巧又是海森堡1925年的论文以及他的被广泛接受的论点(电子轨迹的概念或者它的经典的位置加动量的概念是无意义的)的灵感。
对我来说,这倒是推动我通过把我的实在论认识论应用于批判海森堡对量子力学形式主义的主观主义诠释来检验这种认识论。我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对玻尔谈得很少,因为他比海森堡更不明确,并且因为我不愿意把他可能并不持有的观点强加于他。无论如何,是海森堡把新量子力学奠定在操作主义纲领的基础上,他的成功已使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观点都转而信仰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观点。
无尽的探索20.真理;概率;验证
20.真理;概率;验证
到《研究的逻辑》出版的时候,我才感到有三个我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真理、概率以及就理论的内容及其验证方面把理论加以比较。
虽然虚假的概念——也就是不真实的概念——因而不言而喻,真理的概念——在《研究的逻辑》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十分朴素地使用这个概念,并且仅仅在第84节以“论‘真的’和‘被验证的’概念的使用”为题对此进行了讨论。那时,我并不知道塔尔斯基的工作,或者两种元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区别(一种被卡尔纳普称为“句法”,另一种被塔尔斯基称为“语义学”,后者由玛丽亚·冠克辛斯卡加以十分清楚地辨别和讨论);然而就真理和确认之间的关系而言,我的观点多少成为维也纳学派中——也就是说在像卡尔纳普那样接受塔尔斯基真理论的那些成员中的标准。
当1935年塔尔斯基向我说明了(在维也纳的人民公园)他的真理概念定义的思想时,我才认识到它是何等的重要,并且认识到他终于恢复了大受中伤的真理的符合说,我认为这种理论是并且永远是常识的真理观。
我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主要是试图使我自己明白塔尔斯基做了些什么。说他已经给真理下了定义,是不确实的。诚然,对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化的语言来说,他已概述了定义的方法。然而他也澄清了还有不是用定义而是用公理引入真理的其他基本等价的方法,所以真理是应当用公理还是用定义引入的问题不可能是个根本问题。此外,所有这些精确的方法限于形式化的语言,并且像塔尔斯基所表明的那样不能应用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日常语言。虽然如此,清楚的是我们能够从塔尔斯基的分析中学习如何稍加小心地在日常讲话时使用真理的概念,而且在日常意义上——真理是符合事实——使用它。我最后判定塔尔斯基所做的就是要说明:一旦我们理解了一种对家语言与一种(语义学的)元语言——我们用以谈论陈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