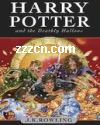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鲂挛侍狻蛘哒缥宜衔氖且桓鑫蔽侍猓菏奔渲甘庆卦黾拥慕峁穑浚┧魑桓稣苎Ъ乙脖换靼芰恕T谒耐砟辏砗盏氖抵ぶ饕搴桶滤固赝叨碌摹拔苈邸保ㄋ橇┒际欠丛勇壅撸┑挠跋煸黾拥萌绱酥螅故共6穆チ诵判模ㄕ缢摹镀謇砺劢惨濉匪砻鞯哪茄U钦庵盅沽κ顾ナЯ硕运约汉驮邮翟谛缘男拍睢K岢觯毫W蛹偎狄残碇皇且恢痔剿餍缘氖侄危ú皇且恢止赜谖锢硎翟诘募偎担B砗斩哉庵忠饧姆从κ牵安皇锹壅械囊恢滞耆锸科诺亩钥故侄巍保ā癳in nicht ganzritterlicher polemischr Zug”)。
至今玻尔茨曼的实在论和客观主义既未被他自己也未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对于历史则更糟。)即使他所捍卫的原子论借助他的统计学涨落的思想取得了首次伟大的胜利(我指的是1905年爱因斯坦论布朗运动的论文),但成为年轻的爱因斯坦以及因而可能是量子力学奠基人所接受的信条的却是马赫的哲学——原子论主要反对者的哲学。当然,没有人否认玻尔茨曼作为物理学家,尤其是作为统计力学两位奠基人之一的伟大。但是不管在复兴他的思想的道路上有什么障碍,它似乎或者同他的主观主义的时间之矢理论(薛定谔、赖辛巴赫、格吕恩鲍姆)有联系,或者同他的H定理的主观主义的统计学诠释(玻恩、杰恩斯)有联系。历史的女神——作为我们的法官而被人崇拜——仍然在玩弄她的诡计。
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揭示了认为时间之矢是主观幻觉的唯心主义理论,也因为反对这个理论的斗争近年来已花费了我许多心思。
无尽的探索36.主观主义的熵理论
36.主观主义的熵理论
我在这里说的主观主义的熵理论不是玻尔茨曼的理论,在玻尔茨曼的理论中时间之矢是主观的,但熵是客观的。更确切地说,我指的是原先由列奥·斯齐拉尔德提出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每当我们有关一个系统的信息减少时,该系统的熵就增加,反之亦然。根据斯齐拉尔德的理论,信息或知识的任何获得必须被诠释为熵的减少:按照第二定律,则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以熵的至少等量增加为代价。
我承认在这个论点中有某种在直觉上令人满意的东西——当然尤其对一个主观主义者来说是如此。无疑,信息(或“信息内容”)可用不可几性来量度,事实上我于1934在《研究的逻辑》中已经提出这一点。另一方面,熵可与所谈论的系统状态的可几性等同。因此下列的等式似乎是正确的:
信息=负熵;
熵=缺乏信息=无知
然而使用这些等式应特别小心:业已表明的一切是熵和缺乏信息可用概率来量度,或可诠释为概率。但这并未表明它们是同一系统同一属性的概率。
让我们考虑熵增加的一个最简单的可能存在的例子:推动活塞的气体的扩散。设有一汽缸,中央是一活塞(参见图2);用热浴使汽缸保持恒定的高温,以使热的任何损失立即得到补充。如果左边有一气体把活塞推向右边,因而使我们能够获得功(提升一个砝码),那么我们为此所花的代价是增加气体的熵。
为了简单明了起见,让我们假定气体仅由一个分子——分子M组成。(这种假定在我的对手——斯安拉尔德或布里鲁国——中间是标准的,因此采取这种假定是容许的;但将在后面对它加以批判讨论。)于是我们可以说,熵的增加与信息的丧失相对应。因为在气体扩散以前,我们知道气体(即我们的分子M)在汽缸的左半边。在扩散以后,以及当它已经做了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在左半边还是在右半边,因为活塞现在在气缸的右端:我们知识的信息内容显然是大为减少了。
我当然准备承认这一点。我不准备承认的是斯齐拉尔德的更为一般的论据,他试图用这个论据建立这样一个定理:关于分子M位置的知识或信息,对转换成负熵,反之亦然。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定理恐怕是十足的主观主义胡说。
斯齐拉尔德的论据由一个理想化的思想实验组成,我想稍加改进可表述如下。
假定我们在t0时知道气体——就是说一个分子M——是在我们汽缸的左边。于是我们可以在这时悄悄地把一只活塞(例如通过汽缸侧面的狭缝)放进汽缸的中央,并且等到气体的扩散或M的动量把活塞推向右边、抬起一个砝码为止。显然所需的能由热浴供给,所需的和丧失的负熵由我们的知识供给。负熵消耗之时,即在扩散过程中以及在活塞向右边运动期间,知识就丧失;当活塞到达汽缸右端时,我们就丧失了M位于汽缸那一部分的全部知识。如果我们通过把活塞推回来使程序逆转,就需要等量的能(补充到热浴上),并且等量的负熵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因为我们终结于我们由之开始的状态,包括气体——或M——在汽缸左半边这一知识。
因此,斯齐拉尔德提示,知识和负熵可以互相转换。(他用分析——我认为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分析——直接测定M的位置来支持这一点;然而由于他只是提示,而不是主张,这种分析一般是合理的,我将不去反对它。此外,我认为这里提供的描述多少增强了他的理由——无论如何这种描述使它似乎更为有理了。)
现在谈谈我的批判。为了达到斯齐拉尔德的目的,必不可少的是用单个分子M而不是用许多分子组成的气体去操作。如果我们有一若干分子组成的气体,关于这些分子的位置的知识一点儿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因此这种知识是不充分的),除非气体确实碰巧正处于负熵状态;比方说,大多数分子在左边。但这显然是客观的负熵状态(而不是我们关于这个状态的主观知识),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客现状态;而且,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状态,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时刻把活塞悄悄地放进去,那么,我们又能利用这种客观的状态(因此知识不是必需的)。
那么,让我们如斯齐拉尔德所建议的那样先用一个分子M去操作。可是在这种场合,我断言我们无需任何有关M位置的知识:我们需要的一切是把我们的活塞悄悄地放进汽缸。如果M碰巧是在左边,活塞就会被推向右边,我们就能升起砝码。而如果M在右边,活塞就会被推向左边,我们也能提升砝码。在这种仪器上安装某种传动装置,使之在哪一种场合都能提升砝码,而毋需我们知道即将发生的运动将取两种可能的方向的哪一种,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为容易的了。
因此为了使熵的增加得到平衡,这里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斯齐拉尔德的分析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对于知识之进入物理学他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就斯齐拉尔德的思想实验,还有我的思想实验多说几句。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够利用我的这个特殊实验来反驳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定律)吗?
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我确实相信第二定律实际上被布朗运动反驳了。
理由是:用一个分子M代表某一气体的假定,不仅是理想化的(这无关紧要),而且等于假定:气体在客观上永恒处于熵最小的状态。我们必须假定,正是气体,即使扩散也不会占满汽缸的下层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只在活塞的一边发现气体。例如我们可以把活塞中的瓣转成比方说水平的位置(参见图3),使得活塞能够没有阻力被推回到中央,瓣在中央又被转回到它做功的位置;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完全肯定,整个气体——整个M——只在活塞的一边;因此它就会推动活塞。但是假定事实上气体中有两个分子;那么这两个分子可能在两边,活塞就不会被它们推动。这表明,只用一个分子M在我对斯齐拉尔德的答复中(正如在斯齐拉尔德的论据中那样)就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并且它也表明如果我们能有一种由一个强有力的分子M组成的气体,它确实违反了第二定律。但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第二定律描述的本质上是统计学的效应。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第二个思想实验——两个分子的情况。知道两个分子都在汽缸左半边确实使我们能够把瓣关上,因而把活塞置于做功的位置。但是把活塞推向右边的不是我们关于两个分子都在左边这一事实的知识。宁可说,那是两个分子的动量——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是气体处于低熵状态这一事实。
因此我的这些特定的思想实验并不表明,第二类永动机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利用一个分子对斯齐拉尔德自己的思想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的思想实验表明,斯齐拉尔德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而试图使第二定律的主观主义诠释立足于这类思想实验是站不住脚的。
我担心已经建立在斯齐拉尔德的(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论据以及其他人的类似论据上的大厦还会继续增高;我们会继续听到说“熵——像概率一样——是知识缺乏的量度”,机器能由知识驱动,像斯齐拉尔德的机器一样。我想,只要有主观主义者提供这样的不可知论,将继续产生夸夸其谈和熵。
无尽的探索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我也曾被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强烈地吸引住——尽管我对大多数进化论哲学家没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个大哲学家以外,那就是塞缪尔·巴特勒。
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含有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即通过达尔文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的训导而使知识成长的理论;这个论点(我在那本书中对此有所暗示)当然增加了我对进化论的兴趣。我必须说的一些事情出自试图利用我的方法论以及它与达尔文主义的类似来阐明达尔文的进化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包含了我联系进化论讨论某些认识论问题的第一次简略尝试。我继续研究了这些问题,当我后来发现我已达到十分类似薛定谔的一些结果时,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1961年我在牛津作赫伯特·斯宾塞纪念讲演,题为“进化和知识之树”。我认为,在这次讲演中,我稍为超出了薛定谔的思想;并巳从此以后我进一步提出了我所认为的对达尔文理论的改进,然而严格地保持在与拉马克主义相对立的达尔文主义范围内——在与训导相对立的自然选择之内。
我又试图在我的康普顿讲座(1966)中阐明若干有联系的问题,例如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地位问题。我认为,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关系犹如:
演绎主义 与 归纳主义
选择 与 反复训导
批判性除错 与 辩护的关系。
上表右侧的观念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确立了对达尔文主义(即左侧)的一种逻辑说明:可把它描述为“几乎是重言式的”,或可把它描述为应用逻辑——无论如何可描述为应用境况逻辑(正如我们以后会明白的那样)。
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尔文理论——在广义上,是试探和排除错误理论——的科学地位问题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
然而不止如此。我还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我称之为“境况逻辑”的一种应用。作为境况逻辑的达尔文主义可理解如下。
没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就被淘汰掉。
除此以外,假定存在一种特殊的框架——一组也许罕见而高度独特的条件,其中能有生命,或更明确地说,有自我复制的然而又可变异的物体。于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境况,其中试探和除错的概念,或达尔文主义的概念,不仅成为可应用的,而且几乎是逻辑上的必需。这并不是说不论是框架还是生命的起源都是必然的。也许有一种生命有可能存在的框架,但是在其中尚未发生导致生命的试探,或在其中导致生命的一切试探都被淘汰了。(后一种情况不只是一个可能性,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的:不止有一种途径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遭到毁灭。)意思是说,如果产生允许生命存在的境况,如果有生命起源,那么这整个境况使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成为一种境况逻辑的概念。
为了避免误解,达尔文理论并不是在每一种可能的境况中都是有成效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也许甚至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境况。然而即使在没有生命的境况中,达尔文的选择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相对稳定的原子核(在所说的境况中)比不稳定的原子核倾向于更丰富,化合物也是如此。
我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能说明生命的起源。我认为十分可能的是,生命是如此极其不可几,以致什么主义也不能“说明”它为什么起源;因为统计学说明最终必须有很高的概率才行。但是如果我们的高概率不过是那种低概率由于可利用的时间的无限才成为高概率(正如玻尔茨曼的“说明”中所说的,请参阅35节注以前的正文),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说明”几乎一切事情。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猜想,任何这类说明可应用于生命的起源。但是这并不影响把达尔文主义看作境况逻辑,一旦认为生命及其框架构成我们的“境况”的话。
我认为除了说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外,对于它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