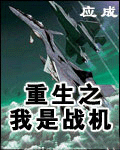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文学]我是我的神-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乌力天扬在萨努娅的书柜里找到一本《人体解剖学》。书很厚,烫金的繁体字书名,书名下有一排拉丁文,像一条扭动着的有着灵性的蝮蛇。乌力天扬躲在贮藏室里,花了几天时间,一页一页看完书中的那些图片。他汗涔涔的,感到强烈的头晕,感到胳膊上正在长出了不起的肌肉,它们在怂恿他,让他朝天空扔出石头。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老到完全可以做一位先知。
乌力天扬派高东风向鲁红军等人送去鸡毛信,让他们晚上到防空洞集中,他将在那里朝天空扔出他的第一块石头。高东风气咻咻地回来,向乌力天扬汇报,鲁红军很高兴乌力天扬把他当朋友,他早就觉得他和乌力天扬是朋友了,他肯定来;简明了不来,他说乌力天扬又不是司令,他不听乌力天扬的。乌力天扬一点儿也不生气,说活该。高东风吸了一下鼻子,可怜巴巴地问乌力天扬,那我是不是也活该?乌力天扬搂住高东风的肩膀,认真地说,你放心,你和鲁红军一样,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活该。
晚上,乌力天扬怀里揣着那本神秘的图书,轻手轻脚地从楼上下来,拉开大门,溜进院子,消失在夜幕中。
乌力天扬像怀了孕的母猪一样,托着肚子,哼哼着穿过黑暗,到防空洞门口不进去,先抬腿踹铁栅栏门,踹一脚,再踹一脚,动静很大,气焰嚣张。
其他人早到了,等着乌力天扬,趁机在矿石灯昏暗的光晕下赌一盘烟标。简明了输给鲁红军两张南洋烟草公司的“双喜”,气不打一处来,往一边推看热闹的高东风,说去去去,小心溅一身血。高东风委屈,听见有人踹铁栅栏门,知道是乌力天扬,谄媚地跑出去迎接。
乌力天扬两只手端着肚子,摇晃着身子进来,看一眼简明了,拉长声音说,你来干什么?又没有打你的米。简明了不吭声,气呼呼地收了烟标,没头没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乌力天扬叫这些人在他面前站整齐,开始点名。他顺着人头叫名字,规定好,叫到谁,谁往前迈一步,挺着胸脯立正,大声说“到”。说“来了”不行,说“哎”也不行,非得说“到”。
点到简明了,简明了有些不高兴,说我不是站在你面前吗?我这么高的个子,你不会看不见。乌力天扬极不耐烦地说,我知道是你呀,电线杆子个头儿也不矮,我拿电线杆子当你成不成?
大家都想早一点儿知道乌力天扬要扔什么石头,都埋怨简明了。鲁红军这个时候要表现自己和乌力天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就说简明了,你烦不烦?你又不是江竹筠,就不能说个“到”呀。简明了被自己的同学这么说,委屈得要命,看了看四周,大家都拿不待见的眼神儿看他,只好极不情愿地挺了胸脯立正,说了声“到”。
乌力天扬看人都让他点射过了,也挺了胸脯向他立过正了,这才让鲁红军站到自己身边,让罗曲直把矿石灯交给鲁红军,像展示宝贝一样,慢慢地、生孩子似的从衣襟下取出厚厚的书。简明了伸手去乌力天扬怀里抓书。乌力天扬毫不客气地一巴掌打开简明了的爪子,然后舔了舔手指,小心翼翼地在灯下翻开书,指着其中一幅剖开的猪下身似的彩色插图让孩子们看。看看吧,看看我们遇到了什么对手。他口气凝重地宣布。
孩子们的脑袋凑得像一丛团结一致的毒蘑菇。有人屏住呼吸。有人喘着粗气。有人晚上吃了茴香菜馅的饺子。有人晚上吃的是醋熘白菜,葱花炝的锅。
罗曲直看清了插图,蛇咬住手似的叫了一声,恐惧地往后退去,然后蹲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孩子们相互看一眼,轰地笑了,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一只见了亮光的木蠹蛾从外面飞进来,绕着矿石灯飞,飞出很多奇妙的姿势。
“笑什么,我见过。不是图片上的,是真事儿。”罗曲直吐完,揩一下嘴。
“吹吧。吹。”简明了发现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妙,不要说正规军,连土八路的干活都危险,于是抢白罗曲直,同时朝乌力天扬讨好地看了一眼。
“我没吹,是真的。那次我爸生病,护士到我家给我爸打针,打完针,我爸从床上起来,裤子没提,把护士按住了。”罗曲直神经质地笑了笑,马上收住。
“你爸怎么了?按住干什么?”简明了抽了一口冷气。
“明知故问是不是?”鲁红军嘘了一声,说完简明了再说罗曲直,“你爸演电影哪。”
“没演电影。我爸把护士按在床上。”罗曲直急了。
“没演电影你爸让你看?”简明了也嘘,“吹牛不打草稿。”
“我爸有红锡包,我想偷一包,拿来扳本儿。我爸去厕所撒尿,我溜进去。谁知护士来了。她说首长好。她说首长我给您打针来了。她说首长不疼吧。她说首长您别这样。她后来哭了,我爸就哄她,说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嘛。我躲在床下,护士在床上,我爸骑在护士身上。不信你们去问,内科的蔡小枚,就是嘴角上有痣的那个。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想吐,吐完以后就兴奋。”罗曲直抢着说,生怕被人拦下来,说完卸下包袱似的喘了一口气,轻松了。
孩子们不说话了。防空洞里一片寂静。这他妈才是原子弹呢!这他妈才是哥萨克夏伯阳呢!他们突然有一种沮丧感,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英勇作战,他们却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沉默了一会儿,孩子们缓过来,简明了带头,大家笑成一片。有人磨牙齿,咯咯的。有人神经质地打嗝。简明了朝乌力天扬手里的书看了一眼,离开乌力天扬,朝罗曲直走过去,很友好地把一只胳膊搭在罗曲直的肩膀上。
乌力天扬不笑,气愤得要命,恨不得扇罗曲直一记响亮的耳光。乌力天扬最讨厌自以为是的人。他从一本秘密的有灵性的书上得到的先知的快乐被剥夺了,这让他忍无可忍,他非教训教训剥夺者不可。你妈的撒谎。乌力天扬冷冷地合上图书,一字一句地对罗曲直说,既然你知道得比我还多,那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你走吧。
罗曲直慌了手脚,不兴奋了,乞求乌力天扬让他留下。乌力天扬不光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对手,还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有很多别人想不出来的鬼点子,总是能在众人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拿出主意,这样的乌力天扬差不多就是组织,罗曲直必须向组织靠拢。
“天扬,让他留下吧。”简明了把手从罗曲直的肩膀上收回来,离开罗曲直,走到乌力天扬身边,劝和道,“一会儿罚他,让他把他爸的事儿再说一遍,说详细一点儿。”
“还不如罚他去偷红锡包呢,一人偷一包。”鲁红军向乌力天扬建议。
“鲁红军你总是这样,利欲熏心!你这种人是没遇上抗战,遇上抗战非当伪军不可!”简明了有点儿急,还记着同学叛变的事,攻击鲁红军。
“我怎么利欲了?我看你才利欲,就想听流氓故事。”鲁红军反唇相讥。
“哈!”简明了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向乌力天扬摊开手,以示清白,“我想听流氓故事吗?天扬你说,我想还是不想?”
“你再吐怎么办?”乌力天扬厌恶地瞥罗曲直,“你把我们都熏晕了。”
“肯定不吐,”罗曲直发誓,“再吐我吐在手绢里,藏起来。”
“早就知道你是撒谎大王。”乌力天扬鼻子里哼了一下,警告罗曲直,“以后你要再敢编故事,将被彻底地从革命队伍里清除出去。”
乌力天扬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他在向天空扔出他的石头。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扔石头的人。他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多,比如说,把这册精美的书拿给简雨槐看,让她看看,他发现的石头是多么的神奇啊。他认定简雨槐一定会喜欢这块石头。他认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但是,乌力天扬的计划没有成功。当天夜里,乌力天扬揣着书回家的时候,乌力图古拉在门口堵住了他。一眼能看清天空中飞过的鸟儿肚子里有没有蛋的乌力图古拉让乌力天扬把怀里掏空,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然后叫来警卫员何子良。让把书拿到院子里烧掉。萨努娅责问乌力图古拉为什么要烧她的书。乌力图古拉回到家里,连萨努娅其他的书一块儿翻出来,一本本检查,稍有嫌疑的,一律丢进火堆里。两个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乌力天扬眼泪汪汪地躺在床上,那天晚上,乌力天扬在心里暗暗发誓,等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一定不会命令儿子把藏在怀里的图书拿出来。他会为儿子买很多有着精美插图的书。他会帮助儿子偷偷地把书从家里偷出去,并且和儿子一起,躲在某个防空洞里,什么话也不说,倚着干燥的洞壁坐下来,安静地看他们的石头。
因为向天空扔石头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不甘打击的乌力天扬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他要把停泊在废料场上的那架日本海军96式陆基攻击机炸掉,以证明除了挨父亲的打,他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到。
飞机是日本侵华军队投降时留在湖北山坡机场的,被拖来做实体弹道测验,然后丢弃在江边的废料场上。飞机上的主要装置已经被拆掉,只留下一具巨大的空壳,像一座主人离去后的魔王空巢。孩子们拿这架巨大的飞机当游戏场,他们喜欢在二十五米长的机翼上摇摇晃晃地跑动,或者钻进十七米长的机舱里玩,而从四米高的飞机上往下跳,历来是孩子们打赌中最刺激的项目之一。
乌力天扬对这架有着蜻蜓复眼式驾驶舱的飞机的全部了解,来自四哥乌力天赫。
乌力天赫酷爱兵器,对各种武器的制式、配制和性能了如指掌,常常让那些技术员大吃一惊。总工程师胡兆周有一次对乌力图古拉说,他得尽快活到六十岁,把位置让出来,免得乌力家的老四等得不耐烦,把他踢出总工程师的办公室。乌力图古拉听了得意地哈哈大笑。
乌力天扬非常讨厌日本人。他对日本人的小胡子、点火烧房屋时狰狞的大笑、说“嗨伊”时愣头愣脑的样子,还有击沉邓世昌和他的致远号这些事充满了仇恨,对整个侵华战争期间,96式陆攻机作为侵华日军的主力轰炸机,对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进行长期轰炸这件事充满了仇恨。乌力天扬一直在找机会向日本人宣战。他决定把基地的那架96式陆攻机炸掉。
乌力家的火柴用得很快。厨师万东葵总是不明白,两天前才买的一大包火柴,一眨眼工夫就没了,数火柴盒子,一个不少,可就是空着。有一段时间,他老为这件事烦恼,不断向何子良抱怨。何子良问他是不是犯癫痫,划一根火柴灭了,再划一根火柴又灭了,要那样,就不是火柴的问题,而是万东葵要赶紧去医院治病的问题。
损失最大的不是万东葵,是乌力天扬自己。为了凑齐足够的火药,乌力天扬不得不忍痛用子弹壳和烟标去换火柴。那些烟标不是脏兮兮的“光荣”、“恒大”、“美丽”、“大重九”、“大公鸡”、“大生产”,或者阿尔巴尼亚的“山鹰”和朝鲜的“祖国”,而是“老刀”、“哈德门”、“红炮台”、“一品香”、“紫罗兰”这样的老牌子。
鲁红军那段时间老往基地跑,他打算搜集充足的弹药,代表“革干子弟”对“革军子弟”发动一次总攻击。鲁红军验明烟标的身份和品相,仔细收好,从书包里取出火柴,一盒一盒清点给乌力天扬。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鲁红军拍了拍乌力天扬的肩膀,深沉地嘱托着。
乌力天扬完全疯了,他甚至用一套《七侠五义》向简明了换了三百盒火柴。他们讨价还价。乌力天扬眼眶里噙满泪水。简明了就像黄世仁,乜斜着乌力天扬手中的烟标,卑鄙地掏出六元钱在乌力天扬眼前晃来晃去,朗朗地背诵课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乌力天扬就此永远地失去了他的《七侠五义》。
乌力天扬花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时间搜集火柴,整整搜集了一千七百零三盒。他躲在防空洞里,刮下火柴头子,用擀面杖擀,筛子筛,碾成药面,在药面中掺上硫磺、硝粉,做成炸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用制成的炸药做了一枚小拉雷,带着高东风到江边,让高东风在一旁望风,自己拉响它。拉雷轰的一声爆炸开,将覆盖在雷上的砖头炸得四分五裂。高东风被拉雷的爆炸威力吓白了脸,半天没说出话。
“敬爱的首长、同志们,”乌力天扬眼里噙着热泪。心里大义凛然地默默念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乌力天扬实施他伟大抱负的那一天,孩子们都去了。乌力天扬那天打扮得很威风,腰里盘着长长的导火线,袖口和裤腿用鞋带扎紧,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只钢盔,钢盔缺了一块檐,有些锈迹斑斑,戴在头上,显得很悲壮。乌力天扬要求所有的孩子都退到两百米开外的江堤后面,趴在草丛中。炸药的威力很大,足以把一个鬼子中队炸到天上去,我不想伤着乡亲们。乌力天扬用突击队员的口吻深沉地说。
孩子们看着乌力天扬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下了江堤,摇摇晃晃地走向那架陆基攻击机。他个子本来就不高,那样摇摇晃晃地朝远处走去,越走越远,远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人影。空气黏得像泼翻的番茄汁。江上有几只船,老也不动,好像是被人画在那儿的。
孩子们看见乌力天扬走到陆基攻击机下,仰了头往上看。他把军用挎包从胸前移到身后,用皮带扎紧,开始顺着拆掉发动机的动力架往机翼上爬。他没有选择更容易的驾驶舱和投弹舱口,这让人不可思议。他爬上机翼,沿着长长的机翼往机身方向走。他险些失了脚,从飞机上摔下来。孩子们惊叫一声。他们看见他扶住机翼,让自己保持住平衡,慢慢站起来,继续朝机身走去。
“如果他摔下来,炸弹就会爆炸,他连头发丝都留不下一根。”高东风硬着嗓子说。高二油已离开部队,本要回老家的,乌力图古拉通过关系把高二油安排到武汉锅炉厂,高东风因此特别感激乌力天扬。
“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