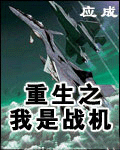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文学]我是我的神-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像填海的精卫那样地搂紧了他,把他纳入她的身下。现在,她是天了,而他是地;她是风了,而他是万物;她是雨水了,而他是河床。她感到她的身下,他在渐渐地变暖过来。她哭了,像一牙天隙、一缕风、一滴雨点那样地哭了。
授功大会召开之前,单位和个人的立功情况已经确定下来。十二连因为穿插有力,作战威猛,战绩卓越,被中央军委授予“敢打敢拼英雄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排被授予“英雄尖刀排”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乌力天扬、肖新风、鲁红军等五人被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三排四十三人,除留守一人外,其余四十二人个个立功。
“真的?”简雨蝉在电话那头开心地大叫。然后咯咯地笑,笑声直往乌力天扬心底里钻。钻得乌力天扬痒酥酥的,“你太棒了天扬!我为你感到骄傲!亲你三百下!”
立功名单宣布之后,紧张了好些天的尤克勤松了一口气,把乌力天扬找去谈了一次话,通知他,准备参加军区组织的巡回演讲团,去各地演讲。尤克勤特地敲了敲乌力天扬的边鼓,要他别骄傲,革命路上继续前进,当然也顺便给了一勺糖,透露了送他去军校读书的计划。营里已经讨论过军校生名单,你在名单上,但还没有最后定,你给我警惕再警惕,别再干出翻墙抄棍子的荒唐事,小心我饶不了你。
段人贵没有功,这件事大家有心理准备。段人贵人已被转到保卫部门,伤没全好,带伤审查。
鲁红军家接到部队通知,知道鲁红军负了伤。立了大功。武昌区委敲锣打鼓往鲁家送喜报,慰问活动搞了半个月没结束。
罗曲直家也接到部队的通知,知道罗曲直失踪了。罗罡往广两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有没有可能搞错,罗曲直不是失踪,也不是被俘,而是牺牲了,要是那样,罗曲直就是烈士,评不评功没什么,至少不是被俘,也没有投敌的嫌疑,那样的话,部队应该给个合理的说法。不要让烈士含冤九泉,也不要让烈士的亲人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简雨蝉听说了鲁红军的事,请了假,搭乘一辆军车大老远从县里赶来。到鲁红军的病房,往乌力天扬身边一坐,说鲁红军,你没事儿,政委说你的情况是最好的,再过几天就给你康复治疗,要不了多久,你就能满地跑了。还和鲁红军开玩笑,警告鲁红军别随便让姑娘看他的断腿,姑娘们脆弱得很,最受不了这个,一看非爱上他不可。
简雨蝉下午要赶回野战总医院。乌力天扬要守鲁红军,说我不送你。简雨蝉说,送什么。我又不是不认路。想起什么又咯咯地笑,笑完亲热地把乌力天扬拉到跟前,踮了脚尖扒在乌力天扬的肩头说,不是我赖账啊,当着人的面,亲不成,留着秋后一块儿算账。乌力天扬心里痒痒的,说好了不送,还是送到医院门口,看进进出出的人都把月光投向简雨蝉,那份儿得意,想收敛都收敛不住。
“少给我来这一套。什么功不功的,我就不是为这个上去的。”鲁红军冷冷地瞟了一眼送走简雨蝉回到病房的乌力天扬,冷冷地说。
“你说过你想当天使。”乌力天扬干巴巴地说。
“像现在这样,半个天使?”鲁红军恶毒得很。
“我不会不管你。我会和你在一起。”乌力天扬赌咒发誓。
“你算个屁。”鲁红军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乌力天扬,“你功拿了,战斗英雄当上了,马上要到处去卖嘴皮子,嘀嘀嗒,嘀嘀嗒,卖完嘴皮子回来继续往上爬,我呢?我怎么爬?没有腿,怎么爬?”
“你要正视现实,这样没用。”乌力天扬苦苦地劝。
“正视什么?我操你妈正视什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干脆点儿,给我补两枪,把我眼睛崩瞎,我就没什么可正视的了!”鲁红军恶劣得就像一只一千年没洗过的夜壶。
“那你要怎么样?雷已经踩上了,腿已经锯掉了,我又不能让你回到踩雷前,让你不踩雷不锯腿!”为了那枚该死的踏发雷,乌力天扬总觉得自己在鲁红军面前抬不起头。他甚至想过。要是他和鲁红军面前放着那颗雷,不能选择。必须去踩它,他会不会抢在鲁红军前面去踩那颗雷?回答是,他会,他会抢着去踩那颗雷。现在乌力天扬火了,他伺候鲁红军已经伺候够了。不想再伺候了。
鲁红军呆呆地看着乌力天扬。病房里安静极了,能听见隔壁病房里的呻吟声。另一头的病房,是几个伤员轻轻的歌声:“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我……我没有睾丸了……我不能生孩子了……我连女朋发都谈不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泪水顺着鲁红军的脸颊流淌下来。他两只手神经质地抓着床头的吊环,肩膀抽搐着,像一张不知所措的驴皮,风一吹就能散掉。他慢慢地从乌力天扬脸上收回视线,慢慢地松开手,慢慢地躺到床上去,企图把身子缩成一团。因为没有了腿,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把脸别到一旁,放声大哭起来。
这才是那个问题,他和他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腿,是睾丸,那对外表骄傲、内里孤独、一直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执着地憧憬着的睾丸,它们不在了。它们不是一般的睾丸,不是简单的睾丸,它们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男人的未来,现在,它们不在了,永远地消失了。
部队专门在医院召开隆重的授功大会,为不能离开病床的立功者戴上功勋章。
鲁红军坐在床上,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团首长把光闪闪的一等功勋章戴在他胸前,军报记者抢上前去拍照,闪光灯咔嚓一下,热烈的掌声在病房里响起。握手。敬礼。鲜花入怀。首长鼓励。你是祖国的英雄,好好养伤,早日回到部队。让英雄讲几句。谢谢首长,谢谢牺牲的战友,谢谢祖国,谢谢祖国人民。
医院请来假肢厂师傅,给截肢伤员们量尺寸。假肢厂师傅激动地表示,一定以解放军英雄为榜样,用最强的责任心、最优良的材料、最好的技术为英雄们做出义肢。
鲁红军的照片和事迹上了《解放军报》,二版头条,整整半版。在报道鲁红军事迹的时候,军报记者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没有写鲁红军是在回国途中踩响的地雷,而是写他在攻打某高地的时候为保护战友勇敢地踩响了地雷,那篇报道的题目叫做《为了祖国,勇士扑向地雷》。
鲁红军的父亲见到鲁红军时完全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学生,不断地向鲁红军检讨,承认自己过去对儿子的悲观失望是毫无道理的,历史证明他错了。鲁妈妈收集了好几份《解放军报》。每天读一遍,每读一遍就哭一次。鲁爸爸说你哭什么?你要骄傲,为你儿子骄傲!鲁红军病房里的鲜花越来越多,来探望的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越来越多,这让哭过以后的鲁妈妈真的很骄傲。
乌力天扬始终在回避该死的睾丸问题。他心烦意乱,但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去医院,床架吱呀地一屁股坐下,参观鲁红军生出新鲜肉芽儿的断茬处。
乌力天扬还抢着看全国人民给战斗英雄鲁红军写来的信。自从鲁红军的事迹上报纸以后,护士每天都会送来大量的信。他们的信写得全都让人感动不已。鲁红军靠在床头,头顶罩着光环。眼里闪烁着泪光,他每天都要护士为自己读全国人民的来信。有的信,那些充满了敬仰的信,他给它们编了号,要护士反复读。如果乌力天扬在,他就要护士把读信的任务交给乌力天扬,让乌力天扬读,让护士坐在一旁听。
乌力天扬大声地念那些信,像念诗歌,一边念一边摇头晃脑,叹气,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羡慕得一塌糊涂,然后喘着气把信放下,用卑鄙而夸张的口气大声说,你妈的比中央领导都闪亮!一直到乌力天扬念得哑了嗓子,再也念不动,鲁红军才会很受用地长长地叹出一口气,示意乌力天扬停下。然后,他像一只急于回到巢穴里的刺猬,磨着屁股,动作熟练地缩进被单里,把自己蒙好,不耐烦地对乌力天扬说。你走吧,该干嘛干嘛去,我要睡觉。
演讲团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一个城市演讲几场,马不停蹄,再去另一个城市,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得挤,还有的城市没安排上。那些城市就派人沿路堵截,苦苦哀求,演讲团的领导出来打圆场,解释英雄们太累了,得让他们休息,硬给堵了回去。
三个多月后,演讲团结束了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讲。
乌力天扬一回到连里就被告之,鲁红军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挪到轮椅上,把轮椅摇到走廊里,去摸电闸。鲁红军没有死成,220伏的电把他从轮椅上打到地下。
部队接到命令,要离开广西,返回原来的驻防地。游戏结束了,如果参加游戏的人不准备接着玩下去,就得打扫场地,退场,去琢磨新的游戏。战争当然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就跟生命会世世代代繁衍下去一样,战争也有生命,也会繁衍下去,战争的参与者也应该繁衍下去,比如轮战,比如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比如在战争结束后学会如何把自己往墙上糊。乌力天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鲁红军耗下去,他必须结束掉鲁红军的怯弱。
“你他妈真有本事!摸电门?那样死起来很难看你知不知道?龇牙咧嘴的。舌头吊出来,屎糊一裤子,比骟猪难看多了!你有这个本事。干嘛不撞墙?红血白脑浆,样子更好看,你撞墙去呀!”
“你当我不敢?要能站起来,我就撞!”
“要什么站起来?就你这个样子,你能站起来吗?有资格站起来吗?站不起来没关系,你往地上撞,你拿地当墙,撞吧,撞呀?怎么不撞?懦夫!你他妈懦夫!”
“随你怎么说。说完没?说完滚蛋!”
“说什么?你有什么好说的?你那都是假的!你的勇敢都是假的!鸡巴整天往基地跑,也就是混件军装穿穿,讨把弹壳玩玩儿,玩儿什么玩儿?你就不是当兵的种,你就不是当兵的命!你从小就这样,汪百团开一枪你都往长江里跳,你玩儿不起!我说你怎么不把裤口往后开?加块屁帘儿,那样就不用换开裆裤了,要不你把裤口往边上开,蹲着撒尿!”
“我怎么撒尿和你没关系。我说了,我没腿,我用小便壶。小便壶你没用过吧?哈哈!”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去你妈的,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有吗?”鲁红军哆嗦着,灰着脸看气势汹汹的乌力天扬,怪声怪气,“‘这回亲不成了’,哈!‘秋后一块儿算账’,哈!你妈的像头发情的骡子,你们全都是发情的骡子,让我寡蛋似的挂着,你他妈是人不是人!”
“不就是这点儿破事儿吗?不就是想操操不成吗?”乌力天扬被逼进绝境,没有了退路,浑身颤抖,“好吧,鲁红军,我他妈陪你,我奉陪到底!我也不操,也做寡蛋。也挂着,行了吧!”
“吹吧,尽管吹吧,不愧是演讲团的人,吹牛不脸红!”鲁红军往被单里缩,不再理会乌力天扬。
“鲁红军,鲁红军你听好了,我要再碰简雨蝉一手指头,我他妈不是人!”乌力天扬一字一句地说。
乌力天扬气喘吁吁,仇恨地盯着缩进被单下的鲁红军。被单下,鲁红军突然笑了,嘿嘿的,像只被人踩了一脚的蛤蟆。
简雨蝉被垂头丧气的乌力天扬讲述的那个荒唐故事弄得目瞪口呆,然后她哈哈大笑,人像抽了筋脉的树叶,软软地往桌上趴,哎哟哎哟地揉肚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别笑好不好,我说的是真的。”乌力天扬脸色如土,不断地伸长脖子往下咽唾沫,紧张得要命。也晦气得要命。
简雨蝉还笑,为了要报复乌力天扬,一撑桌角站起来,人像往树上挂的小豹子,挂在乌力天扬肩膀上,要咬乌力天扬的耳朵。乌力天扬血誓都发过了,不能让简雨蝉碰,把脑袋偏向一旁,躲开简雨蝉。简雨蝉还笑,笑了一阵,不笑了,有些吃惊地看着乌力天扬,看一会儿,一只手指头横出去,抹掉挂在长睫毛上笑出来的泪花。
“喂,你来……真的呀?”简雨蝉眉毛往上一挑。
“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吗?”乌力天扬咳嗽一声。
“乌力天扬,你他妈算什么破男人!”简雨蝉端起水杯往桌上一礅。
“嘴啊,嘴又臭了。”乌力天扬想让事情轻松起来。
“你让我怎么香?我一个大兵,操他妈我怎么温柔娴静?我凭什么让人说香?”简雨蝉怒气冲冲,脸都白了。
然后他们都不说话,一个坐在床边,一个坐在桌角。
“你妈生你的时候吞了一粒钢珠半卷钢带。”简雨蝉平静下来,习惯地捋了捋额前的短发,转身趴在桌子上,用手指在那上面画着什么。
“你怎么知道?”乌力天扬困惑地看着简雨蝉。
“猜呗,猜你铁石心肠是怎么来的。”简雨蝉冷笑了一下,噘了嘴,往桌子上轻轻吹气。
乌力天扬不知道该怎么接简雨蝉的话。他接不上。事先做了准备,想了那么多的话,关于鲁红军。关于他和他、他和她,现在一句也用不上,连抽自己耳光也不起作用。他心事重重地坐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见简雨蝉目光不在自己身上,而是津津有味地看桌子,他起来,走过去,看简雨蝉在桌上画什么。
简雨蝉不是画。桌子上,有一对小小的硬甲芫菁,其中稍小一点儿的那只让稍大一点儿的那只背着。乌力天扬先没看明白,看了一阵儿看明白了,两个小家伙,是在旁若无人地做爱。乌力天扬心里一阵发紧,痛苦地想,他对不起她,他他妈的对不起她!
简雨蝉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两只幸福甜蜜的小家伙。两只小家伙动弹了一下,不动了,根本不管不顾,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聚精会神地施承甘霖。简雨蝉又拨动了一下,这回动作大了点儿,男芫菁身子一歪,从女芫菁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