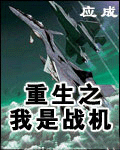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文学]我是我的神-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舞曲刚开始没有多久。还在热情洋溢地问“什么花开花不怕雪,什么军队打仗最坚决”,离曲终还早着哪。在攒动的人群中,萨努娅在一步步接近乌力图古拉。她感到一股热浪隐隐向她涌来。烤得她脸蛋儿灼烫。这让她有点儿不安。脚步错了一个节拍。舞厅是个不错的舞厅,可还没有大成一个世界。不管她是否决定了不理乌力图古拉,他们躲不开,总要见面的。萨努娅接下去想,见面又能怎么样?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面,他把她怎么样了?不是没怎么样吗?萨努娅继续想。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们毕竟是同志,在为同一个事业奋斗。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既然如此,见了面真要是装作没看见,也显得自己太没有胸怀。这么一想,萨努娅就推翻了最初的决定,做出新的决定。她打算在靠近乌力图古拉之后,装作刚刚看见他的样子,不惊不炸地、有礼貌地、微笑着、迷人地向他打个招呼,然后舞步飘逸地离去。以后再也不看他一眼,谁也不招惹谁。做出了新的决定之后,萨努娅浑身一阵轻松,脚下的舞步也轻盈起来。这让她的舞伴一时感到迷惑。不知是乐曲的哪一节段落,让自己怀里的萨努娅由一个美丽的姑娘变成了一只轻盈的岛儿。
萨努娅开始判断舞伴带舞的方向和速度,并且暗中控制着方向和速度。精心制造着一次看起来再巧不过的邂逅。眼见就要接近乌力图古拉了。她却发现他端掉了葛昌南的舞伴,拽着葛昌南往舞池外走,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然后。他松开葛昌南,一个人快步朝舞厅门口走去。
萨努娅愣了一下,立即明白过来,乌力图古拉也看见了她,却并不打算和她“邂逅”,而是准备溜之大吉!这个发现重重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让她非常生气,让春水中的池塘又不平静了,事情是你惹的,不是我惹的,不是我想和你邂逅;你说“合适”就“合适”,你说“算了”就“算了”,这算什么?萨努娅接下去想,本来她已经决定不理他了,因为他负伤。她打算原谅他,去医院向他道别,可是。她去了,他却溜走了,连让她接受他诚恳道歉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她;然后,他们相遇在珠江边。那么遥远的千里之外,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里为同样的事业出现在同一座码头上,那是多好的机会呀,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弥补他做错的事情,热情洋溢地迎向她,向她惭愧地、一遍又一遍地道歉,就算“部队不能久待”。他要“去揍那些不要脸的东西”,至少可以让她在码头上或者船舷边和他握手。让她微笑着、鬓发飞扬地祝他作战顺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再立新功,可是。他就像一只故意要惹母狐狸生气的公狐狸。又溜掉了。让她站在永远也不会移动的岸边,无奈地遥望他得意扬扬的帆影。萨努娅怒不可遏地想,凭什么呀?凭什么他就该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她,惹她生气?她究竟该了他什么!
萨努娅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一种强烈的冲动潮涌而来。她来不及分辨那种冲动到底是什么,只是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委屈到无法忍受。他怎么能这样对待她?怎么能这样无视她那些越来越说不清楚的感情呢?——尽管她恨他,厌恶他。可她却被他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出现和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神秘的失踪给深深地吸引住了;被他昂首阔步从兵面前吧嗒吧嗒走过。搂着枪踢开兵横冲直撞往前冲,泥土埋了九十九层没有死,踹开医院大门满世界去撒野的顽强生命力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萨努娅不顾一切地撇下舞伴,穿过人群。向舞厅门口快步走去,在那里挡住了刚刚拉住大门上光滑的楠木把手的乌力图古拉。
乌力图古拉本来已经溜走了。他已经抓住了舞厅大门的把手。如果他溜走了。溜到大街上,他肯定会有一种冲出包围圈的松弛和快感。可是没有来得及。他预谋中的成功脱险就被终止在离他仅半尺之遥、年轻得令人沮丧、美丽得咄咄逼人、正愤慨地盯着他的萨努娅面前。乌力图古拉傻了眼,窘迫地握着大门的把手,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手从那上面松开。
“萨……萨……这个……”乌力图古拉脑子里一片空白。
乌力图古拉极力控制住一团糟的脑子。尴尬地松开大门把手,抚着大巴掌四下打量,寻找脱身的机会。他必须脱身。这是一场危险的战役,这个他看出来了,“萨雷·萨努娅同志,萨努娅同志。小萨同志,小萨……”
“随便,您可以随便,干嘛不随便呢?”萨努娅有了一些开心。她看出了乌力图古拉的窘迫。毫无疑问,他是窘迫的。她需要用这个来疗治她的创口。但这还不够。她得痊愈对不对?她得从她受到的屈辱中踢开大门走掉对不对?他得为他做出的野蛮行为付出代价对不对?
“是吗?可以吗?”乌力图古拉在挣扎。他用余光侦察了一下舞厅,没有发现可供脱身的机会。却发现已经有人在注意他和她。他俩太出众。太显眼,太一枝独秀两朵争艳,不让人们注意都不行。这是一件好事,可在眼下,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事为好,“萨努娅同志,你能不能,我是说,在这种场合下。注意一点点影响,稍微注意那么一点点?我是说,你能不能,不那么大声嚷嚷?”
“我大声嚷嚷了吗?”萨努娅冷笑一声,弯曲而好看的眉毛往上一挑,“您怎么对影响关心起来了,首长同志?是您教会我嚷嚷的呀。您忘了,在我的宿舍。还有您的指挥部,您是怎么嚷嚷的?您嚷嚷得满世界都听见了,您连椅子都嚷嚷坏了,您连门都嚷嚷坏了,您不也没有注意影响吗?”
“这个。萨雷……萨努娅……同志……小萨……”乌力图古拉语无伦次。“我向你,我是说,萨努娅同志。表示,严重的道歉……”他发现自己完全乱了方寸,怎么是严重呢?应该是严肃才对。可怎么又不是严重呢,那就是严重,“请你接受我严重的道歉。”
“不,”萨努娅倒是很严肃,淡蓝色的眸子清澈地盯着乌力图古拉,嘴角露出一丝愉快的嘲讽,“不不亲爱的首长同志,请您不要这样,这不是您的风格,这不像您,这样的您让我失望,非常失望。”萨努娅感到快乐了。她就是要这样的快乐。她得到这样的快乐非常非常不容易。她尝到了踢开门走掉的欣喜。她希望把这样的欣喜扩大,“第一,您是男人,我是女人,对吧?第二,您是科尔沁草原牧民的儿子,我是柯尔克孜大地主的女儿,对吧?我们是棋逢对手的一对儿,激烈的一对儿,不是吗?”
有生以来头一回,乌力图古拉红了脸,原本青铜一样坚毅的脸,涨成难看极了的紫茄子色。他简直没法儿忍受,想变个蠓子什么的从纱窗钻过去,逃离此地,哪怕钻过去以后再也变不回人形来。现在不是有人注意到他们,而是整个儿舞厅,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们。舞曲还在响着,舞步没有停止,但所有该死的脖颈都他妈的从各种角度扭向他们这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会呀。这简直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凌迟!
乌力图古拉陷入了绝地。乌力图古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说了,我道歉。”乌力图古拉把眼睛睁开,睁成风暴中的骆驼眼的样子,声音有些提高,脸色也有些阴沉。
“您让我有点儿糊涂首长同志。”萨努娅继续冷笑。她一点儿也不怕乌力图古拉的骆驼眼,不怕他提高声音,阴沉脸色。现在轮到她来恶毒了。而且,她觉得她开始迷恋上踢开门昂首阔步吧嗒吧嗒的快乐了,“您是在告诉我,共产主义的大锅里什么裤子都可以洗?”
乌力图古拉生气了,威风凛凛的狮子鼻翕动着。他愤怒地想,是的,是的是的,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对,有那么一点点,嗯,不讲道理,还有,粗暴,还有,不斯文,但是。我不是没有死缠烂打吗?不是主动撤出战斗了吗?不是战略大转移了吗?为什么不看到这个大方向,给人一条出路?再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那么好听的曲子伴奏,我向你道歉,真诚地道歉,你却得理不饶人;这算什么?你就讲道理吗?你的大方向就对吗?
乌力图古拉再一次回头看舞厅,他看见人们仍然朝这边张望,中南局和华南局的领导在休息区小声议论,一个戴了夹鼻眼镜、梳着整齐的亚麻色头发的小个子外国同志十分严肃地询问身边的翻译,然后目光闪烁地朝这边看。这让乌力图古拉更来气。注意就注意,严肃就严肃,有什么了不起?他怕过谁?既然如此,他怕谁,凭什么怕?
“好吧,”乌力图古拉的战斗精神被轰的一声点燃。他昂起巨大的脑袋,挺起厚实的胸,扬起剑一般锋利的眉毛,自上而下,挑战地看着萨努娅,“说,你想干什么?想怎么样?”
舞曲戛然而止,因为舞池中已经没有人再去听它。人们就像松开枝头的果子似的松开自己的舞伴,慢慢拥向舞厅大门口,将两个吵着架的人儿远远围住。舞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夹鼻眼镜满脸不快地朝这边走了过来,一副要冲进顶犄的羊群中的牧羊犬的架势。但是,他晚了一步,没有阻止住战斗。
一袭红色布拉吉的美丽的鞑靼女人眼睛闪烁着,慢慢仰起好看的下颚儿:
“我想怎么样?还能怎么样?我要您兑现诺言——您的诺言。”
“什么诺言?”
“把我们的事情办了。”
乌力图古拉愣了一下,没明白,呆呆地看着胸脯剧烈起伏满面潮红的萨努娅。什么意思?“我们”是什么意思?“事情”是什么意思?“办了”是什么意思?他搞不懂。但是,他很快就懂了,明白了。那是冲锋号!全线出击,总攻开始了!嘀嘀嗒嘀嘀嗒——嘀嘀!好啊,好啊好啊,既然这样,那就来吧!
萨努娅也愣住了。她想天哪,这是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要说这句话!她只不过是生气,被对方的傲慢所激怒,不想让对方再度回到恼人的对抗上去,她就是说“去死吧”也不会说这句话的!萨努娅一下子乱了阵脚,美丽的眸子里挂上一层惊慌的霞色,下意识地往后面退了一步,好像那样一来,她就可以收回她说过的这句话。问题是,从战术的角度讲,这句话不是试射,不是密集射击,不是炮火延伸,而是双方在炮火打击之后最后的刺刀见红。她说出了这句话,就等于是射出了枪膛里的最后一粒子弹,把自己一览无余地亮在对方面前。她再也没有了弹药,这使得她越发慌乱起来。
有人为萨努娅的进攻而激动,不由自主地鼓了两下巴掌。是葛昌南,还有几个军官,他们为萨努娅鼓掌。
更多的人沉默着。现在,舞厅里更加安静,人们在等待另一方的战斗者亮出武器,开始还击,或者放下武器,宣布撤退。
“好吧。”乌力图古拉的眼睛里闪烁着被激怒的豹子般的凶光。“我的诺言,我当然要兑现。我们把事情办了。”
沉默了两个节拍,然后,舞厅中响起一片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两个战斗者被热烈的掌声吓了一跳,各自退后一步,目光从对方脸上移开,惊慌地去看舞厅。他们看见葛昌南眼里溢满雾气,用力鼓着掌,那些解开了风纪扣的军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一双手当成了一个师、一个军,拼命地拍着,中南局、华南局的领导微笑着,轻轻地拍着巴掌,年轻的英德中学、东北军政大学的女学生们,崇拜和羡慕得几乎快要晕厥过去,就连乐队和舞会的工作人员也遥遥地冲着战场这边兴奋地鼓掌。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梳着整齐的亚麻色头发、戴着夹鼻眼镜的小个子外国同志。他皱了皱眉头,不快地瞪了萨努娅一眼,转身向休息室走去。
中南局和华南局的领导基本上把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这一对新人的国际主义大团结当成开国大典遗漏下来的一枚礼炮,为他们“把事情办了”大开绿灯:如果没有新的或者特殊任务下达,乌力图古拉休假十天,打好结婚这场大战役;萨努娅把手头工作移交给其他同志,乌力图古拉什么时候返回部队,她什么时候返回工作组,如果工作组提前返回广州,她就留在武汉,等她和乌力图古拉新婚的战役胜利之后,再返回广州。
乌力图古拉一时成了同僚们共同妒忌的对象。十天哪,奶奶个熊,整整十天哪!日头出来,落下去,再出来,再落下去,再出来,再落下去,这么出来落下的整整十个回合!这期间,所有的日子都归这狗日的,没别人什么事儿,别人想管都管不上,这是什么样的好事儿啊,怎么就落到他脑袋上!乌力图古拉,他凭什么就该享受这个待遇!
“吵吵什么?没听明白呀,开国都大典了,人民都当家了,我该谁来管?还不该轮上一回好事儿?那你们说说,这命还有什么革头?”乌力图古拉得好不饶人,咳嗽一声,挺胸拿架子,眼白左抡一下,右抡一下,抡得他那些醋意兮兮的同僚们,吐血的心思都有。
萨努娅那儿遇到了一些麻烦。库切默不赞同妹妹这桩婚事。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男人,而且还是个老男人,而且还是个让汉人同化了的老蒙子,他怎么可以做萨努娅的丈夫?这太可笑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肯定地表示,萨努娅是在犯错误,犯一个严重的人生错误。
“莎什卡,”库切默看出自己已经不能阻止妹妹,万分难过,“你已经长大了,翅膀硬了,我已经说服不了你了,你就自由自在地飞吧。等你受了伤,从天上跌落下来,再回到哥哥的怀抱里来吧。”
国际主义战士库切默眼圈红了,他向妹妹张开怀抱。萨努娅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狸猫,委屈地缩进哥哥的怀里,又是鼻涕又是泪,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她的鼻涕和泪水把库切默的衣襟都给打湿了。
两天之后,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举行了他们的婚礼。结婚仪式由中南局和华南局的领导共同主持。中南局接待处的同志把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接到汉口租界区最豪华的德明饭店,拿出一把落地长窗直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