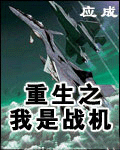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文学]我是我的神-第8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喜欢没长大的人。”乌力天扬承认,从脖颈上刮下一溜混浊的汗水。
“我也是。但你尤其喜欢那个小坏蛋。他是简雨蝉的孩子。你喜欢简雨蝉。”
“是的。”
“你一直都爱着她。”
“是的。”
“你为什么不睡她?”
“什么?”
“你们已经睡过了。你们可以继续睡。什么事情一继续,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解决。永远不会出现这种事。”
“你害怕什么?”
“我不害怕。”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睡她?你可以为自己找一个伴儿,你们一起穿过地狱。你告诉我地狱和天使的事情,我就想,它们是怎么回事儿?我想明白了,没有什么天使,天使是人们幻想出来的,这样,人们在地狱里待着就容易多了。”
乌力天扬扭头看鲁红军。鲁红军硕大的脑袋被阳光照耀着,额头上满是汗粒儿,样子十分认真。乌力天扬问自己,他幻想过吗?幻想出什么来了吗?也许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他还在进化,还在路上。
“需要买两口新锅炉。大棚里温度老上不去。”
“你为什么不睡她?你老是在关键时刻走开,这是你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关键时刻。”
“要是打点一下,再买三千亩地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简雨蝉过来了,鲁红军眯着眼看跳过鱼往这边走来的简雨蝉,告诉乌力天扬,好几个北京人打过简雨蝉的主意,可惜没能得逞,这件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但想起小时候,他们想干掉简雨蝉,最终也落荒而逃,这么一想就不奇怪了。
鲁红军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按动扶手上的电钮。简明了在远处跳起来,像狗一样四处看,然后向这边跑来,身子一斜一晃。
“你们谈吧。”鲁红军把轮椅驶开,去迎接简明了,“对了,我已经告诉办公室,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助手,你做公司副总。”
“我不做助手。”
鲁红军没有停下来,连头也没有回,让过简雨蝉,被跳蚤似的急忙奔过来的简明了推着,上了简易村道。
“为什么?”简雨蝉往红扑扑的脸上用力扇着风,“他在提携你,给你机会,你没看出来?”
“我喜欢待在有蛾子的地方。”乌力天扬说。他说的是真话。他一直在说真话,只是大多数时候别人听不懂,或者不肯相信。
“你想干什么?”简雨蝉看着乌力天扬,“乌力天扬,你怎么这样?你他妈是堆生蛾子的臭狗屎,你他妈是社会渣滓!”
乌力天扬平静地看着简雨蝉。他不明白她干嘛要动那么大的气。她可以好好对他说。或者,他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什么也不用说,只做爱。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找不到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痛恨,或者不是痛恨,而是别的什么。
“我俩是一对儿冤家。”他又说了一句真话。
“没错儿,死去活来的冤家,离不开,又搞不好。”她笑了。
“不如不做冤家。”他建议。
“什么?”她看着他问。
“给我生个孩子吧,留下点儿纪念。”他看着她。目光单纯,真诚地说。
“妄想。”她嘲笑道,就像看到了一条蜥蜴,厌恶地撇了一下嘴,“就算我给半个中国的男人生孩子,也不会给你生。”
他们彼此咬住了,谁都不会投降,谁都不会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对方。他们就像杂卤石和玉髓,一样脆弱,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一样容易受到伤害。
“这又何必?何必赌气?”
“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像二流子。你像二流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踏实。”她发现他根本没有阉掉他的野蛮。他不是当年的他了。他比任何人都结实,而且一如既往。关键的问题是,她发现他随时随地都能点燃她,“我俩就这样,谁也不欠谁。”
“好吧。”他赞同。
他们很快转移开话题。简雨蝉告诉乌力天扬。她打算带简雨槐离开一段时间,去北京看病。简雨槐没治了,这谁都明白,但没治和治不治是两回事。
“反正我现在没事儿。乌力家和简家谁都管不了她。她不能成为没人管的人。她是人,是人就得有人管。”简雨蝉脸上挂着一种淡淡的神色,说。
乌力天扬知道简雨蝉的平静是假的。问题不那么简单。不光是简雨槐,是整个儿简家。
简家的麻烦大了。简先民不到六十就发现了冠心病,人倒过几次,抢救过来了,照说装个支架能解决不少问题,报告送上去,却迟迟批不下来。老干部那么多,需要照顾的心脏越来越多,而且那些心脏是政治审查中过得了关的心脏,轮到谁也轮不到简先民,拿原则说话,给猪装支架也不能给简先民装。简先民在等死。医生说了,他这种情况不会太痛苦,说没就没了。方红藤患上了乳腺癌,切掉了一个乳房,病灶转移了,也在等死。简小川到底做了逃亡者,弃家而去,有人说他在罗马,在等大赦令下来后领取合法居留证,也有人说他死在了缅甸,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人捅死了。简明了只管自己的事,抱怨说他在简家什么好儿也没落下。
简家破落到扶也扶不起来,要说好处,只有一个——基地再也没人翻简先民的老账。谁没有做过缺德的事?谁没有昧过良心?
谁也没想到,简家的二姑娘简雨蝉现在成了简家的支柱。她回武汉,不光为了照顾简雨槐,还要照顾一塌糊涂的简家。她现在是垂死的简先民的拐杖,还是后妈方红藤的希望。她开始学着爱那个什么都失去了的老人,那个想要主宰自己同时征服他人却最终没能做到的老人。她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给简先民做了支架,为方红藤找了最好的肿瘤医生,但她不许他俩流泪。你们不该我的,就算我吃了你们十几年,不白吃,还你们。她这么对他们说的时候,口气仍然是淡淡的。
简雨蝉也爱她的生母,那个叫夏至的女人。生母终于认了简雨蝉,是在她的丈夫死了以后。生母痛哭流涕地告诉简雨蝉,她不能把她俩的关系说出来,说出来她就毁了。简雨蝉从不说她是怎么回答生母的,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生母,就像生母最先离开她一样。
这些事情乌力天扬全知道,却没有说。
鲁红军对乌力天扬不当副总的事耿耿于怀。
乌力天扬接手蔬菜养殖基地八个月,基地的基础建设推进迅速。鸡场和奶牛场扩建了,供应商代理网铺进了全市所有主要零售点,一些老大难问题,比如废水涵道问题、垃圾处理场问题、两百亩黑布李果林的烂摊子问题、国营农场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都漂漂亮亮地处理掉了。附近两个“道儿上的”团体,也让乌力天扬给收拾了。人家过去吃国营农场,后来国营农场被鲁红军吃下,变成养殖基地,他们又转吃养殖基地。乌力天扬去了,不让吃,也不让人家下岗,弄了十几个精养鱼池,让两拨“道儿上的”猴子分头侍弄,专门、伺候公款钓鱼的主儿。精养鱼池投资不大,来钱快,养殖基地这边,鱼池的租子不收,只接待公司的客人,花销多少,记上账,到年底对折结算。猴子们乐得仗义,公司也免去一笔不小的开支,两厢里皆大欢喜。
鲁红军对“道儿上的”事情不感兴趣,这种事他不耐烦做,要做也能对付。鲁红军感兴趣的是,乌力天扬怎么就把国营农场下岗职工的社保和看病的事情给解决了。鲁红军为这事没少找市里,该打发的部门没少打发,结果事情没解决,钱都打了水漂。后来听说,乌力天扬怂恿下岗职工去政府门口打着标语静坐,静坐不是一天,是持久战,带着被子和毛毯,夜里不让撤回。他们终于拦下了市长的坐驾,硬是和市长说上了话。
鲁红军吓了一跳。怂恿个屁呀,那就是处心积虑地组织嘛。鲁红军汗都下来了,破口大骂乌力天扬,恨不能开着轮椅把乌力天扬给碾死。事后一想,职工又不是他让下岗的,政府卸包袱,烂摊子丢给企业,没道理。事情反正不是他让干的。要追究起来,他也会把事情往乌力天扬头上推,让乌力天扬去顶缸。总不会把已经办下来的社保和医保再收回去,要这样,政府就别做政府了。
“你妈的不是在算计我吧?你拿我当段人贵,玩儿你那套丢手榴弹的把戏。”鲁红军心里打鼓,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狐疑地盯着乌力天扬,探过身子去,闻了闻乌力天扬身上的汗味儿,“要来这个,我对你不客气。”
乌力天扬一点儿也不在乎鲁红军客气不客气。他给鲁红军分析情况,他对鲁红军的不待见,鲁红军比谁都清楚,要是当上了鲁红军的副总,让不让,他都得把冒着烟的手榴弹往鲁红军脚下扔;他不会把手榴弹踢出去,也不会把鲁红军扑到地上用身体盖住,他会让手榴弹当场爆炸。“红旗飘飘”箭响林外,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公司的猫儿腻大了,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侵占国有资产、套用挪用资金,哪一样瞒得过副总去?那还不一炸一个准儿,炸出个人仰马翻的动静来呀!
鲁红军哈哈大笑,笑得很急促,轮椅晃动着,笑声转眼戛然而止。很认真地看了乌力天扬半天,抹掉额头上的汗,承认乌力天扬说得对,还真不能让他当副总,他当副总害人。
简明了像是激素没打好,打到尾骨上,气急败坏地问到公司来交报表的乌力天扬,他该怎么称呼他。是称呼乌力主管还是乌力准副总。过去你就挑拨我和老同学的关系,现在你还挑拨,你太没劲了。
符彩儿两颊上泛着两道冷冷的青铜色,用不明白的神色看乌力天扬,说她知道会这样,乌力天扬不会接受副总的职位。她只是想不明白,他完全可以不答应鲁红军,根本就不进公司,既然进了,为什么给个位子又不干?
乌力天扬不和简明了符彩儿费口舌,没接他俩的话,但有一个人的话他得接。
“真正征服邪恶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爱它。你是这么想的吧?”简雨蝉揶揄乌力天扬。
“那倒不是。我就是想做点儿正经事,比如捉捉菜虫子什么的,省得一天到晚泡在酒缸子和澡堂子里,迟早淹没了。”
“这么说,你什么也没有战胜,包括你自己。”
“我要战胜什么呢?”
简雨蝉看乌力天扬。乌力天扬一脸认真。没有说俏皮话的意思。简雨蝉想起来,乌力天扬打重新露头起,就没有说过任何俏皮话。但她还是想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她想知道他的真实念头。
“这回见你,真有点儿不同了。”简雨蝉若有所思地看着乌力天扬。她这么说过以后就走了,带简雨槐去北京看病。
乌力天扬去火车站送简家姐妹,肩上扛着姐妹俩的箱子,被人群挤来搡去。简雨蝉为简雨槐戴了一顶大大的帽子,帽檐拉得低低的,尽可能遮住简雨槐惊恐的眼睛。她握着简雨槐的一只手,一边推开拥挤的人群一边对乌力天扬说,这回非得把简雨槐的病治到头儿,北京不行换其他地方,不治到头儿不回来。
“你不该把孩子丢在学校。”乌力天扬说。
“那怎么办?我爹和方红藤病入膏盲,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孩子跟精猴子似的,你给我带?”简雨蝉不耐烦地说乌力天扬,“给你说这个等于对牛弹琴,你谁也不相信,就连你自己,也只偶尔相信自己一次,那还得看天气阴晴的情况。”
乌力天扬想对简雨槐说,她说得不对。他并非她说的谁也不相信,连自己都不相信。他是相信的,而且越来越相信。正因为相信,他才会回到这座城市来,找回他失去的相信。但他没说,没把那些话告诉简雨蝉。
火车开走了,简家姐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乌力天扬逆着人群往外走,隐隐约约感到心口灼疼。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吃晚饭的时候,萨努娅看乌力天扬没精打采地往嘴里扒饭。严肃地对他说。
乌力天扬被萨努娅说的这句毛主席的话给逗笑了,差点儿没让饭粒噎着。
“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乌力图古拉皱了皱眉头,伸出筷子指点菜碗,“这碗烧白是左还是右?这碗豇豆呢,是左还是右?不是扯淡嘛!它们就是猪肉和豇豆,吃了有营养,拉了能做肥。”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阶级就不吃饭了?哪个阶级他不吃饭?哪个阶级宣言上说了他们就想当饿死鬼?打上烙印不还得生活,还得吃饭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萨努娅,你有完没完?”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乌力天扬嘴里嚼着米饭,心里想,这话说得多在理啊。
第三十九章 必须搜集更多的火柴
一旦忙碌起来,生活就变得像生活了,好比一头驴,有鞭子在后面抽着,驴就像一头驴了。
乌力天扬喜欢这样的忙碌。这样的忙碌让他老有汗出,可以大量喝水。他觉得自己恢复得非常好,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就像一匹来自罗德河谷的巴伐利亚温血马,身体的发育越来越适合用来进行杂交了。
蔬菜养殖基地在武汉北部的黄陂县,离家远,中间隔着长江,乌力天扬回家一趟比去一趟上海还难,有时候开着基地那辆破烂不堪的“江陵”面包,咯叽咯叽地过江回家,要是车在路上拉了缸或破了胎,到家准得天亮。
童稚非不爱给乌力天扬开门。童稚非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说乌力天扬,你就不能不回来。乌力天扬不能不回来,他越来越喜欢小时候睡过的那张床,他还要帮助萨努娅对付乌力天时的褥疮。乌力天时终于生褥疮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植物人,过了二十年才生褥疮,这是奇迹。
乌力天扬成了乌力家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