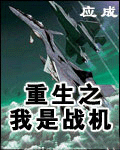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文学]我是我的神-第8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乌力天扬付了五十三块二毛钱的电话费,他月薪的十八分之一。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没有癌症治疗费那么复杂。现在他要做的是如何节省开支,不能再从狙击步枪中一颗一颗地往外抠子弹了。他打算在冬天来临之前,关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就像关闭不起任何作用的大门。把风关在外面。灰白色的风。
一看见汪百团手里那卷脏兮兮的钞票,乌力天扬就出了手。汪百团根本禁不住乌力天扬的拳头,人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植钵机上。
“你这个该死的没长进的毒贩子!”
汪百团仰身躺在那儿,痛苦地喘着气,爬起来,撑着地站起来,朝门口歪歪斜斜地走去。走了几步,想起手里的那卷钞票,把钞票丢在地上,冲钞票吐了口血唾沫,说:
“找汪大庆要的。高利贷,三分的利。她攒给孩子买钢琴的。要嫌不干净,你自己退去。”
乌力天扬像个傻瓜似的愣在那里,脖颈上的青筋突显着,怎么也下不去。他感到强烈的头晕。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滠水河边的草地上坐着喝酒。两瓶黄鹤楼,一碟霉千张,一簸箕黄瓜。一群群的蠓虫不断地飞过来,往他们脸上和酒瓶子上扑。他们谁也没有提二十年前发生的事,那支点32的左轮手枪和大军山少管所,也没有提那卷肮脏的钱票。月色中,几只被称作斑鱼狗的翠鸟在河水里忙碌着,黑色的翅膀发出瓦蓝色的暗光。
“百团,等卢美丽的病治好了,你去治眼睛吧。”
汪百团不说话,斜着眼,黄瓜蘸进霉千张汁里,转一个圈,咬一口,再咬一口。
“你治眼睛,我供你,咱们把眼睛治好。”
汪百团伸长脖子,把嘴里的黄瓜咽下去,拎起酒瓶,仰头灌了一口。
“还有,你得成家,成个家了。”
汪百团吸了一口凉气,是被酒杀的。他的半边脸肿着,嘴角的淤血一时半会儿不会消,这使他像是长了三只眼睛。月光下,他那只坏了的眼睛显得非常亮。
“你不能老和野店里的姑娘混。她们有病。你这样,混不了两年就把自己混成一堆烂肉了。”
“谁不脏?谁没有病?”汪百团瞧不起地瞪了乌力天扬一眼。
“我没说她们脏。”乌力天扬解释。
“你不明白她们。她们心眼儿好,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过了好一会儿,汪百团说。
论到乌力天扬不说话了。他在想那些心眼儿好的乡下姑娘。她们有着结实的胳膊和野性十足的眼神,笑起来咧着大嘴,前仰后合。蠓虫找到了规律,飞来飞去的像跳祭祀舞。部落里的情况也会是这样,鹿脯烧熟了,猎鹿人为什么还不回来,他们遇到狼群了吗?
“她们都是些朴实的姑娘。”过了好一会儿,乌力天扬想明白了,承认说。
“好姑娘。”汪百团纠正道。
沁人肺腑的空气中。有一道暖流涌了过来。蝈蝈的叫声在深秋到来之前将是滠水河边最后的生动。
乌力天扬突然笑了,在月光下无声地咧开嘴。他想起了一件别的事。
“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看《人体解剖学》的事儿。”
“怎么不记得。你从家里偷出来,把我们召集到防空洞。”汪百团仰头灌了一口酒,头没动,伸长脖子,用那只好眼睛望着天空中的星星,“那个时候,我们最佩服天赫,可你的主义最多,跟他妈星星似的。小时候,多好啊!”
“我是害怕,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别人在哪儿,不知道这个世界安全不安全。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乌力天扬羞涩地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什么地方走岔了道儿,没有走回丛林里,所以才没长大。”
汪百团笑了,不知意味着什么,叹了口气。有一段时间他们没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刚才可能真的会打断你的腿。”
“你做不到。我不会让你打断。”
乌力天扬扭过头来看汪百团。黑夜未必不能看到,白天未必能看到。这一点他没有想到。
“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让我觉得做人实在。我想死,早不想活了。可我没死,死不了。我活着,能干活儿,有饭吃,有好姑娘睡,还能给卢美丽弄钱,我喜欢这种感觉。跟着你,我觉得踏实,我就这样活着。你呢?”
“什么?”
“为什么回来?你完全可以不回来。”
“错过了。”
“错过什么?”
“你想过没有,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打心眼儿里敬重——安静地出生、尊严地死去、至死相爱,可是,我们总是错过它们。我们在错过中经历战争、灾荒、动乱、革命、运动。我们说它们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这有多么荒谬。可生命不会在想撒手不管的时候就终止,我们注定了要在荒谬的时代中经历。能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生命它有自己的性子。那么。那就回来,万劫不悔地回来!”
瓶子里最后一点酒见了底,簸箕里还剩下半截黄瓜。汪百团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下了河堤,朝河里走去,他在那里站住,回过头来。
“我不会再胡来,但你也别管我和姑娘们的事。而且,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你并不适合她们的胃口。”
汪百团衣裳没脱,直接坐进河水里。
乌力天扬从草地上爬起来,脚上的鞋甩到一边,没脱衣裳,摇摇晃晃下了河堤,朝河水深处走去。
第四十章 下到水里当一条鱼
孩子不是简家塞给乌力家的,是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在路上捡的。
孩子在学校惹了祸,用石头把教导主任的脑袋给打开了花。学校让家长去解决问题,简家去不了人,学校就把孩子给送回来了。
简先民的心脏病气得犯了好几次。方红藤只惦记着怎么把药再配回来,根本没有力气追剿小肇事者。简明了正忙着离婚,躲前妻躲得整天不回家。孩子没人管,乐得从家里折腾到外面,有一天在操场的检阅台下睡着了,那晚下雨。人泡在泥水里还呼呼地睡,愣是没被浇醒。
乌力图古拉牵着泥猴似的辨认不出模样的孩子。心疼得直抽搐,站在操场上大骂简家缺德,还歪着半边身子非要去收拾简先民。
碰上那天乌力天扬回家,才把事情解决了。
乌力天扬好些日子没回家,他和汪百团在黄陂承包了百十亩菜地,雇了十几个四川人种菜,让农民工胡纠纠管着,用种菜的收入供卢美丽治病。乌力天扬脑子好使,看着什么菜时兴。什么菜市场上没有,专种什么菜,吩咐不用化肥,用大粪和河泥,不用农药,用草木灰杀虫子,还给菜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村里菜”,市场上很受欢迎,菜价比大棚菜高出两三成。
乌力天扬那天回市里收钱,再去肿瘤医院交钱。顺道回家给老干部们送柿子椒,路上碰上乌力图古拉、萨努娅和孩子。乌力天扬想也没想就说,领回家去吧。
乌力天扬第二天去了寄宿学校,找校方谈孩子的事。学校问乌力天扬,你是孩子什么人?乌力天扬说,算是叔叔吧,来替孩子赔礼,替孩子认罚,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怎么罚都行。学校说,礼是肯定要赔的,罚是肯定要认的,但不是你。孩子的监护人是谁让谁来。监护人来不了,谁生了孩子谁来。谁生了孩子来不了,直系亲属来。叔叔算什么?
乌力天扬还是给简雨蝉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一五一十,把孩子的情况给简雨蝉说了。谁知简雨蝉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好半天没有出声儿。等乌力天扬喂喂地叫过两声,那头把电话挂断。再打过去,打出警报声也没人接。
乌力天扬不明白简雨蝉什么意思,是不相信他的话呢,还是急赶着去火车站买票回武汉?凭直觉,两样都不像。乌力天扬想不明白,苦笑一下,去柜台交电话费,出了邮局。
孩子被带到蔬菜养殖基地,高兴坏了,啊啊地叫,像一头小野兽,他说要爬粪堆、下干池塘、骑狗,谁也不许管他,谁管他他就踢破谁的脑袋。
汪百团直皱眉头,说乌力天扬,破孩子,又不是你的私生子,领到这儿来干吗?怎么带?不是添乱吗?
乌力天扬没听汪百团的,孩子带在身边,想怎么玩儿都行,敞养。
孩子警觉得很,认准乌力天扬是一头阴险无比的丛林蚺,合计着要吞掉他,老和乌力天扬保持一定距离。
有一天晚上,乌力天扬从睡梦中疼醒,醒来闻着一股焦臭味儿,伸手一抹,鼻子给烧出一串大水泡。是孩子干的。孩子一直在暗中算计乌力天扬。他打算从乌力天扬的鼻毛开始,一样样收拾他,按照计划,半夜起来摁着了气体打火机。
乌力天扬从杂物间里把孩子捉出来。孩子紧张得要命,牙咬得咯咯响,瞪着一双小眼睛看着乌力天扬,因为恐惧,一张小脸儿显得十分丑陋。
乌力天扬想揍孩子一顿,像当爹的揍自己孩子那样揍。这么想着,拳头攥紧,气提到胸口,可看到孩子恐惧的眼睛,突然心软下去,气头子无缘由地消失掉。
两个人一前一后,匍匐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精养池塘爬去。孩子有一阵儿跟不上,想站起来,被乌力天扬狠狠地摁在地上,摁了一嘴泥。乌力天扬拿眼睛瞪孩子,示意他别出声。乌力天扬的目光寒冷得很,在月光下亮得让人心悸。孩子打了个寒战,没敢出声。
孩子蜷在瓜地里,冷得直哆嗦,没看见乌力天扬是怎么把鱼弄上来的。一条气势汹汹的大白条,差不多两斤来重。他们很快离开了那个地方,找地方收拾战利品。
“知道不知道,你他妈真让人讨厌。”
“看起来你挺聪明的,可白聪明了,连在瓜地里爬都不会,讨厌都比我小时候差多了。”
“你骗人!”孩子生气。
鱼很快烤熟了,香气扑鼻。孩子很快吃掉大半条鱼,样子像贪吃的小浣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爱得很,而且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响亮的饱嗝儿。乌力天扬坐在那儿,仰头眯缝着眼看天上。滠水河汩汩地流淌过去,有各种昆虫在草丛里了无忧愁地鸣叫。
“我妈也喜欢看星星。”
孩子悄悄地移动着身子,靠近乌力天扬。乌力天扬看了孩子一眼,把烘干的衣裳取过来,扑打了两下,帮孩子穿上。
“我妈咬我爸。她叫我爸去淹死。”
“别说大人的坏话。”
“我妈是婊子。”
“不许这么说。”
“是我爸说的。”
“那也不许说。”
“我妈就是婊子。她把我爸踢得站不起来。婊子才这样。我喜欢做婊子。”
孩子仰天向后倒去,重重地跌躺在草丛里,腿扬得老高,像做广播体操的青蛙。乌力天扬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巴掌,把巴掌在裤腿上蹭了两下。
“你妈看的不是星星。”
“那是什么?”
“她看她自己。”
“怎么是她自己?”
“有时候,她不想待在地上,想去别的地方。她想去别的地方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她想要找到的东西。”
“我知道。我也不想待在地上。我想下到水里去,当一条鱼。”
乌力天扬笑了,扭头去看孩子。
“你同意我当鱼?”
“让我想想。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你肯定?”
“你得答应我,不许踢人的脑袋。”
“嗯。”
“不许做婊子。”
“嗯。”
“要疼女人。”
“包括妈妈吗?”
“她是第一个。她是最美的鱼。”
“明白啦!”
孩子很快跑开,去河边玩水。他把脑袋埋在河水里,像一头去水底寻找同伴的水獭。
乌力天扬从后面看孩子,即使孩子不能变成鱼,至少也能和海水成为好朋友。孩子该是一切事物的朋友,而不是别的。
过了几天,鲁红军打电话过来把乌力天扬骂了一通,说乌力天扬拿着他的工资跑自己家保姆的事,不光工资,还有时间,还有汽油。乌力天扬知道是谁告的密。有时候就是这样,告密者永远都是告密者。但他没有提亲戚的话,只说这件事他必须管,工资可以停发,汽油费另算,但车得用,要不跑一趟武昌得五六个钟头。
鲁红军倒是没在这件事情上纠缠,让乌力天扬别拿辞职威胁他,坦率地说,蔬菜养殖基地需要乌力天扬,没他玩儿不转,叮嘱乌力天扬抓紧度假山庄装修的事。他几个朋友已经说了,今年春节不去澳门赌了。太累,就在度假山庄里等着。打点儿小牌。
“你还是放不下简雨蝉。”鲁红军在电话那头说。
“孩子得有人管。”乌力天扬看看屋外。外面的风很大。孩子在小路上歪歪扭扭地推一辆两轮车。
“气象预报说今年上游的雨量大,得准备点儿麻袋石头。”
“长江是中央的长江,你管得了?上面有葛洲坝挡着,孙文大总统设计的,你就放心吧。要不,我让符彩儿去你那儿,帮你把小杂种带着?”
“不用了。我能行。”
“我说,你真该把她睡了。”
乌力天扬知道鲁红军说的是谁。听得出来。鲁红军是真心的,他的口气甚至有些伤感,和平常的他不一样。乌力天扬没有接鲁红军的话,先把电话挂掉,起身去屋外,叫汪百团去胡纠纠那边看看菜地的情况。再叫孩子把车放下,和自己去检查蔬菜大棚。
孩子像鸟儿一样飞过来。
风大了,天阴得厉害。
雨季没有和谁商量就来了。
大雨一连降了十几天,蔬菜大棚里的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转着,棚顶上挂着大滴大滴的水珠子,钢结构上长出一层茸茸的绿霉。先是奶牛场断了饲料,运牛草的车过不了九丈堤,那里的湖水漫上来。路基全泡垮了。接着是养鳝池、牛蛙网箱和精养鱼池。附近几片荒湖吃足了雨水,一下子丰腴起来,湖水倒灌进池塘里,野鱼家鱼乱了阵线,鳝池里的鳝鱼全跑光了,牛蛙死了不少,塘鱼跑了几十万斤。黄花畈一带的油桃林和黑布李林也积了水,排水管道堵塞住,十几台水泵没日没夜地轰鸣,积水还是排不出去,出现了果树烂根的情况。
乌力天扬嗓子都喊坏了,养殖基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