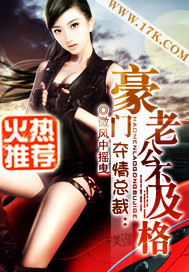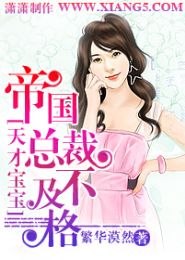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羽这个举动被称为“挂印封金”,佳话流传了上千年,但罗贯中笔下皮里阳秋,似乎对关羽并不那么友好。在后面的文字里,利用“挂印封金”给读者剥开了关羽虚伪的一面。
且看,第二十七回中,曹操率人追上了关羽,准备送给关羽黄金一盘,关羽说:“累蒙恩赐,尚有余资。留此黄金以飨将士。”——原来关羽并没有把曹操给他的所有的钱都“封”了,还是带走了一部分,这应该是罗贯中想告诉我们的吧。
也是在这一回中,关羽连连过关斩将,到了第五关时,秦琪引军出问:“来者何人?”关羽的回答是:“汉寿亭侯关某也。”——咦?不是把汉寿亭侯的大印留在了许昌,表达自己不受曹操所封的心意了吗?怎么又自称为“汉寿亭侯”了呢?
看到这,我就想笑,罗贯中实在是太“坏”了,明着不敢,暗地里还是对关羽不大感冒啊。
可怜的韦小宝
在金庸的小说人物中,最可怜的莫过韦小宝了。
其他人物,比如郭靖,虽然憨厚到了虚伪,但终于博得了一代大侠的名声;再比如岳不群,虽然耻辱地死在了武功最差的仪琳手里,但终于为汉语增加了一个伪君子的代名词。好的好到底,坏的坏到底,都算各得其所。惟独韦小宝,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又坏不到极至,让人不知所以。
这里不是想分析小说里的人物,比如这个属于扁平人物,那个属于圆形人物等等,而是说他们在金庸言谈中的地位。说韦小宝可怜,是因为在金庸的嘴里,他也是变来变去的。
最初,金庸写了《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这样评述自己对韦小宝的态度,“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
那时,金庸对韦小宝是喜爱的。谁会把自己不喜爱的人当作朋友呢?
后来,大约2001年吧,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金庸又说了类似的话:大家要学习郭靖,不要学韦小宝。
前几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金庸又提起了韦小宝,说真的想过最终让韦小宝七个老婆逐个离他而去,因“这厮实不应可享尽齐人之福”,“小朋友读到会不好”。
就这样,两三个起落,韦小宝在金庸嘴里便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至于从前金庸说过的韦小宝的“义气”之类在现在他当然不会提起了。
其实,韦小宝还是那个韦小宝,贪玩好色,但义薄云天,不过金庸的处境不同了,自然和韦小宝生分了。
从前的金庸,也是一江湖人物,为了增加报纸的销售量,不得已操刀玩起了武侠小说,自然和同为江湖人物的韦小宝多亲多近。而现在,金庸靠近了主流,处了庙堂之高,抛弃个把从前的朋友在他看来实在没什么不正常的。
从这一点上说,金庸现在的性格和另外一个江湖人物宋江有一些相似。那就是,当着水浒好汉的面绝对不会打开自己的木枷,一旦四下无人,自然落得个轻松自在了。
他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打紧,可苦了韦小宝了。如果韦小宝泉下有知,当和七个老婆抱头痛哭一场吧。
三十六万六的一顿饭
有人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饭庄西安分店一桌饭花掉了三十六万六千元,听了这个消息,我很吃惊,第一反应是“假新闻”。我一顿三百六十六的饭吃过不少,对三十六万六的饭实在没有概念,于是好奇。读了这条新闻,又看了后来的跟踪报道,判断一下不像是假新闻。新闻里说,一个梁姓商人要吃满汉全席,便和店主商量出这么一个价钱。怎么做,当然店主说了算。
于是,店主把饭做出来了,梁先生吃了。
店主做得很细心。在CCTV…12频道《新闻夜话》主持人的追问下,店主详细说了其中一些菜的做法,比如“有一道菜我们叫仙鹤指路,这道菜就是这个绿豆芽。这个绿豆芽是咱们精选的豆芽,我们的师傅就是用咱们修手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修手表的师傅不是经常戴个放大镜吗,卡在眼睛上,拿一个特制的金属丝把豆芽一点点贯穿掏通,往豆芽菜里面放什么,里头灌的是燕窝茸、鸡茸。这才是个鹤的翅膀,我就说光这个鹤的翅膀就这么难做。这道菜做出来您说是多少钱,一万二。它的仙鹤翅膀就这么难做,它还有头呢,还有脚,还有身子,就是说还有旁边的整个造型……”
说得够详细了吧?但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一万二到底值在了什么地方。
我不喜欢这样的铺张,但说实话,和这铺张比起来,我更不喜欢的是CCTV那个主持人咄咄逼人的语气,比如这样的对话:“……主持人:你是说杀掉一百条鲤鱼,把它们的须子拿下来炒成一盘菜,然后只是动一筷子,只是欣赏一下这个菜就扔掉了。嘉宾(店主):这是一种饮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饮食文化。主持人:这是哪个国家的饮食文化?”
如果遇到事情一定要有个态度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说,我不喜欢,但实在看不出有谁受到了伤害。我不喜欢是我的事,吃的人喜欢——而且买单的时候明确知道自己没有受到欺诈——饭店有了利润,国家收到了税款(当然前提是店主没有偷税),真的不明白CCTV的主持人为什么在对话的时候像是在审问犯罪嫌疑人。
看了网上的评论,发现有很多人大骂梁姓商人,难道仅仅因为他吃了一顿昂贵的饭?花自己的钱吃饭犯法吗?我不愿相信会有人这么想。莫非有钱人把钱都装到瓦罐里,埋在地下才算正常?至于说到浪费,说到奢侈,只要人消费得起,好像也没踩着谁的脚。话说回来,不多消费怎么拉动内需呢?
我最后的态度是,没谁做错什么。如果梁先生的钱真的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可能来路不正,或者店主进行价格欺骗,也和这顿饭本身没关系。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CCTV的主持人说:“我们认真地做了一次换算,很多观众说,就是吃金子也吃不了三十六万六千元人民币。根据今天上午上海黄金市场开盘的交易价钱,那一天的一桌饭菜,大概等于吃了四公斤的黄金。”我实在搞不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假如我有很多很多钱,只要我愿意,一顿吃上四十公斤黄金,好像也没谁管得着。
黄金时代
赫西俄特(Hesiod)在《工作与时日》中告诉我们,人类有五个时代,即、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现在的黑铁时代。比诸这个,对于内地中文网来说,1998年前的日子完全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个时代了。
古希腊传说这样描述黄金时代:无数的恶魔还不曾散播于人间,所以人类是天真而快活的;没有法律,而奸邪不生,刑罚不用;无强寇,无小窃,也没有什么刀枪盔甲之类;地不
种而生五谷,河中流着的是牛乳与酒;四时皆春,橡树中流出蜜来。
四五年前的内地中文网络,无门户之乱耳,无商务之劳形,虽然没有希腊传说中那样无忧无虑,起码算是轻松、自然——除了上网费用巨贵外,一切都让人怀念。
聊天室的多种功能都是后来由技术高手们逐渐添加的,最早的聊天室除了说话(敲字)外没有任何功能,想跟谁说话都要先打出对方的名字来。现在,网友们进入像(infodaily/chat/)这样的聊天室会开玩笑说它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际先进水平,那时候的聊天室都是这样的,无一例外。
当时,虽然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起一些“耐火砖”、“土豆”等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但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并没有谁真的忌讳将真名字说出来,害人之心全没有,防人之心一点无。甚至网友聚会的时候还留下了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打印出来,做成通讯录。1998年世界杯期间,瑞得聊天室108个网友聚会,创造了空前记录,通讯录自然也是厚厚一叠。后来西安古城在线的网友居然有486人参加——现在超过六个人都懒得去喽。
归根到底,在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多数人只把它当成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有什么其他——商业上的、个人名利上的等等想法,所谓无欲则刚,人没所求的时候自然放得比较开些。
比如我最早进入的BBS,四通利方(现新浪网)体育沙龙(后来有了金庸客栈、读书沙龙等等)的网友们就是这样。我是1998年初到体育沙龙的,前几天和陈彤(网名GOOOOOOAL,现在居然是新浪网的副总裁了)聊天,他说我算“黄埔二期”的,一期自然是他和老榕、北京厨子、从良匪兵、黄鱼@西湖——黄鱼@西湖是当时拥有个人主页的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他的个人主页(happycast)早于一切门户网站——等人。那是中文网最早的BBS之一了,集中了海内外无数的球迷。
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催生出了新浪网,从那时候起,中文网进入了白银时代,也就是许多网虫变成了CXO,开始了辛勤耕耘的年代。至于天下大乱、怪招迭出的青铜时代,则是门户林立、电子商务泡沫兴起之后的事了。
当时四通利方体育沙龙的很多网虫,后来都被称为网络写手,比如韦一笑、李寻欢、五朝臣子等,但在当时那里的人们只是探讨足球,虽然经常吵得不亦乐乎,但见了面后便都浇灭了心中的块垒,一笑便泯去了恩仇。
逐渐地,人们发现了网络的“自由”,于是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网络会给国家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等等。对个人来说,我甚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这么计算:如果人的寿命有八十年,那么二十岁上网,等于生命延长了六十年,变成一百四十岁了。
将网络算作生命的一部分,是黄金时代许多网虫的通病,到后来才发现,网络上除了信息丰富一点儿、交流便捷一点儿、检索容易一点儿外,什么都不是。如果说,现在是网络的黑铁时代的话,等于是说网络回落到了它应该的地位,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工具或者玩具,而不能代表生活本身,许多在网下得不到的东西,在网上同样得不到。
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第四十一个》中的尼古拉耶维奇这样阐述黄金时代:哦,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不觉得自己同全世界处于敌对的地位,而是你完全溶化到这样的宇宙的大自然里……它的呼吸就是你的呼吸。
现在没人这么天真了,不过想一想,还真是怀念那个年代,那时——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
丢在哪儿了
人无信不立。这话是古人说的,但古人做得怎么样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也有一些类似尾生为了守信等人不惜身死的故事告诉我们祖宗们做得不错,但这样的故事总有点儿血淋淋的,听上去很不舒服。
从两年前高考作文的出题者把“诚信”做了主题后,呼唤诚信的声音就不绝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呼唤什么就意味着缺少什么,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是恐怖的社会,比缺少粮食更
让人毛骨悚然,但好像还没人问一声,我们的诚信到底丢在哪儿了?
近来重读《三国演义》,在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里看到了这么一段:“(夏侯)渊急使人到黄忠寨,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次日,两军皆到山谷阔处,布成阵势。黄忠、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式,各不与袍铠,只穿蔽体薄衣。一声炮响,陈式、夏侯尚各望本阵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尚带箭而回。”
虽说是交战双方,但黄忠在交换俘虏时放冷这种毫无诚意的做法也实在让人心寒,如果这种作风一直遗留到上个世纪并不幸流传到全世界,估计两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死亡率最高的兵种应该是卫生兵,更不要说还优待什么俘虏了。
不用说昏庸的阿斗做皇帝,单是有黄忠这样不存诚信的上将军,蜀国灭亡丝毫不值得同情。
如果是黄忠只是一介武夫,不足以代表古人的话,那么看看知识分子的说法吧。对于三国的这一情节,李贽(据研究为他人托名,不是真的李贽)的评论是“老黄通”,毛宗岗的点评是“多换了一箭,却是便宜”,李渔的说法则是“人以换回,又多了一箭,受次小便宜”。从托名李贽这样的大学问家的人到李渔这样的通俗文艺家,赞扬的居然都是黄忠,并且对遭箭的夏侯尚语带嘲讽,谁要说他们都是在意诚信的人,我是不会相信的。
从武将到文人,千年下来就这么一个德行,令人一叹。
从三国再往前很多年,有个宋襄公,不击半渡之敌军,不打没排好队伍的对手,不抓白头发的老人做俘虏,不杀死对方已经受了伤的士兵,至今有人讲历史的时候都要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愚蠢的”三个字,当时他的手下大臣公子目夷这么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我怎么都觉得宋襄公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但他已经被嘲笑了几千年。
莫非那么早我们就丢掉了那些东西?
经历了风雨没有了彩虹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这是十年前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歌,李宗盛的,有人说听起来有点儿像二人转,天天哼哼这个旋律,可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他唱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歌的后面还有谈恋爱和感叹青春的意思,就把它当成了和李宗盛其他流行音乐一样,只是为了取悦大众而炮制的“产品”而已。
十年后的今天,我虽然不否认李宗盛的这歌依然是产品,是商品,是所谓媚俗的典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它击中了我,一个俗人。
我是一个曾经对罗大佑无比热爱的俗人,我多次说过,我们成长的年代,除了崔健,只有罗大佑。崔健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