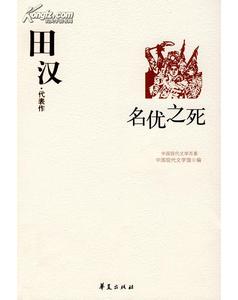矛盾文学奖提名 张居正(全) 作者:熊召正-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玉娘退了出去。
高拱问高福:“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
高福答道:“老爷,这位玉娘就是上次邵大侠来京时带来送给你的。”
“哦!”
高拱这才记起那档事情,邵大侠走后,高福把玉娘安顿在一处尼姑庵里,每日里有两个小尼姑照顾她。高福曾向主人几次提起,要他抽机会见见玉娘。高拱总是推辞,一来这些时朝廷接连发生大事,的确忙不过来;二来高拱也担心京城人多嘴杂,在这非常时期,不要招来物议,事情就这么搁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玉娘却在家中出现了。高拱顿时恼下脸来,斥责道:
“高福,你小子胆子也真大,竟敢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高福急忙申辩:“老爷可不要错怪小人了,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
“夫人?”高拱一愣,“我那老婆子,她如何知道?”
“是,是小人告诉她的。”
高福于是讲出事情经过:昨日,高拱离家后,夫人把高福找来,说道:“我看老爷这些时不但忙得脚不沾地,眉心上攒着的那两个疙瘩也总不见消除,天晓得他有多少烦心事。你跟了他多年,主人并不把你当奴才看,而是情同父子。你总不成眼看老爷活得如此艰难,而不帮着他找些子快乐。”高福听了也有同感,他冥思苦想一阵,终于鼓足勇气把玉娘的事向夫人禀告了。夫人一听,不但不生醋意,反而要高福把玉娘领回家来让她看看,高福领命,今日把玉娘领进家门,夫人接见说了会子话儿,竟对这玉娘十分地喜欢,便吩咐留在家中侍候老爷。
听罢原委,高拱笑了起来,说道:“我家这个老婆子真是开通,居然给老公拉皮条,既是这样,就叫玉娘进来吧。”
高福转身出门把玉娘领了进来,又把食盒子里的酒菜拿出来摆好,这才退了出去,小心把门掩好。
高拱家中的书房同客厅一样大,平素夜里只点一盏宫灯,光线不甚明亮。今夜里书僮按高福的吩咐把书房里的四盏宫灯全都点燃,因此屋子里明亮得如同白昼。借着亮炽的灯光,高拱仔细端详坐在眼前的玉娘:只见她穿着一袭素白的八幅罗裙,腰间数十道细褶,每一褶一道颜色,搭配得既淡雅,又别致,裙边一二寸宽的地方,滚了大红的花边,看上去很醒目,让人产生愉悦。也许是独自面对高拱的缘故,玉娘有些紧张,微垂着白腻如玉的鸭蛋脸,只让高拱看到一个梳裹得整齐的用金银丝线挽成的插梳扁髻。
“玉娘。”高拱喊了一句。
“老爷。”
玉娘抬起头来,只见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脉脉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猩红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露出些许的调皮与天真。面对这么一位不胜娇羞的美人儿,高拱不免心旌摇荡,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玉娘的脸蛋不挪开。玉娘被看得不好意思,香腮上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说:“老爷,奴家给你斟酒。”
“好,你陪老夫喝一杯。”
高拱说着,趁玉娘挪步过来斟酒的当儿,伸手把她执壶的手摸了一把,他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遭到电击。在官场同僚中,高拱以不近女色闻名,可是今夜里,他也忍不住失态了。
“老爷,奴才敬你这一杯酒。”
玉娘双手举着酒杯,半是羞涩半是娇嗔地送到高拱跟前,高拱有些情不自禁,说话声调有些异样:“不是说好,你陪老夫一起喝么?”
“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下一杯奴家再陪你喝。”
“好,那就一言为定。”
高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玉娘又斟酒两杯,两人碰杯对饮。一杯酒下肚,玉娘的脸庞更是艳若桃花,光泽照人。高拱也是神采奕奕,兴致大发,他吃了两筷子菜,问玉娘:“你和邵大侠是何关系?”
玉娘答道:“奴家原籍在淮北,十一岁因家境没个着落,被父亲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边的玉箫楼,认了一个新的干妈。那干妈便教我弹琴唱曲,吟诗描花。五年下来,倒也学了一些糊弄人的本事。干妈本是把我当作摇钱树来栽培,指望日后靠我腾达养老。
那一日,邵大侠逛到玉箫楼来,不知谈了什么条件,就把我赎出身来,并把我带来北京,讲清楚了让我服侍老爷。“玉娘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经历,这倒更引起高拱的怜爱,问道:“你那干妈可还疼你。”
“疼是疼,可是管教也严。”
“怎么个严法?”
“我进玉箫楼,从没见过一个生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应酬。”
“你那干妈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大鱼。这不,邵大侠就上钩了。”
高拱说罢,先自大笑起来,又把玉娘斟上的酒饮了一杯。玉娘也赔着笑了。
高拱接着问道:“邵大侠是怎么跟你说的。”
玉娘两颊飞红,抿着嘴唇不语。
“说呀!”高拱催他。
“邵大侠说,他给我寻了个除了皇帝之外的天底下最显赫的人家,让我来当偏房。邵大侠说的这个人,就是老爷您了。”
玉娘细声细气说完这段话,羞得无地自容,伸出两支玉手捂住发烫的脸。这副忸怩不安娇滴滴的样子,越发逗得高拱开心。这时他已春心荡漾,很想上前把玉娘搂进怀里亲她一亲,但他还是克制住了,又寻个话头问道:
“你干妈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好多啦,大凡堂会上流行的曲子,奴家都会唱。”
“啊,那你就唱它几支,给老夫佐酒。”
“奴家遵命。”
玉娘答应,出门去拿了一张琵琶进来,调了调弦,问道:“老爷要听哪一支?”
高拱平素极少参加堂会应酬,就是偶尔参加,也无心留意曲牌,让他点唱可真是难为了他,因此答道:“你就捡好听的给我唱来。”
玉娘点点头,敛眉略一沉思,便轻挥玉指拨动琵琶,随着柔曼如捻珠般的弦声,玉娘唱道: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如果单只说话聊天,高拱只把玉娘看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胚子。及至玉娘开口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俱佳的豆蔻佳人。听她慢启朱唇刚一开腔,高拱便有三分陶醉。他索性闭了眼,静听玉娘的一曲妙唱。那声音媚甜处,让人可以感觉到怀春少女的似水柔情;娇嗔处,让人如置画楼绣阁,听红粉佳人的打情骂俏;紧凑处如百鸟投林,飞泉溅玉;悠扬处如春江花月夜的一支洞箫。字正腔圆,珠喉呖呖。高拱听得痴了,玉娘一曲终了,他尚沉浸其中。
“老爷,奴家献丑了。”玉娘说道。
高拱醒过神来,连声叫好。望着明眸皓齿的玉娘,不禁又蹙了蹙眉头,说道:“你方才这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只是过于伤感。看看,曲子唱完了,你的眼中犹自泪花闪闪。”
玉娘怀抱琵琶欠欠身子,歉意地说:“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唱了出来,没想到惹得老爷不高兴,奴家赔罪了。”
高拱没想到随便说一句,竟引起玉娘如此紧张,便故作轻松地一笑说道:“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极少听人唱曲子,你却是唱得真好,你再唱下去,唱下去。”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如何?”
“随你。”
玉娘又不经意地拨了一下琵琶,定定神,又唱了一首:
提起你的势,笑掉我的牙。
你就是刘瑾、江彬,也要柳叶儿刮,
柳叶儿刮。
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
我的哥罗!你休当玩耍,
如今的时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
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
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
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
唱这支曲子,玉娘好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忧戚一扫而空,换成逗人发笑的顽皮。二八佳人学街头耍把戏的那种油腔滑调,这悬殊的反差本身就很出彩。因此把高拱逗得胡子一翘一翘地大笑,笑声止了,又满饮了一杯酒,高拱问道:“这支曲子叫啥名字?”
玉娘答道:“回老爷,叫《锁南枝》,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
高拱眼眶里闪过一丝不易捉摸的光芒,说道:“老夫听到了,你唱的曲词儿中提到了刘瑾、江彬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
玉娘摇摇头,答道:“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后才学会的。”
“啊,跟谁学的?”
“也没跟谁学,那一日,在两个小尼姑的陪同下,到泡子河边看景儿,在一个小书肆里买回一个唱本儿,上面有这首词儿。”
“既是唱本儿,里头肯定有许多的词,你为何单单选中这一首来唱?”
“这……”玉娘欲言又止。
高拱追问:“这里头难道还有什么可隐瞒之事?”
这一问,倒把玉娘唬住了,她连忙答道:“老爷言重了,奴家自到京城,日日夜夜都想着老爷,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拣了这首词儿来唱,原是想讨老爷的欢心。”
“此话怎讲?”
高拱说话直通通的,口气很硬。这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养成的习惯,叫一个女孩儿家听了很不受用,但玉娘隐忍了,依旧含笑答道:
“奴家听说,老爷很不喜欢宦官。”
“哦?”高拱端起一杯酒来正准备一饮而尽,一听这句话又把酒杯放下了,问道,“你一个女孩儿家,怎好打听老夫官场上事?”
玉娘说:“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不喜欢紫禁城内的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拣耳朵听来。”
“因此你就拣了那首词儿来唱,讨我的欢心,是么?”
“正是,”玉娘黑如点漆的眸子忽闪了几下,不安地问,“老爷,这有什么不对的么?”
“也没有什么,”高拱长吁一口气,说道,“玉娘啊,老夫看你是聪明过头了。”
高拱说着,脑子里便浮出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石不能言最可人。”
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儿家,干吗要打听大老爷们官场上的事情?既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她日后不掺乎进来播弄是非?虑着这一层,高拱又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奴儿花花,她不也是有着倾城倾国之貌么?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毒害越大。这么想下去,本来已被撩拨得精神振奋欲火难熬的高拱,刹那间又变得眼含刻毒心如冰炭,他推开杯筷,起身走出书房。
一直候在书房外头过厅里不敢离去的高福,见主人走了出来,赶忙满脸堆笑迎上去,喊道:
“老爷。”
“唔,”高拱停下脚步,盯了高福一眼,说道,“你把玉娘送回去。”
高福一愣,小声问道:“送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