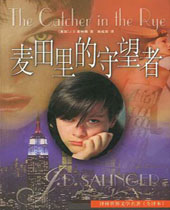俾斯麦-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威廉亲王与西姆松(这是一位令法兰克福人失望的领袖)辩论他哥哥到底是接受帝位还是不接受帝位?俾斯麦也大为诧异,因为早一天,他们在议会曾签署一篇劝进文字,献与君主:“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们深信,请陛下担任德意志至尊无上的皇帝……我们迫切期望陛下不要忽略德意志国会的请求。”
这篇劝进文章有俾斯麦的签字,也有他的亲戚克莱斯特与阿尼姆的签字,同时签字的还有两位有爵位的大臣。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所有的传记作家都忽略了这件事。俾斯麦就是这样承认他所深恶痛绝的法兰克福民族国会成为德意志人的舆论机关。劝君主承受帝位——只因他相信他的君主要做皇帝!他是于1849年4 月2 日为这篇劝进文签字的。这一天他却以为君主太偏于民主派,会有演说反对他。说到一半,他大哭起来。一年之间,这位初出道的外交家的忠心却是有了不少长进。
君主辞了帝位不做,人人都很诧异,贵族公子们却是很放心。21日,俾斯麦在演说台上说道:“法兰克福国会所颁布的仅为显示自己欲望的不合法律的议案(这时有许多人打岔,议长摇铃制止),我认为我们是不该奉行的。”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法兰克福造出来的无政府”。不肯拿他们的承认帮助法兰克福贪得主权。
他往下说道:“我不能同时写两个字……一个是普鲁士,另一个则是德意志。况且联盟范围较窄的德意志民族,除了普鲁士人民之外,别的只有极少数。”
他的最后几句话说道:“谁不想德意志统一?……但是要牺牲这样一个宪法的代价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我认为这大可不必……若是非要牺牲的话,我宁愿普鲁士还是普鲁士……也许法兰克福所奉献的帝冕可以发出奇光异彩,但是制冕的黄金可以使光彩变为真实。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将普鲁士的王冕放在熔炉里重炼出来的王冕,在这样的宪法里还能呈放光彩?”
俾斯麦在1849年就是这样抛弃“统一德意志”的观念的,他所用的就是理论中常用的一种归谬法,二十年后,他自己却放弃了这个办法。但是当拉多维茨当大臣的时候,劝君主赞成小德意志的办法,很详细地发展他的计划。俾斯麦隐去名字在《十字报》上撰写文章,挖苦“拉多维茨的声音中都是赞美自己的话,当众人发出如雷的喝彩时,这个大臣就如同一个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鬼一样,洋洋得意地缓步回到自己的执政座上。”
无论是在柏林,抑或在耶尔福,拉多维茨都在讨论有关联合宪法的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论是关于德意志的或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所要做的只是防备革命的到来。他公然反对议会有不肯投纳税的表决权。他大声疾呼反对同英、法两国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元首,是从革命的血手上得到他们的王冕。他反对自由执业,反对法律式的结婚,尤其反对大城市,他认为大城市是“酝酿革命的温床”。对于大城市,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市镇里有真正的普鲁士人。倘若大城市又要揭竿而起,还是真正的普鲁士人会强迫市镇服从,即使牺牲一切,将市镇削为平地也在所不惜。”他的态度是一种很强硬彻底的态度。他在耶尔福时,有人拿他与革命派领袖弗格特相比。
私下里,他极力挖苦他所在的、热心为人民办事的议院,他说在这个会场里,“有三百五十人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可惜不到五十人会晓得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在这五十个人中,有三十个是有奢望的,又是些没有良心的光棍,再不然就是战场上的小丑,被虚荣心所膨胀。”他很可惜,在南部德意志还有革命活动,他对罗岑菲尔德说道:“我祈求上帝来保佑你的军队,尽管这是很靠不住的。这样一来,战争就会变得愈加激烈,那样会有更好的结果,到那时,这个溃烂的疮口就会彻底地好起来。……这样一来,一切就会如你我所愿的。如果我们动用更大的武力,这件事也就会更好办一些。”他完全陷入一种非基督教的深恶痛绝之中。“三月之乱”后一年,他去看那些为自由奋斗而战死的人的碑,然后他写信告诉夫人:“我认为死者也不可饶恕……因为他们十字碑上的碑文,都是夸张自由权利的,这是人与上帝都以之为耻的!”
只因革命要废除贵族制及其它特权制度,俾斯麦对此便深恨不已。所以从这个时候,俾斯麦便开始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一个Von 字,在这之前,凡是签字,他的名字之前都没有这个“冯”(VOn )字。他对一个自由党说道:“我是两个贵族之子,我要享受我的地位和利益!”但是当召开委员会议时,他却喜欢坐在反对派里面说:“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是极其沉闷乏味的,现在却有趣得多。”他在一次演讲中称赞普鲁士贵族的长处,说得很平和很透彻,这使他的演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看见许多普鲁士贵族们诚然有他们的耶拿……但当我考查贵族的全部历史时,我发觉这些日子人们对贵族们攻击的话是毫无道理的。“随后他又将贵族与君主相比较,研究威尼斯、热那亚、荷兰的贵族,认为欧州大多数国家,现在之所以不太稳定,都是一个时代的结果,那时有势的王公们压制独立的贵族们,——这一种趋势表现在脖特烈威廉第一说的一句话中:”我要用铁腕建立王权。“
俾斯麦走着一条将自己与他的反叛祖先相连结的道路,同独裁制的法治制度挑战,他的那些不太机灵的同事们听了这番话,很是诧异,他的阶级感情同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他演说之后,《喧声》报问道:“我想问一下,1813年那位俾斯麦在哪里带兵?”俾斯麦立刻回答,并且带有一种报复心理说道,关于他自身的问题,他将在报里给予答复。但是关于他的祖先们,有四位(却无他的父亲)是在1813年的战争中坐镇指挥。‘当有人说羞辱我祖先的话时,我就想——等我有了反击的证据时再说——你那有教养的思路,并不完全与我的思路相异……我期望你能给我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君子所不能不答复另一个君子的。“
有时候,力量与基督教这两个要素往往发生冲突。——不过这种事只发生在家庭中。他的岳母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极其独立,所以往往同俾斯麦发生冲突,她很赞同匈牙利自由派的观点,贬斥雷淄,这人曾用血腥镇压将自由党的一些期望完全扼杀。俾斯麦很是激动地给他的岳母写信(在这之前,他只是在她生日时写信为她祝贺):“您对于波顿宜的亲戚们有着许多同情,难道对于千千万万无辜死去的良民就没有同情了吗?这千万人死去了,但他们身下尚有妻小,这些凄凉的情景都是叛党们所造成的。他们如同摩尔一样,要用他们自己的疯狂办法,强行得到他们自己的快乐。这样就是把他们杀了,能够赔偿被焚烧的那些市镇,被躁睛的许多州郡,被无辜杀害的那些人民吗?上帝将法律和权利交给奥地利的皇帝,如果都像您这样怜惜罪犯的话,那是要担负起最后六十年国体走向责任的。您说奥地利政府将走民主制的道路,但是您怎么能将合乎法律的权利与叛逆之徒相提并论呢?符合法律的权利以利刃担负起保护上帝交给人民的权利,而叛党们却不能,当他们也妄敢借助于利刃时,他们就变成了杀人凶手,仍然是说谎的人。他们能杀人却不能正当判人的死罪。路德宣称,‘教会以外的法权,切勿饶恕那些作恶之人,必定要惩罚这种人。’……我为这些事写封长信给您,请您原谅我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很为您这些话所触动,因为将来我若有执掌大权的那一天,我不愿意乔安娜对我的感觉,就像你对雷端的感觉一样。……女婿俾斯麦。”
写这封信的人,好像将这封信当作是一件执政大臣的批文。但当他开始晓得自己的前程是什么时,或是他努力要达到这样的地位时,他认为必定要练就铁石心肠,不为怜惜所动。其实他原是心软的人。尽管他很爱他的夫人,但他从心底里认为她很危险,因为有其母必有其女,她每年要同母亲过几个月,这种影响是很可怕的。在好动情的乡绅社会中,他们不喜欢独裁者就如同不喜欢自由党一样。在我们所引用的这几行信中,俾斯麦发出些低沉的警告,他要反对家中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使他们最后改变观点,这样他才会觉得心安。
十三、婚姻生活
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职业议员了。从三十三岁到三十六岁,他都以议员作为自己专门的工作,倘若他的行为令人诧异的话,我们就会记起他为此所作的解释,想到他为此所付出的热心与努力。他以强有力的意志,来补救他从前所虚度的十年光阴。如今,他却很有些狂妄,再加上天生胸怀大志,迫使他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的身体很好,吃得多,喝得多。“我吃了这样一顿晚餐……吃得太饱了,都差点坐不住啦。”他又说:“在我要睡觉前,我们又吃了些香肠,用刀将香肠割开,分作三次吃完,一点面包都不吃,薄的那一端不如厚的的那一端好吃,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又有一次他写道:“今天我吃了许多无花果,还要喝点烧酒。”还有一次他写道:“随后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吃晚饭,几乎将全部的香肠都吃光了,味道很不错,我喝了整罐的啤酒;我现在写信给你,我把第二盒杏仁糖收起来了……我其实还是想吃,但这时候我的肚子里装满了香肠,实在填不下了。”
他无论做什么都很专注,很热心。有一次他散步走得很远,回来后因为太疲惫,倒头便睡。这觉睡得很长,他的一位朋友出去跑马,跑马回来后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惊动他,否则俾斯麦会大发脾气的。有时他花一天时间出去打野鸡。“昨晚我吃了许多鳄鱼,喝了些啤酒。”他冒雨出发,从一点走到四点,这之间他歇了三次,“因为疲倦得很,我不只一次地要跌倒在地,我只好躺在湿草上,任凭雨淋。……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一只鸡。我看到几只,却离得太远。——五点钟,我回到家中……捱了二十四个小时的饿,幸而我的胃很好,喝了几杯香摈酒。这一觉我一睡就是十四个小时,睡到午后一点钟,现在我觉得很舒服,比出发前舒服得多啦。我追忆上帝赐给我的奇异的大自然风光,这是多么的快乐。‘他研究修辞术,不再像以前那样羞怯。他同歌德三十岁时一样,说他现在的生活比较快乐,达到心境的安泰。只要略微有些不舒服,他就不满意。后来因为他说话有些缺陷,他就深感不安。”因为得了伤风,我就觉得一早上都不舒服……我忘记了我要说的最好听的话,因为我很糊涂。“他承认,”到了晚上,除非我是疲倦极了,不然的话,独自一人总觉得心烦。“
他要在柏林过独居的生活,这使他很痛恨一切,尽管如此,他还要久住柏林,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倘若他租几间房子过冬,他就会把屋子很准确地描绘给夫人,告诉他所睡的床放在什么地方,告诉他所花的房租是议员薪水的三分之一。谭斯麦一生都很注意他所居住的地方。“我的东西满地都是,无人替我收拾。小宝贝,我不知道几时才能与你在红帐之后安宁地同眠,几时才能同享我们的茶点。”
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很安宁,他们还要再享四十年的安乐日子。恋爱时的如火如茶如今并没有丝毫减少。这并不是因乔安娜比所有女人都好,实在是因为他娶她作夫人时,他的性欲最旺盛期已经过去了,转化作同别人竞争的力量。他们轮流记日记。结婚那一天,他写道:“结婚啦!”有一次她写道:“吵了一整天,两天不说话。”他看到后用笔划掉,用一恰当的比喻在一头写道:“好天气!”有时他写信给她说:“我们分开还不过四十二个小时,我就觉得从看见你站在山顶的杉树丛里朝我摇动手帕至今,似乎已有一个星期那么漫长……我的泪水滴到胡子上,我记得从前放假之后,要回学校。离家之前,我哭了,此后这是第一次哭。我回顾从前,使我感谢上帝,因为还有人让我对她难舍难分。”
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对她说:“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就算生下来的是只小猫,我也要感谢上帝,因为生完孩子,乔安娜就不再痛苦啦。”当她临产时,他睡在她屋里,与那个服侍月子的看护相比,她更相信自己的丈夫。“我就是这样过日子,有时写点东西,有时忙着策划政治奋斗计划,其余的时候,我就当我夫人的看护。我觉得这两件事我都会办得很好。”
倘若他的夫人或儿女们病了,俾斯麦就慌得不行。他写道:“小宝贝,自从孩子得了红痴症,我每天都处在绝望不安中。接到你最后一封信,令我无法不难过。最后这几天,各种可怕的可能都在我的脑海中—一走过。”当奶妈的孩子死在柏林的时候,他写了三封信寄到乡下,告诉家里人应该怎样慢慢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乳娘,免得这个噩耗会危及吃奶的孩子。
他那因爱而生的专制也在渐渐增长,他离开他的夫人几个月后,他不许她住在娘家候产,“你若是在赖安菲尔候产,那么就等于我们离了一半婚。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与你分开这么久,我们分离的日子已经够多啦。”当她附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她的一个朋友时,他求她下次“把住址姓名写明白些,我拿起大笔一挥粗粗地在住址上写交‘你的伊丽莎白’。无论你怎样喜欢她,你在信封上总要写得冷淡些、客气些,这是习惯。”
当他向她求婚的时候,虽然也曾要求她出来做事,然而那时他自己是否出来做事,还在未定之列。现在他已混入政坛,进入社会,他却不要求她也这样做,他写道:“这样的新闻虽然使你的父亲觉得很有趣味,但你是不会明白的。”但是他在她的信里头,乱七八糟地将国际间的政治与家庭琐事混在一起。“倘若孩子跟着乳娘生长得并不好,你自然做你所提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