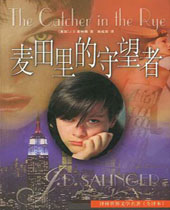俾斯麦-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是自己在政治上的弟子。俾斯麦极为渴望得到这个差事,他为此想了好几个月(他也是很努力地去争取这个差事),这个差使是极为重要的。在普鲁士想做官却是极不容易,倘若只是一个人,哪怕你有再大的能力,若要爬到上层去,还需要许多秘密的关节。有人若提议升他的官,光提议就要好几次,还要在宫廷内活动,在内阁活动。
现在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着地道的外交官的话,这个职务是费了许多力气才得到的,他认为是出于偶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差事,就如同从前的一则“捕鸟者亨利”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亨利外出捕鸟,忽然有人请他做皇帝。挥斯麦对于得到这个职务就是带有这种感觉的。他探望夫人后,刚刚回到柏林就给夫人写信,说道:“这里没有人不在谈论法兰克福这个差事,今天报上已经登出这件事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又写道:“他们派给我的是一件外交差事。……我想将这个差事长久地保持下去,以便也将你安顿在那里。……也许我对这件事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也许这件事会失败的。……凡是不能使我享受家庭之乐的差事,我不久就会摆脱开的。”他又说:“假使我甘愿受这种束缚,那就意味着我要失去许多人生的快乐,失去了和你与孩子们第一次过冬和过安闲日子的希望。上帝将会决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快乐的事。……我尚未对外声明我的想法,也不想在哪一方面活动活动。”又过一天,他说道:“我的可怜的小宝贝,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啦,还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一份薪水。”
俾斯麦解说这一件事,说这是上帝对他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要用“格拉赫”代替“上帝”两个字。他所说的关于房子和家庭,尤其是他所说的“束缚”两字,却是极为真实。他想这必须先要在法兰克福站稳脚跟,因为他既想舒服地过日子,又不想放弃政治。又过了一天,曼陀菲尔问俾斯麦,想不想担当这个职位?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愿意。”他一得到这个差事,他那久已暗藏的傲气全部发泄出来,他去见君主。
“你一向并无外交阅历,却担任这个外交责任,这表明你是一个胆大的人。”
“陛下将这样重大的事托付给我,应该是陛下的胆子大。倘若我不称职,就请陛下毫不客气地免去我。我自己不能说凭我的才力能不能称这个职,要等我试了以后才敢说。陛下有胆量任用我,我就有胆量执行。”
“好呀,我们试试看吧。”
这次君臣的谈话着重谈如何为国家尽力,但是十三年前,他辞职的时候,只告诉了省长的门卫,说他一走就不再来啦。今天他写信给她的夫人说:“你曾经说过不满意的话,说长官们不肯委派给我官职。今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忽然得了这个差事。从现在看来,这是我们外交差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虽然在这封信里流露出他的夫人要他做官的事情,又因为他得不到官做,他的夫人很难过,他却很安详地说:“我并未求这个差事,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只好奉行。我不能做别的……辞去就意味着你无胆量,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有一位慈祥的上帝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危及我们的幸福,不伤害我们的灵魂。”又过几天,他却改变了这些见解,吩咐要缝制一些丝绸衣服,置手枪,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是不叫一个外交家的。他还告诉她,他不过只做几个月的属员,随后就做大使。
现在乔安娜却开始说不满意的话啦:“你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在国外诚然是很适意的,但我一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乡下,而且隔得很远,我就心怀怜爱,一想起来几乎就要落泪。……你一定要习惯这一点,明年冬天你就要到这个大世界来。如果你不来,我怎么会感到温暖呀?将来有几年,我将不时地请短假回家。……我是上帝的兵,他打发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凡是上帝让做的事都得做好。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吧。……我害了想家的病,想你们,想翠绿的春天,想乡下的生活。我的心很沉闷。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军长,用条约和君主的情形来教训我,我却从窗口看底下的花园,园里的野栗树开花了,在风中摇荡,我只想同你一起看,我看得十分人神,并未听见格拉赫说的什么。你的信是昨天到的,我觉得很不快乐,心里以为你病了,躺在床上流泪。……我在法兰克福,最初的薪金是三千元。我要变作一位参政——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参政,现在我却要当参政了。这是上帝惩罚我。……我只想抱你一分钟,告诉你我是多么地爱你,若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会十分难过的。……我忽然得到这样体面的差事,心里却是很痛的,…我比以往都爱你!”
在他心中,来来去去的就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上帝与爱人使他无从选择。他不能坦白地承认他的诸多用意,其实这许多用意都是很合理的,各方面都说得过去。俾斯麦到底害怕什么呢?他不怕权力,也不怕奋斗,也许他看见这官道的阶梯而觉得可怕,这是他少年时就望而生畏的。他虽然并未爬到最顶层,他也是害怕,怕他的长官,怕受强迫,怕作报告,怕长官将他指挥来,指挥去。他的傲骨怕是要被折服。所以他忽然很想回去过田园般的生活,这是他多年所不享的清福。所以他想将乔安娜搂在怀中以求欢乐。但是格拉赫站在他的身旁,正在教训他。还未说完便催俾斯麦动身。这位新任的外交家写信给他的夫人,信尾还附了几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奇异的悲喜交加的感情:“你以后写信要写明寄交莱茵河边法兰克福,钦派普鲁士大使馆参赞俾斯麦收。”
一、大使生活
“我觉得这里面让人厌倦得很,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奥地利人接连不断地搞些阴谋,但是我们在面子上还不得不作相处友好的样子,……各小邦的代表,大致看来,都是一群老派的外交家。即使他们只是同你借个火,他们也要拿出外交家的态度。当他们向别人索要厕所的钥匙时,他们也要带着特有的礼貌,选择好讲话的字眼,摆出友好的态度,然后才向你索取钥匙。……倘若我在这里能够不受他人控制,我就要斩除野草,不然我就打道回府。……我在这里觉得有些埋没自己,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我盼望不久这一切将会有所改变。……况且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德意志政策能否实行,如果能够实行,那么将要实行到什么程度,除非我重权在握。……据我看来,在普鲁士外交界里头,极少能使一个成年人的奢望达到满足,他能够办的事也寥寥无几。除非他是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所以当俾斯麦初人外交界的时候,他的心清处于不耐烦和厌倦之间,挖苦与讽刺之间,他所渴望的东西,也只不过才到手几个礼拜,如今他所处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他已说过,他所做的事不值得一个成年人去做。他认为他的同事们是极其可笑的,他想解除自己身上所承受的种种束缚。假若有人告诉他,不到1862年,大权是不会落到他手里的,假若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再等十一年,他定会立即辞职,然后躲在申豪森的家里安闲度日。他一定不喜欢当副军长,却喜欢做君主。如果能这样的话,德意志问题他转瞬间就会解决掉。
现在使他伤神的是,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顶头上司,他要听这个顶头上司的调度,而且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他到法兰克福的第一天,写信给乔安娜说道:“我必定要习惯做名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按着钟点做事,什么时间办什么事,而且一办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那些游戏与跳舞的事都与我无关了,上帝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对他的夫人说着这种郑重的话语。其实她与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也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枯燥无味的人。他还是以前的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性格是永不安静,无论他办成功什么事,事过不久他就看不起这样的成功。凡是浮士德那样以长久的努力而办成的事,由于他那永远不能满意的精神,又让这件事败坏于魔鬼之手。
他写信给格拉赫:“去年春天,若是派我在德意志作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当一个学徒的话,我想我会更加高兴的。”其实,据他看来,无论什么差事,都要比在最后的第三年里整日听着那些他所耻笑的代表们乱说着一些毫无道理的话要强得多。对于他第一次打交道的这些外交官们,他觉得:“比下议院的代表们更可笑,而且他们更加盲目自大。……现在我深知在一两年或五年之间,他们将办成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一整天不要胡闹乖乖地呆着,我自己在二十四小时就可以办成。”他才称赞柏林的气象好,谁知在法兰克福呆了几年后,回到柏林,他又开始生气:“议院的诸多争辩毫无道理,有各式各样的无理取闹的事令人气愤。其实我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作一番长长的有礼地辩驳。”
俾斯麦的心清就是这样变来变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事物观察明晰,善于推理,使他能够很快地解决诸多问题,甚至能超过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而且由于他性情的变幻莫测,又使他一旦办成一件事,立刻就转而瞧不起这件事。俾斯麦若是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人,他也就会因之而愁苦至死的。
他所担心的就是谜特烈威廉承受不了奥地利的压力,最后终会取消派遣大使。仇敌们见了这种状况,该会多么高兴!他写信给格拉赫说:“我并非像你的兄弟所想的那么有野心。……假使是由于党派的原因给我的这个职务,若是辞退了,别人就会以为有势力的人认定我不称职。……我现在很想得到这个差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就是这样两面进攻,游说格拉赫兄弟两人,他想这兄弟二人肯定会把他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但在他心里,他对于自己的将来还是很有信心,因为他写信给夫人说道:“薪水已经有三千元,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进项,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但是还需要节省。所以倘若到了夏天,我还未当上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让他们给我加薪,若是办不到,我就不于啦。”
他的朋友们却劝拿不定主意的君主俾斯麦今年不过三十六岁,向来未曾为国家出过什么力,现在一切例案都已推翻,居然当了大使。因为他原是君主麾下的一名侠士,还因为他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傅斯麦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自己一手操办,因为他的夫人尚欠阅历,又不在他身边。现在为了使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身边就需添置一些东西,这与他少年和晚年时一样。他的大使的薪俸从二万一千元起,他手头上从未拿过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开始就置办了好多东西,但仍是很节俭的。他写信给哥哥说道:“一年前,或是六个月前,谁能想到我会花五千金币(每个合二先令)租一间房子。我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以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已经花了一万至一万两千元购置家具,如今尚未置办齐全。花钱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等器皿。地毯与木器却花钱不很多。因为这里吃饭是每一个盘用一个叉,请三十位客至少要用一百副餐具。……我要开一个三百人跳舞的舞会。……仆人们忙着准备东西,无用的花费实在太大……更不必说那十二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一半男仆,一半女仆,我宁愿管理三十个乡下仆人。”
在这个讲究钻营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猜测没有任何人开始做一件大事会像俾斯麦这样从容。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却也会细致地讨论用多少副餐具,或告诉他哥哥说他的老马夫穿起新式衣服来,好像一位伯爵——他对他哥哥说起这些琐事,从另一方面表示俾斯麦的祖先们是成长于不甚宽裕的家庭。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称他是个“世界伟人”,然而他却不过是二等乡绅,只是在忽然间受命当国家代表。俾斯麦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他那乡绅的本色,如少年时大手大脚地花钱,后来才开始知道节俭,一心想增加田产,努力清还田产所担负的债务,然后添置新产,添置森林与村庄,为子孙谋利。有时他觉得这样做很让人讨厌,但是从基本上说,这样做却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由于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使得他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家,并且使他由家长制作风演变成国父的作风。
他的阶级骄傲,也是忽然间变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派头,因为这样的骄傲大于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这个伯爵认为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就是失了身份,俾斯麦报告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说道:“我同那些卖给我家具的商人的太太们跳舞,这些人极有礼貌,几乎使我暂时忘记他们丈夫是那么狡猾的商人。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就是卖给我雪茄烟的商人的太太,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同一位先生跳舞,那位先生是前天卖给我太太窗帷的商人。”俾斯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不同阶级宣战,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种行为很符合他的个性。
惟有他的哥哥明了这一切,但是却不明白俾斯麦的别的事情,他的哥哥“就是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他兄弟二人虽有言在先,两人的钱财要分得清清楚楚,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做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哥哥经营什么事情,他们却彼此不断地互相传递经济方面的情况。他现在属于本地的政事局,却向局里诉说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填补款子、河堤等等。“我现在从申豪森收到欠租,我有许多还债的计划,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极为贪财的资本家。”当他们夫妇不断地被一些王公贵族们宴请时,他却在心里算计,“赴宴时须随身带着行李与仆人,坐马车需要花钱,喝酒也需要花钱,这样算来,我们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在家请几位客的。”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