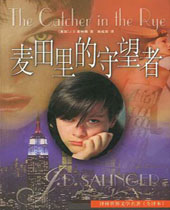俾斯麦-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李与仆人,坐马车需要花钱,喝酒也需要花钱,这样算来,我们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在家请几位客的。”接着他又算计,以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多少次客。“请这许多次客,要花许多钱,我得小心打算,从前对于钱财却没有像现在这般小心。我们现在花费很节省,赔补去年冬天的费用,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又可以好起来。”有这样一笔一千元的款子,从前是可以记公账的,现在却要他自己掏腰包,他当然很不高兴。其后他对于社会上的诸多应酬,他也不再肯花钱。不仅在他早几年的信中,连后来六年的信,都提到这种宴会。“说到这些宴会,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那些切碎了的肉!倘若我一个人将剩肉都吃了,会弄坏脾胃的,倘若我宴请的老少们都帮我吃掉,我喝了太多的酒,也会伤害我的脾胃的。”
基本上讲,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他写信给他的岳母:“我从早上吃茶点时起到中午,这段时间接见大使、听属员们报告公事……随后再到议会,闭会最早也要在一点钟,迟则在四点钟。闭会后等到五点钟,有时我要出去骑马,有时要阅览公文。……我们吃大餐时多数时候有一两位随员相陪,餐后(往往我还未吃完,就有人请我出去)是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我躺在大虎皮交椅上吸烟,乔安娜同儿女们围着我,我翻着二十张报纸。到了晚上九点或九点半左右就有人来报告,说马车准备好了。我满肚子的不快,关于社会上所说的快乐,我有一种很痛恨的感觉,我们必须装扮好自己,以便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乔安娜在宴会上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同她们的女儿们跳舞,要不就同她们的父亲们谈一些严肃的话题,将近半夜时,甚至更晚,我们才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看书,直看到我睡着。等到乔安娜喊我起来,问我究竟是起床还是再睡。”
“使馆里有一种随意的舒适感,其实就是乱,因为太多的礼节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的一个老朋友美国人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说道,‘有好几处大房子,人们在里边可以随随便便’,这就是其中之一。……私宅都在后面,向着花园。人们在这里都是很亲密的,老的少的,祖父母们领着孩子们,旁边还跟着一条小狗。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弹钢琴。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啤酒、饮料、香擦等应有尽有。人人都收藏着极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就吸。”当俾斯麦能够穿他的那件带花的睡衣,并穿到很晚,有时穿到中午,他为此会非常高兴。当他要出门的时候,却不得不脱下这件花衣,打扮整齐。“与其买十件浆过的内衣,不如买五件更好一些的。你只花两元钱是买不着好内衣的。”
这样的生活,使他觉得活得很年轻,在他的朋友柏克给他画的一幅油画中,俾斯麦就显得很年轻。现在他剃了胡子,却失去了许多苍老的感觉。在他未当大使之前,他确实显得有些苍老,后来渐渐地恢复了年轻。他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做外交家考虑的,他虽然对夫人说,他之所以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听从她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听了涅塞洛德的一句示意的话,才决定将胡子剃去的。因为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他不习惯那种坐着不动的生活,这样他会觉得难过。他说了不满意的话:“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使我讨厌到疯狂,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种糟蹋。因为人们要吃许多杂七乱八的东西,以便敷衍到终席。我的肝可要毁了——这些不良后果就先别提了。”但是当他的医生告诉他要他早上五点钟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说:“假使能够找着一个死的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死得更自然一些。”
他身体很重,只能靠骑马、打猎才能把体重减轻些。倘若有公事使他不能出猎,他常常会发怒。“到底还是打猎才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在森林的深处,那里既无人,又无电线,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会感觉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日子,想出了思乡病。……我已日渐衰老,我想享受这闲适的生活。”他求他哥哥给他一匹马,“要能载得动我,还要好看一些的。我不管马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的体力。”我们看什么样的马,就知道他十年间的变化。从前他看马匹与女人,是越野越好;现在他不要驯服什么人。只有当他在丹麦海口外,在狂风大作时在船上过一夜的时候,只有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的时候他有时还会火气很猛地发牢骚说:“人们在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是得不到这样的阅历的。”
其实他的新事业使他老得很快。在他当大使的时候,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力也日渐衰落,然而他却更难以让人对付。他变得更加敏感,看见时光转瞬即逝。他虽然在十年间很不满意普鲁士所作的事,然而却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报告与公文中消磨。两年之后,他写道。“我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会习惯了例行公事,如今我在这里已习惯了这些。……我天生不愿写东西,又是天生的懒,我极为惊异我竟能如此节制这两件事。”我们要想起从前的神斯麦是什么样,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受了怎样的约束。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了两个星期没得到报纸看,就后悔自己少年时虚度了光阴。他在法兰克福三年后,他又说不满意的话,“因为没有事做。”
他说的事自然是政治上的事,并非日常公事,这些是他的属员们去办的。在联邦议院,当议员们发表一些繁冗的演说时,他就写家信逍遥。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犯了政治罪,他得知要拘捕他,他就一大早爬了三层楼去见这个年轻人,说道:“你赶快跑到国外去!”少年迟疑不决,俾斯麦又说道:“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没钱,我给你点儿钱,你赶快跑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说巡警办事可是比外交家麻利。”又一次在俄国都会,有一个逃犯是使馆认识的,俾斯麦替他预备衣服改变装束,从后门把他放走一一俾斯麦随后反责备警察让坏人逃走!这样不合法的事是少有的,但是当遇到这种事时俾斯麦的冒险敢为的性子又发作了。
当他写信时,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的随员们说他走来走去,穿了一件绿色的睡衣,话从口里一句接一句地冲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些批评的话。当他心情好时,他会拖住一位秘书,然后他口述,由秘书来记录,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做人家的长官是很正直很和蔼的。他受不了同他拘泥于礼节的秘书,这使两人在一起不舒服。他请他的秘书们同他一起去打猎洞他一起饮酒,当他在不太得志时,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满意。有两位秘书说起他时,所讲的情形基本相同,俾斯麦训斥他们如同训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有一次有一位秘书没有完全听他的命令,俾斯麦说道:“我想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见解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顾体面的人只要负责一件事,他就会把它做得很好。”如此类的话,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而且他还用一种颇为和气的语气说出来,让人听了真有些不寒而栗。有一次,有一位秘书将一件历史事件记错了,他很客气而又冷冰冰地问:“难道你没有读过柏克的世界历史XX页吗?”
二、政治魔方
奥地利是最重要的敌人,俾斯麦也最痛恨奥地利。当他在法兰克福尚未体验过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无礼的滋味之前,他就已经将奥地利列为全部作战计划的目标。他原本就不喜欢奥地利,现在又有了一层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俾斯麦更加反对它。在法兰克福,俾斯麦已经等待了十二年,先后四任外交部长官都受到他的猜度,因为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正是他所期望得到的,他甚至将怀疑的目光也对准了要占据普鲁士地位的诸邦,在他看来,凡在普鲁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别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他对于奥尔米茨事件的难过,甚至超过了条约本身带给他的难过。他并不袒护这宗条约以避免战事爆发,而是想延缓战事。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欲望决定了他所要采取的方针。
他不能居于最高职位,这一点令他一开始就不甚满意。他只得装作很亲密的样子同十几位大使坐在一起。主席的职位不是他的,而是别人,这对于一个自大的普鲁士人来说,是多么的难以忍受。而那个做了主席之职的人,对俾斯麦来说就是自己挑战的目标。就自大与狡诈而言,图恩伯爵并不亚于施瓦岑堡。俾斯麦是这样描绘他:“穿着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衣衫扣着,里面显然没穿背心,只是露出一点领边,他讨论起议会的事就如同在那儿拉家常。”这几句话,就表明他看不起这位主席。他说他是用一个科学家的理智与冷静,来思考这个令人奇怪的主席,然而他的话我们却不太相信。“图恩在俱乐部赌博,一直赌到早晨四点钟,从十点钟开始跳舞,一直跳到凌晨五点,脸上是一种很舒服、很享受的表情,看这副样子,真不知一夜喝了多少冰镇的香摈酒,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美艳妇女们。……他既有贵族的冷漠,又有斯拉夫族农人的狡诈。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谨慎的诡流。”图恩的副手是一个男爵,俾斯麦说:“有时这个人是一个诗人,极易动情,有时看戏看到动情处常会不由自主地落泪。他表面上对人很和气,乐于助人,喝酒却也常常过量。”
这几句挖苦话,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并不能表明是在什么情形下,比如什么眼神、什么话语才激发出他的这番话来。在俾斯麦尚是使馆的秘书时,曾拜访过图恩一次,陪他同去的还有一位柏林的官员。图恩知道俾斯麦快要做大使,就特意撇开他,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俾斯麦“极为不安以至于声音发抖”,他对同事说:“你看见图思是怎样对待我的吗?”这第一次会面就决定了俾斯麦与图恩的个人关系,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有一次,俾斯麦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访图恩,这次图恩坐着吸烟只穿着内衣(因为天热)接见了他,而俾斯麦也在他面前点了一只雪茄,图恩见了大为惊诧。这一次俾斯麦总算出了一口气,第二天他就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联邦议会开会时,俾斯麦却在会上写着家信:“我所处的位置很不好,因为我的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从两面夹击我,你记得甲的气味吗?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再加上他有狐臭,乙是吃的好东西太多而无法消化所出的气味,这是外交家们所常有的气味。”
在法兰克福,有许多问题都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志的倾向,不只是俾斯麦这样,这构成了联邦议会的部分氛围。从表面看诸邦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奥地利在其中称雄。这是由于最近的历史所造成的。三年前,普鲁士曾离开这里,宣布要重新建立一个联邦议会,撇开奥地利,现如今却又吃了后悔药,重又跑了回来,由此,谁会希望奥地利的代表不会当着众代表的面欺侮普鲁士的代表呢?奥地利有着诸邦的支持,而普鲁士却只有靠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投票。其它诸邦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疑心,因为他们相信,普鲁士会在联邦议会上压制他们,而强大的普鲁士却不会这样。全部的专制派,这就是说几乎全部诸侯都较为附和奥地利。
所以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所见到的,都足以证明他从前的见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让他诧异之处。他从中年到老年,一直都认为,奥地利与普鲁士交好“不过是少年人的梦想,发生于解放之战之后。……”他来法兰克福,本是抱着反对奥地利的信念而来,但是当他发觉奥地利是如此仇恨普鲁士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俾斯麦原想要打听施瓦岑堡的关于奥尔米茨的公文,其中是这样说的:“或者侮辱普鲁士,或者很大方地饶恕普鲁士,其决定权都在施瓦岑堡的手上。”俾斯麦在普鲁士议院极力袒护奥尔米茨条约,他一看见这句话,心中就窜起了无名怒火。
到法兰克福六个星期后,他发表过一次演说:“奥地利现在是,将来也是赌钱的骗子,奥地利人的奢望就是推倒一切,与他们进行交往,他们的外交政策都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引导,我想他们是绝对找不到真正的同盟的。”
在十一月间,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反击:“图恩伯爵说话的意思与波扎”一样,发明了许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说几句话来补充一下他的发明。我说,按照这样的光景,普鲁士的存在,尤其是宗教革命的出现,原来是很让人惋惜的事实。……从前在欧洲,是不存在这样的普鲁士,‘就像不承认腓特烈大王的遗产一样’当我能够劝说本国采用这样一种政策之前,必须用兵器来解决诸事。“还有一段文字也记载了这两个联盟”友邦“的谈话,将所有的遮挡都撕了去。我们所诧异的是,俾斯麦之战十五年后才发生。
这样的批评发言,多次被扔到维也纳,自然使两国的猜忌也在不断增加。当格拉赫大声读一段俾斯麦的信给君主听时,柏林的感觉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一段信说,“全部的不幸都根源于我们同奥地利让步,因为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比一个外人更能伤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与我同床的若是一个残忍而懦弱的人,尤其容易做这种事。”那时将图恩伯爵撤回,也无济于事。接替他的是一个政治家,在未调来之前,是奥地利的驻柏林大使。
普罗克施一奥斯膝伯爵比图恩较有意味,很了解近东的情形,是一个比较好的欧洲人,却有种特殊的地方让普鲁士大使不安。
普罗克施一奥斯股拜访俾斯麦多次而且往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来了就同孩子们媒戏,又未免太过于和气。当开会时,他会同俾斯麦谈话谈得很久。“总的来说,较为明显的是我与普罗克施一奥斯膝的关系要比和图恩的关系坏一些,因为图恩偶而还有说实话的时候,而普罗克施却绝不讲实话。‘俾斯麦接着说,”虽然这样,我还是能够常常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