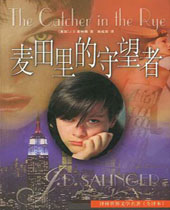俾斯麦-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麦最喜欢的就是:同这个人开玩笑。我却不同这人开任何玩笑,对这一位上司不表示任何友谊的举动。他请我吃中饭,我拒绝了。他屡次请我吸雪茄,我也拒绝。其实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惧他三分,所以他才对我极为恼怒。“
六个月后,俾斯麦病得很重,已经离开使馆很久了,施勒策写信给他的姨妹说道:“全是‘土耳其总督’的错,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来为难我,我只是不想告诉你。”二月间,俾斯麦为家具和仆人之事写信给他,因为别人办不了这两件事。“‘土耳其总督’就是这样为了吃酸苹果而给我写私信。……我的回信也是极为客气,两次都应他所求的给他办妥。”同时俾斯麦写信给他柏林的长官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只有说恭维施勒策的活,起初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如今是完全改变了。”他说这话距他们初次见面已有一年时间了。
再过六个月,转而到了夏天,施勒策写道:“我同俾斯麦相处得非常好。我在柏林听到他在外交场合中说我的好话。我又听说当他身体不好公事又不太顺手时,有人对他讲我的坏话,最初他讲了我好多坏话,如今却都很诚恳地收回他所说的话,我们俩现在相处非常愉快,他在政治上简直是个魔鬼,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几天,他又写道:“我每天都同俾斯麦一起吃大餐,这都是他特地约好的。他就是政治的化身,没有一件事不激励他、促使他采取一些行动。他要在柏林化无秩序为秩序,但却不晓得应该怎样人手。……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常自相矛盾。”俾斯麦到俄都的两年后,写信给柏林,说不要那个无能的卡罗依王爵,而换施勒策当一等秘书。在他未发这封信前,他特意先让施勒策看。而信里说:“当上司的人是很难与施勒策相处的,最初我与他也有一段极为尴尬的时光,但是他办公事认真、负责,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前对他的看法。”
俾斯麦一生只有一次碰到过如此独立的属员,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以后也从未与那些骄横的属员议和过。这两个人最初彼此讨厌,却又不得不赞叹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伟大之处。俾斯麦称赞施勒策非常有办事能力,施勒策称赞他的上司是个天才,后来二人为此惺惺相惜。只是在这之前,这两人都有贵族的傲骨,彼此不肯在资格或地位之前屈服,只可以拜倒在天才与骨气之下。这两个人既然都是天才之人,又都是有着坚强的傲骨,所以他们谁也没输,都是胜者。
七、转折点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神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工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努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1860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人到自由党与对1848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一一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店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对这位失去了权势的人就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久他就渐渐地将格拉赫忘记了,又同别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久他又重回俄都,如今时势变得更为紧张,他从俄都远远地观望那边的形势、甚至为之激动到发狂的地步,然而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一遭。以下这段文字施勒策描述俾斯麦的情形:“我那‘土耳其总督’激动得令人可怕,在柏林逗留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那里流行的慌乱和疑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就要到来、施莱尼茨很快就会辞职不干了,前景极为光明。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适合于普鲁士吗?普鲁士人对他的口味么?在这样狭小而有限的诸多环境中,忽然闯人这样一个性如烈火之人卜…他们并不喜欢俾斯麦,而且他们在做事时也并未考虑过他的存在。所以他也只好玩自己的把戏。他不愿住在这里,牢骚满腹。他嫌这里物价太高,嫌这里人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整日也很难见到一个。他经常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便坐在那里披着一件绿色的睡衣动也不动,由于很少运动,酒就喝得多些,喝过酒就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同我谈了许多话,都很开诚布公。他的话很有趣味,对什么都显得猜疑不定,对理由化的东西不屑一顾。试想一下,如果让他来掌管整个外交部,事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来他常说施莱尼茨必定会改当内务府大臣。‘君主就会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当外交总长。’这是总督自己说的话!他日夜都做梦做了一部的大臣!”
如今悍斯麦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有铁链拴住他使他无法吃人,他却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开来。他开始觉得过去的那些消遣都变得索然无味,既不想见人也不想拉猎,在他心里时常转动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何时才能手握大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俾斯麦,比给夫人写信时要真实的多。在这些家信中,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受挫折的信奉基督的人。
后来到了1861年正月间,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摄政王威廉便做了普鲁士王。为了这个位子,他足足等待了三十年,现在已六十三岁。登位后他发觉国内局势极为混乱,自由党对他的陆军新计划大加攻击,心中十分不安。回到家中又要同妻子争吵,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在他心里有一阵是想着让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今年三十岁),全部的保守党(也就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肺特烈威廉一旦传位于他的儿子,脓特烈会很受他那英国夫人的影响,立刻就会同自由党联盟。君主最重要的帮手罗恩是个正派军人,是君主周围那帮人中最为正直的一个。他这人极有大丈夫气概,严肃、谦逊、忠诚不二。他还不善于恭维别人,对有才能之人也从不妒忌。他为人靠两句话作指导:“作你所应该作的,忍受你所必要忍受的。”铸造普鲁士的各种利器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最反对作战的,但是在这个以武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他自己也必须依靠武力来作成一件事情。新君主本是一个军人,在他当摄政王时就请罗恩帮他整顿陆军。罗思让威廉追忆他那伟大的祖先,他亦决心扶持这位君主。当威廉终于加冕时,罗恩劝威廉要学习他的祖先,要臣仆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他的祖先从前都是专制君主。其他的大臣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反对这个主意。罗恩知道只有一个人会勇敢做出决断的,并且只有这个人才配担当施莱尼茨的席位。这个人还有坚强的毅力,他会强迫大臣们宣誓效忠于君主,还能在一个立宪国与党派发生冲突时力行整顿陆军,这个人就是俾斯麦。
但这时君主却不想对俾斯麦作太大的让步,他只想让俾斯麦担任内阁大臣,因为他需要一个奋斗家与压制家来管理之一摊事务,但是绝不能让他来掌管外交部,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神斯麦为此写了一封私信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说:“若是人家诬蔑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条顿种的魔鬼,而不要诬蔑我是一个加尔种的魔鬼。”这是他第一次避而不用普鲁士人的名词;这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当时罗思竭力主张大臣们应向君主宣誓,并要将此列为王室的一条规矩,须人人遵守。他请俾斯麦来柏林,请他电传告诉他自己的策略,因为“君主很难受,王室的至亲没有一人不反对他,劝他不顾体面地签署和约。”在这个冬季,俾斯麦极想得到一个部臣的职位,如今已过去六个月了,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他所愿的职位,这令他大为失望。他并没有发电传告诉罗恩,只是很小心地写了一封回信。
“当我一边想打一只嫩竹鸡,一边却想着回家看我的妻子时,你却命令我‘上马’,很与我的心境不符。我现在已不如从前那样好动,整日无精打彩又加之心灰意冷,我的身体也就远不如从前了。”他认为宣誓并非什么很要紧的事,他并不想执掌内部的一些事务,因为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是太过于自由了,而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又太过于保守,其实这二者完全翻过来才是正确的。他的心里既然装了这么多想法,他就写了两句关于德意志人的话,这两句的含义是极其深奥的:“我们几乎同法国人一样虚荣,倘若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我们在国外还有威望,那么我们在国内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迁就的。”他又说到:“我忠于我的君主,忠到牺牲自我的地步,至于别的什么人,我都懒得为他们动一动手指头。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我恐怕与我的君主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