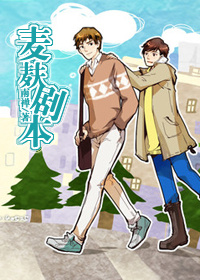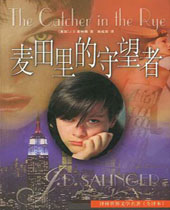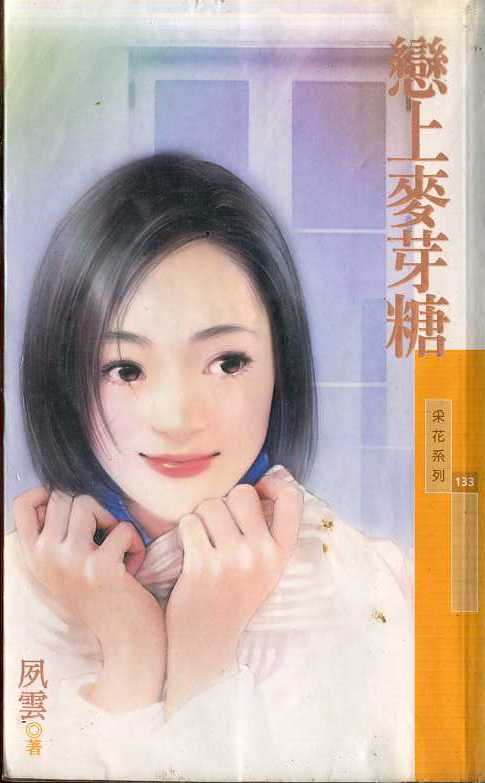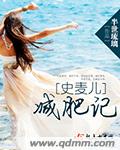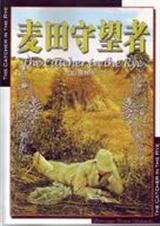俾斯麦-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牺牲自我的地步,至于别的什么人,我都懒得为他们动一动手指头。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我恐怕与我的君主的想法是太合不来,他很难认为我会是一个好顾问。‘当他结束这封信时,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倘若君主能略微让些步,与我的意思相符,我想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的半推半就的态度,这种不敢冒险的腔调,只可以说是他这个人太为执拗,并不能说明是因为他有病。他能够半夜起来外出打竹鸡,而他却以健康为借口,只不过是他要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其实俾斯麦已经看破对他的宣召并不像在办一件公事那样郑重,这样就将他放置于一个极不庄严的地位,这令俾斯麦极为恼怒。后来他来到了柏林,他的老对头奥古斯塔已经赌赢了,君主已经让步,并不要求臣仆们非向他宣誓效忠。“加冕的礼服是二月间定制的,”罗恩说道,“君主似乎更听王后与周围那群人的话。他的身体必须变得更加强壮,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将来会趋向于受议院制和共和制的束缚。”
俾斯麦赶紧去巴登拜见君主,威廉一见到他,立刻显现出“极不高兴的诧异,他认为我是因为看到政府有变动才来的。”只有等到君主对这个“魔鬼”的见解深信不疑时,他才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时有一个日耳曼学生想刺杀威廉,因为他认为威廉并没有为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任何努力。俾斯麦与这个暗杀未遂的学生的见解相同,只不过他不是用手枪射向威廉,而是将许多观念射向他。俾斯麦认为时机已到,便紧紧抓住不放,对威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时幸免于一死的威廉也被学生那单纯的动机所触动,俾斯麦也趁机将自己的意见说与他听,随之将这些内容写个提要。这是他在赖安菲尔避暑时所准备的,是由他的夫人来誊写的。在这件公文里面表达了他的许多可贵的思想,许多不成熟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他那统一德意志,成立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思想也充分表露出来。
“普鲁士绝不能在德意志处于从属地位。……一个联邦要行使的权利要多过其它任何一邦,必须有一个统帅的力量来制约这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在联合的中央法权内派德意志人的民族代表,尚可以联络诸邦,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对抗力量,与诸邦分立政策的离心趋势相抗衡。一旦在每一个德意志之邦中都建立了民众代表制,就不能认为整个德意志采用同类的制度是革命的办法。……假使会员不由民众直接选举而是由各议院公举,那么这样的会员的睿智及他们的保守行为,大约是可以有担保的。……议院的一些穷极无聊的争论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将精力投放在如何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来处理德意志的普通利益问题。”至于内政,各邦必定要保全自己的法权没有任何缺损。因为奥地利一定不会采纳这种计划,自然不能由现在的联邦议院实行。“若想尝试走一条关税联盟之路,来促进异种民族的发展,也许会较为有利。这许多计划一经宣布,必定会发生一种双关的效果:第一层,关于我们计划的范围,要安抚德意志诸王侯之心,可以使他们明白,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乎让他们独立以保存他们的名位,而是在乎他们是否是一种自愿的心态;第二层,要不至于令人们灰心,只有让人们抛弃那些错误的观念认为现在的联邦议院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就会徘徊不前。”
俾斯麦的那许多关于建立关税议院的观念,开始发展成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将现在与他在1840年发表的演说和书信相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已从一个政客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现在是想将他的革命理想转化成为现实,那就是统一德意志。从前他却抛弃这种理想,那是有他的原因,他曾说道:“无人不想德意志的统一,但是有着这样的宪法,我却不要统一。”到了今天,他虽然还是不要这样的宪法,却极力赞成德意志的统一。他的顾虑经过多年之后已化为乌有,并且也成为合乎法律之事:“绝不能再称其为革命。”他不仅仅承认,而且宣称允许德意志人来自己统治,不仅仅是允许,而且是必须——用以对付诸王侯的妒忌!
上文所引用的公文是用律师笔墨来写的,俾斯麦政策的大改变,在他所写的一封信里可以发现,信中还有更为有力的话和俾斯麦所特有的话语。这封信是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反对保守党计划的内容。“德意志诸王侯的无稽的、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的妄想(他们用我们的联邦关系作为一个架子,他们站在架子上,当自己是欧洲的列强),将要变作保守党的惯坏了小宝贝。…哦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该向那些挑剔的民众们让步,无论是在联邦内抑或是在一种关税联合的议院内。……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彻底保守的民族议会而尚能得到自由党的感谢。”
俾斯麦说这番话的十年后,果然召开了第一次德意志帝国的议会。
八、出使巴黎
加冕仪式开始了,威廉一世站在神案之前,从神案上拿起王冕,戴在自己头上。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是从上帝那里而不是从人民那里得到这个王位的。随后是大检阅,在那些神采飞扬的阔人堆里,有一个穿蓝色军服的魁梧汉子。常常出入宫廷的人会猜他是俾斯麦,然而他却满头头发,只有当你走近他听他大声说话时,你才会真正肯定他就是俾斯麦。他说:“我站在宫廷大院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仅要穿上军服,还要戴上假的短发,把伯恩斯托夫压倒,若是无假发,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我想我会受不了的。”国王加冕这一天,他就是这副打扮,再过十年到皇帝加冕时他居然又是这样打扮。第一次加冕,国王躲着他的臣仆们,十年后加冕还是这样。这次威廉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避免外界说他是反动派,王后的行为很让他的丈夫和俾斯麦难堪,她遇到她的对头——俾斯麦时,已经比以前客气了许多。有一次正在行大礼时,她站住脚,站在俾斯麦前面,开始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国王抓住她的手领她走,叫她不要再说下去,连拉了她几次,她都一动也不动。”
但是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王冕,他仍不安心,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到了年底,进步党选举得胜。君主要检阅新军,议院却不答应,到了春天,他命令解散自由党内阁,成立了保守党内阁以助罗恩之力。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见解也还算新颖,但力量却不够大还不足以使他走上新的道路。他代替了施莱尼茨当了宰相,但施莱尼茨仍在背后掌握大权。所以在后来将俾斯麦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他就称不久就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候作了一件错事,当他所辖的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他就派了许多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件事给别人留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俾斯麦对伯恩斯托夫说道:“你若要同黑森宣战,就派我当你的次长吧。四个星期内我保证你有头等的国内战事。”
1862年春天辟斯麦变得很热心于工作,他预备当内阁大臣。俾斯麦自己认为他的专长在外交方面,君主又说一些屈辱他的话,说他当别的还可以,但是绝不可当外交总长。他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久等着,后来他送了一道最后通碟给他的长官说道:“请给我委派职务,不然我就辞职。”结果是在三个小时内就派他到巴黎当大使。他虽多次与上方抗争,但以辞职来恐吓君主这还是第一次。恰好此时巴黎与伦敦都尚未派大使,伯恩斯托夫想到伦敦去,所以就将愧斯麦派往巴黎。他的官运并不太好,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王后更是视他为眼中钉,君主将他看作是一个不祥的政治家,然而俾斯麦却仍敢下最后通碟,敢冒敕令辞职之险。伯恩斯托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帮助俾斯麦的只有罗恩一人,他很得君主重视。
在俄都时,俾斯麦认为他的职务不过是暂时的,果然他只上任不过一年半便调离俄国。他将到法国当大使看作是旅游,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局势一发生变化,罗恩就会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达成的心心相印。从前他很喜欢巴黎,现在却很难有什么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空气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却喜欢装模作样,凭空显出许多虚伪的成分。这两年来,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手握重权,另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会令他生厌,有时过于沉闷使他显得郁郁寡欢,常令他追忆自己少年时最不欢乐的那段时光。
当他从俄都调任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自从我得病以来,我就变得懒于动心计。我的精力再也无法应付那些充满激情的环境。三年前我还可当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如同马戏团里的一个有病的马夫。……上帝与君主喜欢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或到巴黎、或到伦敦、或是仍然留在这里,这一切都无所谓,既不会令我懊恼也不会让我欢喜。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我害怕担负一个内阁大臣的职责,如同一个人见了冷水浴就先抖。我宁愿接受那些形同虚设的席位,或回到法兰克福,或是回伯尔尼,我在那里会很舒服。……凡哈根是个爱慕虚荣且心无恶意之人(俾斯麦正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但是谁不是这样呢?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如何使他们的心走向成熟,成熟的果实中有的就会长了蛀虫,有的会在阳光下显得更为饱满,也有的会被雨水所淋坏;果实有的会变苦,有的会变甜,有的却烂掉了。”
其实俾斯麦是很少受过病魔的折磨,他的夫人,他的子女及其家中的其他人口,却接连不断的有病。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尤其是写信给他妹妹,口气日渐和蔼,也更加柔和。当他自己得了重病时,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以哈姆雷特的心境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世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伪诈与幻术。无论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或是得了一场热病,亦或是一枚子弹将一个人的面具拆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迟早是要扯下来的。等将面具扯掉后,有谁能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普鲁士人,哪一个是奥地利人呢?等到人的血肉与面目都化为乌有时,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与恩钝还不是都一样了吗?如此这样看待世事,就会使人摆脱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于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