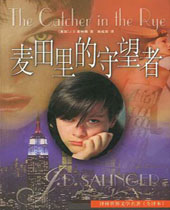俾斯麦-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俾斯麦对法兰西采用这样锋利的手段,实在是件新鲜事。从前他唯有对奥地利才说过这样的话,上文所引的话,是他给他的次长的训条,底下还写道:“你们好像全睡着了!”我们从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俾斯麦睡不着,在那里生气。
自从与卢森堡进行许多交涉时起,俾斯麦就预感战争迫在眉睫。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三世的不稳地位必将引起战争,也许在两年之内就要发生;同时他对另一个客人揭示他欢喜战争的基本动机,他说:“要大多数的德意志人作更广大的联合,只能用武力达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共同的危险。”随后他又换另外一种理由,他同他的朋友柯雪林私谈,描述上一次战事所遗留在他心中的可怕印象,有两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假使普鲁士打败法兰西,到底有什么效果?假使我们得了阿尔萨斯,我们还得保守这块地方,还要永远占据斯特拉斯堡。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法兰西总会寻找新的联盟——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这两句话既简约又预测了未来。
十四、大权在握
俾斯麦说道:“当我以辞职恐吓的时候,老头子首先呜咽流泪,说道,‘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怎么办呀?”这是神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他自然另有用意,那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此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我的主人虽晓得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认为只要教育好了他的长子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悍斯麦曾在一封私信中说自己看不起所有的部长,只看得起罗恩。君主与俾斯麦矛盾冲突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漠的。
俾斯麦虽与君主相处甚久,然而君主却很难与俾斯麦相知,俾斯麦强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于是驯服了那个惟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起初他虽然是驮君主的一匹马,现在却变为骑马的人。谈到七周之战,他有好多理由,“那时候我很卖力,用靴子夹,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悍斯麦常用他的方法,表演他那半悲半喜的子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在1869年初,那一次,他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要挟,他疑心乌泽多姆可以当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的惟一遗憾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陛下要我办的所有事……我要用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我负责的事情,即使我用尽我的精力,还要陛下体谅我,减轻我的各种负担;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需要陛下对我的绝对信任,但还得让我自己行动。我的灰心是被环境造成的,就是说,为公事而择人是要很慎重的,我为国办事而进行了许多奋斗,因此令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又为那些有权力的人所不悦……陛下要原谅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为陛下着想……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的身体会像老王那样。我本不该让陛下论公事时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番话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一件事知道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面对数次罢工他躲着不出来。后来他呈递这封信,在信中他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客观的理由是因为威廉偏听偏信,干预他(俾斯麦),使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死去的,如同老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你怎么可能让我答应你的要求呢?我的最大欢乐就是与你共处,你怎样能因一件事与我意见不合,就随意提出辞职,……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列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想离开我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终于被抛在江心了。君主要兔了他的秘密会友之职,是很难为情的。乌泽多姆丢了官俸,君主解私囊给予赔补。君主原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就是你也不会盼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所说的秘密话。”君主说,他也觉得同他一样的疲劳,问他是否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在三千万人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陛下这样,这无须证明。若是一位大臣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俾斯麦现在与太子相处得还好。这一次胜仗缓和了他们两个人的冲突。腓特烈的自由派亲信敦克尔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未采用;民族自由党们正在追逐大臣席位,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的脾气更大,更骄矜,借在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像是用“同他开玩笑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看你的大志好像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俾斯麦却很郑重地回答她:“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按照我的家风,我要做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一位君主不同,不必被迫用银盘子供食。也许我个人信念将不会被全部继承。我虽然并不猜度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多君主会绝种的。假使没有君主出来,下一代可以变成共和。”这是三个意思,每个都象一杆长矛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全无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这样的天才的显露是一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从此以后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从此以后,人人都把俾斯麦所说的话记载下来。舒尔茨1848年原是一个革命党,逃避到美国办过许多事业,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到柏林来,是一位美国军长,他满肚子都是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能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当他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为其折服。“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显得精神饱满,那有趣的俏皮话,他的大笑(有时候他引人大笑,有时却很厉害地讽刺人),他由诙谐又过渡到深远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事。他的直冲而出的腔调显示出他的霸道人格。”俾斯麦请舒尔茨明日共进晚宴,其他客人都是让人讨厌的,等到其他客人散去之后,神斯麦留住他,现在俾斯麦很和气地问他许多话,包括关于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有许多外交家特有的本领,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有一次阅操,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他说道:“我觉得生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破裂了……我的额后没有脑子,只剩下一团浆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忠君的医生。他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曾用他们的势力反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就会属于在易北河左岸的一部分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一一但这正与事实相反。
有一次一个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他,他装作是一个民主党,谈强迫征兵的好处,他说:“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我被迫扛起了枪,有时我不得不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当一个种田人说他曾经也与乡绅们地位相当时,就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军队里既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需要亲自动手做事。”他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要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他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但他并未在干草上睡过,惟一经历是他在出门打猎时,出于玩闹睡过。
那时候罗恩曾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灵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用这个法子使同事们甘心于自欺欺人,这使我看见难过。他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要让别人明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缩手,他所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的,为世人所讪笑。这一点他看得不错;试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句话问的话表达了罗恩心中深深的忧虑,罗恩见到他自己用符咒所请出来的神,心中十分不安。
俾斯麦一方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是这样),一面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效果对他采取相应的政策至关重要。他不好名,所以他认为名声是一件最可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当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个将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河马”。他把头衔与徽章当作是可笑的东西。在他的公文里他删去几种惯用的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的时候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未到?”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派一个轻批人做宰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缓带滑到地上,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人家替他挂起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耐烦,指着一位王公说道:”徽章大级带是应该这人披的,我想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生有引力,这种东西把徽章大级带都吸紧了,不会滑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喜欢讪笑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况且他很少呆在别处的),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对着他的亲人们,对着他的秘书们时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意在使他们有机会把他的这许多特别之处告诉后人。
这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都说他是大魔术师,是查拉士图。在外国京都出版的书信与传记中也满载他的名字。梅里美说一件事将要发生时,“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要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贵客,左拉把他描绘得极为形象,说道:“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的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的漫步时,她的亲夫却跟在背后。俾斯麦伯爵,原是一个魁梧的猎人,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消遣,忽然间爆发出一阵轰笑声,他的两眼带着嘲笑的神色。”
这时候他的名誉与他本人的人品是相符的。世人也将他当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大家,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识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最善骗人的事之一,但当俾斯麦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欺骗别人,却使人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说他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却不由自主地说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说道:“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过‘我们绝没想到为德国而取得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很容易地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告诉我说,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荷兰,倒是有人想到奥地利的几个操德语的省份。”
其实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要使他的左邻右舍们与仇敌们不安。在他作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使听者传播,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样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是他祭骛不驯的写照,他喜欢这样骂人。自己喜欢说人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知道他能够这样做,这可以带给他一生的快乐。
弗莱塔格的批语虽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引人注意的:“俾斯麦只能在一个出于黑夜而人于白昼的时代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是那些旅行好事者与漂亮的贵族公子们所特有的区域……我看俾斯麦好像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惟一的一个人。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人不能做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极为任性的人,他的祖先也是不甚发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于危险而不顾,拥有真正超群的品质,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有如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同时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的。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全部政敌,与全部阶级,格格不人的。“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说这两句话。“我如果不反抗你们,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从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