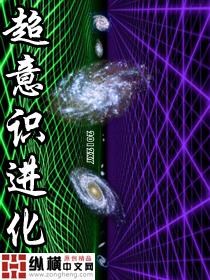西风不相识-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孩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地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份,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晚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的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地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地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象是宿舍里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本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地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地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开了门,我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来,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说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地盯着这个没正义感的人。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
“你肯签字吗?”
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了,才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了。”他叹了口气说。
“贵国的学生,很少有象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
“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地与他握了握手。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地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顺利。
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觉得听见有人在说中文,我很自然地转过身去,就看见两个女同胞排在间隔着三五个人的队里。
我对她们笑笑,算打招呼。
“哪里来的?”一个马上紧张地问。
“西班牙来的。”另外一个神秘兮兮地在回答。
“你看她那条裙子,啧,啧……”“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啊!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她的事情?”
“学生会讲的啊!大家商量了好久,是不是要劝劝她不要那么没有教养。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你想想,小事情,去告什么劲嘛——她还跟德国同学出去,第一次就被人看见了……”我听见背后自己同胞对我的中伤,气得把书都快扭烂了,但是我不回身去骂她们,我忍着胃痛端了一盘莱,坐得老远的,一个人去吃。
我那时候才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洋鬼子可以不忍,对自己同胞,可要百忍,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
我的同胞们所谓没有原则地跟人和平相处,在我看来,就是懦弱。不平等条约订得不够,现在还要继续自我陶醉。
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住处,是托一个好朋友事先替我租下的房子,我只知道我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幢木造的平房。
我到的第一天,已是深夜了,我的朋友和她的先生将我送到住处,交给我钥匙就走了。
我用钥匙开门,里面是反锁着的,进不去。
我用力打门,门开了,房内漆黑一片,只见一片鬼影幢幢,或坐或卧;开门的女孩全裸着,身体重要的部分涂着荧光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倒也好新鲜。
“嗨!”她叫了一声。
“你来了,欢迎,欢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说。
我穿过客厅里躺着的人,小心地不踏到他们,就搬了箱子去自己房间里。
这群男男女女,吸着大麻烟,点着印度的香,不时敲着一面小铜锣。可是沉醉在那个气氛里,他们倒也不很闹,就是每隔几分钟的锣声也不太烦人。
那天清晨我起来,开门望去,夜间的聚会完毕了,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交抱着沉沉睡去,余香还燃着一小段。烟雾里,那个客厅象极了一个被丢弃了的战场,惨不忍睹。
这些人是十分友爱和平的,他们的世界加入了我这个分租者,显得格格不入。
比较之下,我太实际,他们太空虚,这是我这方面的看法。
在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可能跟我刚刚完全相反。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侵犯我、妨碍我,但是我还是学了孟母,一个月满就迁居了。
我自来有夜间阅读的习惯,搬去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之后,我遇到了很多用功的外国女孩子。
住在我对间的女孩,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劳学生,她每天夜间跟我一样,要做她的功课。我是静的,她是动的,因为她打字。
她几乎每夜打字要打到两点,我觉得这人非常认真,是少见的女孩子,心里很赞赏她,打字也是必须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的生活,我总是等她夜时收班了,才能静下来再看一会书,然后睡觉。
过了很久,我维持着这个夜程表,绝对没有要去计较这个同学。
有一夜,她打完了字,我还在看书,我听见她开门了,走过来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就说:“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嗯?”
我回头看看那盏书桌上亮着的小台灯,实在不可能强到妨碍别一间人的睡眠。
我叹了口气,无言地看着她美而僵硬的脸,我经过几年的离家生活,已经不会再生气了。
“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可是,我现在打好了,你的灯却不熄掉。”
“那么正好,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
说完我把门轻轻在她面前阖上,以后我们彼此就不再建交了。
绝交我不在乎,恶狗咬了我,我绝不会反咬狗,但是我可以用棍子打它。
在我到图书馆去做事时,开始有男同学约我出去。
有一个法学院的学生,约我下班了去喝咖啡,吃“唐纳子”甜饼,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上了他的车,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把车一开开到校园美丽的湖边去。
停了车,他放上音响,手很自然地往我圈上来。
我把车窗打开,再替他把音乐关上,很坦然地注视着他,对他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我想你找错人了。”
他非常下不了台,问我:“你不来?”
“我不来。”我对他意味深长的笑笑。
“好吧!算我弄错了,我送你回去。”他耸耸肩,倒很干脆。
到了宿舍门口,我下了车,他问我:“下次还出来吗?”
我打量着他,这人实在不吸引我,所以我笑笑,摇摇头。
“三毛,你介不介意刚刚喝咖啡的钱我们各自分摊。”
语气那么有礼,我自然不会生气,马上打开皮包找钱付给他。
这样美丽的夜色里,两个年轻人在月光下分账,实在是遗憾而不罗曼蒂克。
美国,美国,它真是不同凡响。
又有一天,我跟女友卡洛一同在吃午饭,我们各自买了夹肉三明治,她又叫了一盘“炸洋葱圈,”等到我吃完了,预备付账,她说:“我吃不完洋葱圈,分你吃。”
我这傻瓜就去吃掉她剩下的。
算账时,卡洛把半盘洋盘圈的账摊给我出,合情合理,我自然照付了。
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鱼饵是洋葱做的。
也许看官们会想,三毛怎么老说人不好,其他留洋的人都说洋鬼子不错,她尽说反话。
有一对美国中年夫妇,他们非常爱护我,本身没有儿女,对待我视如己出,周末假日再三地开车来宿舍接我去各处兜风。
他们夫妇在山坡上有一幢惊人美丽的大洋房,同时在镇上开着一家成衣批发店。
感恩节到了,我自然被请到这个家去吃大菜。
吃饭时,这对夫妇一再望着我笑,红光满面。
“三毛,吃过了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你。”
“很大的?”我一面吃菜一面问。
“是,天大地惊喜,你会快乐得跳起来。”
我听他们那么说,很快地吃完了饭,将盘子杯子帮忙送到厨房洗碗机里面去,再煮了咖啡出来一同喝。
等我们坐定了,这位太太感情激动地注视着我,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水。
她说:“孩子,亲爱的,我们商量了好多天,现在决心收养你做我们的女儿。
““你是说领养我?”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气极了,他们决心领养我,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但是,他们没有“问我”,他们只对我“宣布”他们的决定。
“亲爱的,你难道不喜欢美国?不喜欢做这个家里的独生女儿?将来——将来我们——我们过世了,遗产都是你的。”
我气得胃马上痛起来,但面上仍笑咪咪。
“做女儿总是有条件的啊!”我要套套我卖身的条件。
“怎么谈条件呢?孩子,我们爱你,我们领养了你,你跟我们永远永远幸福地住在一起,甜蜜地过一生。”
“你是说过一辈子?”我定定地望着她。
“孩子,这世界上坏人很多,你不要结婚,你跟着爹妈一辈子住下去,我们保护你。做了我们的女儿,你什么都不缺,可不能丢下了父母去结婚哦!如果你将来走了,我们的财产就不知要捐给那一个基金会了。”
这样残酷地领儿防老,一个女孩子的青春,他们想用遗产来交换,还觉得对我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再说吧!我想走了。”我站起来理理裙子,脸色就不自然了。
我这时候看着这两个中年人,觉得他们长得那么的丑恶,优雅的外表之下,居然包着一颗如此自私的心。我很可怜他们,这样的富人,在人格上可是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啊!
那一个黄昏,下起薄薄的雪雨来,我穿了大衣,大校园里无目的地走着。我看着肃杀的夜色,想到初出国时的我,再看看现在几年后的我,想到温暖的家,再联想到我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