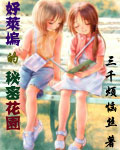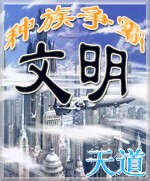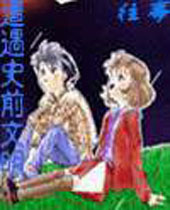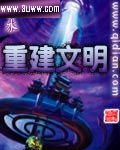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
您所在的位置: 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 >正文
15 对女子行刑的极端处心积虑的艺术
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病后杂谈》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深居简出。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当是凤毛麟角。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女性的过激行为惹怒了官府的事情。于是,如何给女人施以刑罚,成了一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有的妇女犯了罪,根本可以不受惩罚,因为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为受刑。这应该算是对女子行刑的一个极端。古书中关于“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的说法也有很多,体现出法制的“德”的一面。就笞杖刑罚而言,对妇女也是有照顾的,而改用鞭背,对于犯奸罪的则采取脱裤留朡(内裤)的方法。而且,对这类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行刑者也多半会比较宽容,怜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
对于处死女犯,古人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的方法。赐三尺白绫让人自尽的方法看起来也是比较人道的,可是法国一位汉学家依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不过,总有些心理变态的长官,不仅不懂得给女犯留面子,还要变本加厉地暴露她们的耻部。在他们看来,目睹女性赤裸的臀部受抽打,耳闻雌性弱者的呼号,世上或许没有比这更能满足人的偷窥欲和更刺激性欲的事了。前面“旁观者”一节提到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超级变态的刑具——骑木驴,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您所在的位置: 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 >正文
16 神奇的中医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
我们的中医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金庸
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军,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349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
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夹上木板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