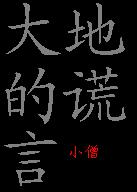大地飞鹰-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是不是一直很需要钱用?”“是的/班察巴那冷笑,忽然回头问小方:“你愿不愿意跟我打个赌?”“赌什么?”“我敢赌这个叫柳三眼的人现在一定已经死了。”班察巴那从未见过柳三眼,甚至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不但赌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而且敢赌这个人是在一个时辰之前那段时候死的,而且随便小方赌什么都行。他赌得实在很荒谬。小方居然没有赌。小方虽然不知道他怎么确实柳三眼已经死了,可是小方知道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小方相信如果班察巴那肯跟别人打赌,就一定不会输的。班察巴那果然没有输。柳三眼果然已经死了,死在他自己的床上。还不到半个时辰,出去调查的人就已经回来了,证实了这件事。“柳三眼是被人用一根竹筷刺穿咽喉而死的,杀死他的人手法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线索,附近的人也没有听见一点动静。”班察巴那一点都不惊奇,这本来就是他预料中的事。惊奇的是小方。他忍不住要问班察巴那:“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死的?”班察巴那不回答,只淡淡地笑了笑:“还有件事我也可以跟你打赌,随便你赌什么都行。”“这次你赌的是什么事?”“我敢赌胡大磷他们三个人的棺材现在已经不在他们的坟墓里。”班察巴那问小方:“你信不信?”小方不信。死人已经入棺,棺材已经人士,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呢?班察巴那凭什么敢打这种赌?小方实在忍不住要跟他赌一赌。幸好他总算忍住了。因为他若真的赌了,他就真的输了,赌多少就输多少。胡大鳞他们三个人的棺材,居然真的已经不在他们的坟墓里。坟墓已经是空的。三口装着三个死人的上好捕木棺材当然不会忽然凭空消失。这三口棺材到哪里去了?世上有很多看来很复杂玄妙的事,答案往往都很简单。这件事也一样。——棺材是在地道中被人运走的。——山脚边这块向阳的坟地下面,早已挖好了一条很长的地道。班察巴那问小方:“现在你总该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能确定柳三眼已经死了?”小方不开口。就算他已经明白,他也不会开口。因为他已经发现,在班察巴那面前还是闭着嘴比较好。所以班察巴那只有自己解释。“埋葬这三口棺材的人名叫沙平,在江湖中虽然没有名,却是吕三属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小方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他早已准备好这块墓地,早已在下面挖好了这条地道。”班察巴那又解释:“为了避免我们怀疑所以才找柳三眼做幌子。”他又补充:“柳三眼正需要钱用,沙平就用钱买通了他,等到事成后,当然就杀了他灭口。”用一要竹筷将人刺杀于不知不觉中,沙平的出手无疑比马沙更快更准更狠。班察巴那道:“可是他的智谋比他的出手更可怕,因为他能想得出这个法子。”这个法子无疑是唯一能逃过班察巴那属下迫踪的法子。也只有用这个法子才能尽快地把他们三个人的尸体送到吕三那里去。小方终于开口:“不管怎么样,三口装着三个死人的楠木棺材,总不会凭空飞走的,不管这三口棺材到哪里去了,总要有人去抬。”“不错。”“抬着这么重的三口棺材,不管走到哪里去,多少总会留下一点痕迹来。”“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追?”“如果你要去追,我们就去。”班察巴那道:“只不过我还可以跟你再打一次赌。”“赌什么?”“我敢赌我们一定迫不到的。”这一次小方还是没有赌。地道的出口在山阴。出口当然有痕迹留下来。无论出口外面是草地是干地还是泥地,要将三口棺材运走,地上都一定会有痕迹留下来。无论他们是用人抬还是用车载都一样。可是小方这一次如果和班察巴那打了赌,输的还是小方。因为这地道出口外不远处,就有一条小小的河流,水流虽然湍急,要用羊皮筏子运走三口棺材,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无论是河水是湖水还是海水,水上都绝不会有任何痕迹留下来。被迫踪的人只要一下了水,就算是品种最优秀、训练最严格的猎犬,都追不到了。蓝色的穹苍,苍翠的山脉,湍急的河流,河滨有一排叶子已开始凋零的大树。树下有人,很多人——只有人,没有棺材。小方和班察巴那一走出地道,就有一个人向他们走了过来。一个非常有规矩的人,走路的样子规规矩矩,穿的衣服规规矩矩,言语神态也规规矩矩,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让人觉得过份。小方以前见过这种人,但从未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这种人。——名门世家中的仆役总管,历史悠久的酒楼店铺中的掌柜,通常都是这种人。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小厮学徒出身,从小就受到别人无法想像的严格训练,历尽艰苦才爬升到现在这种地位。所以他们绝不会做出任何一件逾越规矩的事,绝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讨厌。这么样一个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现在这个人已经走过来了,向小方和班察巴那微笑行礼。“小人吕恭。”他说:“双口吕,恭敬的恭。”他的微笑和态度虽然恭谨有礼,却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点谄媚的感觉:“三爷特地要小人在这里恭候两位的大驾。”“三爷?”小方问:“吕三?”“是。”“你知道我们是谁?”“小人知道。”“他要你在这里等我们干什么?”小方问:“是不是要你带我们去见他?”“不瞒两位说,小人虽然已跟随三爷多年,可是三爷的行踪,连小人也不清楚。”他说得很诚恳,就算是疑心病最重,最会猜疑的妇人,也不会认为他说的是谎话。——奇怪的是,最会猜疑的妇人,有时候反而会偏偏相信一些别人都不信的事,最不可靠的事。小方和班察巴那没有疑心病。他们也不是妇人。可是他们都相信吕恭说的不是谎话,因为说谎的人在他们面前一眼就会被看出来。所以小方又问:“吕三要你来找我们干什么?”“三爷跟两位神交已久,已经有很久未曾相见。”吕恭说:“所以特地要小人到这里来等候两位,替他招待两位一顿便饭。”“他要你替他请我们吃饭?”“是的/吕恭说:“只不过是一顿不成敬意的家常便饭。”——吕三为什么要请小方和班察巴那吃饭?——难道这又是个陷饼?——饭菜中是不是又下了能杀人于无形无影中的剧毒!小方看看班察巴那,班察巴那也看看小方。“你去不去?”“我去。”班察巴那说:“我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家常便饭了。”吕恭没有说谎,吕三请小方和班察巴那吃的确实是顿很普通的家常便饭。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来,这顿很普通的家常便饭又很特别。班察巴那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喜欢孤独,喜欢流浪。他通常都是一个人独处在那一片寂寞冷酷无情的大漠里,以苍大力被,以大地为床,只要能充饥的东西,他都能吃得下。因为他要活下去。可是他最喜欢吃的,并不是他经常吃的干粮肉脯青棵饼。他最喜欢的是葱泥,一种风味极特殊的葱泥,用葱泥来拌的饭,刚出锅的白饭。对一个终年流浪在大漠里的人来说,白饭远比任何食物都难求。吕三要吕恭为他们准备的就是葱泥拌白饭。小方是个浪子。———个没有根的浪子,就像是风中的落叶,水中的浮萍。但是当他午夜酒醒,不能成眠时,他最想的就是他的家,他的母亲。他也曾有过家。他的家简陋清贫,几乎很难得有吃肉的日子。但是一个母亲对一个独生子的爱心,却永远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改变的。他的母亲也像别的母亲一样,总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长得高大健康强壮。所以只要有机会,他的母亲总会做一点可口而有营养的家常小菜给他吃。——韭黄老少蛋,烂糊白菜肉丝,八宝炒辣酱,红烧圈子,咸蛋蒸肉饼等。这些都是很普通的江南家常小菜,也是小方小时候最最喜欢吃的。吕三要吕恭为他们准备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吕三当然还为他们准备了酒。虽然每个喝酒的人都有某种偏嗜,可是真正的好酒,还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吕三为他们准备的是一种真正的好酒,只要是喝酒的人,都不会不喜欢的好酒。班察巴那先喝了一杯,才间一直站在旁边侍候的吕恭!“你是不是很奇怪?”“奇怪什么?”“奇怪我为什么不怕酒中有毒?”“小人不奇怪。”吕恭说:“如果三爷会在酒中下毒来暗算五花箭神,那么他就未免太低估了自己。”“完全正确。”班察巴那又喝了一杯:“你确实不愧已跟随吕三多年,只不过你还是想错了一件事。”“什么事?”“你真的认为吕三只不过想让我们吃顿便饭?”“难道不是?”“当然不是!”班察已那道:“他请我们吃这顿饭,只不过要我们明白,他对我们每一点都完全了解,甚至连我们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叹了口气:“别人都说卜鹰是人杰,吕三又何尝不是?”小方忽然问他:“你呢?”“我?”班察巴那又叹了口气:“如果你要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问错人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了解过自己。”班察巴那不让小方再问,反问小方:“你呢?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小方没有开口,班察巴那已经替他回答:“你是个怪人。”他说:“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哦?”“你是个江湖人,是个浪子,常常会为了别人的事去流血拼命。”小方承认。“你好酒、好色、热情、冲动。”班察巴那道:“可是刚才我三次要跟你打赌,你都没有赌。”“我不喜欢赌。”“就因为你不喜欢赌,所以我才奇怪。”班察巴那道:“像你这种人,没有一个不喜欢赌的。”“我也喜欢赌。”小方说:“不过我只和一种人赌。”“你的朋友?”“不对!”小方说:“我只和朋友喝酒。”“你只和哪种人赌?”“仇人!”“你们通常都赌什么?”“赌命。”班察巴那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却还是不明白你这个人。”小方问他:“难道我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当然有。”班察巴那说:“有很多男人都会把女人看得比朋友重,可是你不同。”“哦?”“你对你的朋友实在不错,可是你对你的女人就实在太错了。”班察巴那说:“不管是你喜欢的女人,还是喜欢你的女人都一样。”“哦?”“譬如说‘阳光’。她应该可以算是你的朋友。”小方承认。“可是这两天你一直避免和她相见。”班察巴那说:“就因为她是个女人,而且你多多少少有一点喜欢她。”小方没有否认。“还有苏苏,”班察巴那说:“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总算为你生了个孩子,不管她是为什么来的,现在她总算来了。”他问小方:“可是你对她怎么样?你看见她简直就好像看见活鬼一样,只要你一看见她走过来,你就落荒而逃了。”小方沉默。可是他并没有闭着嘴,因为他一直在喝酒,闭着嘴就不能喝酒了。“还有齐小燕,”班察巴那又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得出她对你不错,可是你对她呢?”他叹了口气:“她走了之后,你连问都没有问过,你根本就不关心她到哪里去了,根本就不关心她的死活。”小方忽然放下酒杯,盯着班察巴那:一就算我关心她们又有什么用?”他问:“我能对她们说什么?我能为她们做什么?”“可是你最少应该表示一下?”“表示你对他们的关心。”“你要我怎么表示?”小方又饮一满杯,“你要我跪下来,跪在她们面前,求她们原谅我,还是要我用脑袋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班察巴那不说话了。小方仿佛已有了酒意:“就算我这么做了,又能表示什么?”他又问班察巴那:“是不是我一定要这么样做,才能表示出我对她们的感情?”班察巴那无法回答,小方又问他:“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这么样做?”“不会!”班察巴那终于叹了口气:“我不会。”“你会怎么做?”“我也会跟你一样,什么都不做。”班察巴那也饮满一杯:“到了必要时,也许我们会为她们去死,可是这种时候,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他的表情也很沉重:“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时无论什么事都要去做,有时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做。”“不错!”小方说:“就是这样子。”班察巴那又长长叹息,举杯饮尽:“也许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悲哀。”一直站在他们旁边侍候着他们的吕恭忽然也长长叹了口气。“其实每种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悲哀。”他说:“像小人这种人,虽然在混吃等死,过一天算一天,可是也一样有悲哀的。”“那么你不妨也说出来。”“小人不能说。”“为什么?”“因为像小人这种人,无论做什么都是身不由主的,就算心里有什么难受的事,也只有闷在心里,不能说出来。”吕恭道:“也许这就是我们这种人最大的悲哀。”他脸上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仿佛忽然下了决心!“但是无论哪种人偶尔都会做出一两件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说出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来,就算他明明知道说出来之后一定会后悔的,他也非说出不可。”“你想说什么?”小方问。“两位刚才是不是提起一位齐姑娘?”“是的。”“两位说的那位齐小燕齐姑娘,以前是不是很喜欢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是的。”“如果两位说的是她,那么两位现在已经可以不必再为她担心了。”“为什么?”小方又问。“因为她现在活得很好。”吕恭笑了笑,笑得很勉强!“也许远比两位想像中好得多。”小方盯着他,过了很久才问:“你知道她在哪里?”“小人知道。”“你能不能说出来?”吕恭又沉吟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小人本来不想说的,可是现在好像已经非说不可了。”他说:“那位齐姑娘现在已经被三爷收做义妹了,而且三爷已经做主为她订了亲。”小方的脸色没有变!好像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只不过喝了三杯酒,喝得很快。“订亲?”喝下三杯酒之后,小方才问:“她跟谁订了亲?”“小人也不清楚。”吕恭说:“小人只知道邓位未来的新姑爷是位剑客,剑法之高,据说已经可以算是天下第一。”“叮”的一声响,小方手里的酒杯碎了